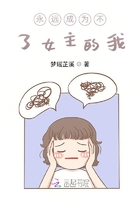下午刚一上班,骆垣就给任之良打了招呼,说要请市委的甄书记一块儿坐坐。让他安排一下。
任之良稍稍征了一下,马上就镇静下来。他想,这个骆垣也真会出难题,局长徐树军刚刚外出,他就要请客,不知他的肠子里又有什么鬼点子了。他是副职,不掌管财务,让自己有点为难,但他请的是市委领导,就让你这个当办公室主任的不敢说半个不字。此其一。其二,骆垣要请的甄书记,就是市委副书记甄恪。这位甄恪,任之良见过面,但没有近距离接触过,听说有点不好伺候。此人是几年前从本省的另一个市调过来的,刚进天龙市的门,他就演义了一段颇具神秘色彩的故事,这个故事至今还在机关上流传,谁想起来都有点不可思议:
他来天龙市报到,事先没有给天龙方面任何消息,只在临出发时,给天龙市委打了个电话,说自己已经出发了,乘的是某某次列车,几点到达天龙市。仅此而已,再没有一句多余的话。秘书长看了电话记录后,立马就傻了眼,他想,如今这领导调动,大都是迎来送往,车接车送,谁都习以为常了。这位可好,独出心裁,坐火车独自赶来了。他在机关工作了二三十年,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自己坐火车来上任的市委副书记。但不管你遇没有遇到过,事情已经发生了,从彼市到本市,区区几百公里,坐着火车,说到就到。怎么办呢,秘书长一时拿不定主意,就去请示市委书记钟润生,不料钟润生轻松地说:
“这没有什么,要是在战争年代,干部调动之事,上级一声令下,扛起行李就走,哪里还有迎来送往这档子事呢。甄书记既然是乘火车来的,到火车站接一下站不就可以了嘛!”
于是秘书长组织人马,急急忙忙地赶到火车站等候,心想这位书记如此廉洁,大概是位好伺候的主。
秘书长率部提前进入月台,因为没有约定接站,秘书长又没见过甄恪,只从侧面打听到他的一些外貌特征,就指示下边的人注意,车一到站,只要看到这样特征的人,都要主动前去询问。
甄恪乘的这趟车到站后,在此站下车的人不多,他们很快就发现了秘书长描绘的、具有甄恪特征的人,此人提个大皮箱,径直向出站口走去。秘书长急忙跟过去,问:
“请问,您可是新来的甄书记?”
那人含含糊糊地“哼、哈”了两声,不理不睬地径直出了车站。
秘书长不能确定此人是不是就是甄书记,他吩咐其他人继续注意下车的旅客,自己紧跟着那人出了站,他又小心地问了句,伸手要接那人手中的皮箱,那人又不知可否地“哼、哈”了两句,叫了辆出租车,上车走了。
秘书长赶忙折转回车站,此处已经车去人空,料想刚才那位“哼哈”先生无疑就是新来的甄书记。
当他率部回到市委大院,甄恪刚从出租车上下来,提着皮箱往办公楼上走呢。
他望着甄恪上楼的背影,轻轻地摇摇头,又摆摆头,一句话也没说,就去到钟润生那儿复命。而这位副书记留给他的这个噱头,至今仍令他难以释怀。
秘书长都难以释怀,任之良就更加难以释怀了。由他来接待,不知还能不能演义出更加神秘的故事呢!
按照骆垣的旨意,任之良到骆垣经常光顾的 “君来顺”大酒店去订座。任之良第一次到这里来。他留意了一下,这是一座外表很普通的酒楼,普通得连墙体都没有包装,红砖完全裸露在外边,被风雨剥蚀得有点寒酸。他进了楼,楼内却装饰素雅,有古有今,古今结合,令人耳目一新。一楼前厅正中,是用天然石块垒成的假山,上面长满了绿色的苔藓,假山下面是一水池,水池左侧装有一仿古水车,水车缓缓旋转,车出的水轻轻地洒在假山上,再从假山上缓缓流入水池。水池里放养着一些名贵金鱼和锦鲤鱼,看上去五颜六色,赏心悦目。
上了楼,曲曲折折的走廊装饰得古香古色,两旁包间的门也很有讲究,艺术味很浓,门楣上面,均以牡丹、桂花、春兰、秋菊等名花命名。进了包间,其内宽畅明亮。一面是宽大的玻璃窗,其余三面,以木制的字画装饰其上,显得古朴典雅。屋顶上的巨型吊灯、豪华的桌饰和空调吹出的丝丝凉气,则透着现代化的气息。楼内楼外,反差如此巨大。任之良想,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真人不露相吧!
任之良点好了酒菜,吩咐大堂经理,接待的是位大人物,一定要搞好了。大堂说没问题,又问任之良,找不找小姐。任之良想了想,说,要找就找两个靓和一点的。大堂又问,小姐们陪不陪饭了。任之良犹豫了片刻,说,先把人找好,客人来了再说吧。
过了一会,客人到了。主宾甄恪是位矮胖矮胖的中个儿男子,神情泰然,和颜悦色。他和任之良握握手,就被骆垣让着坐在了上席。他的左边是骆垣,笑容可掬,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右边是甄恪的秘书,此人看上去三十出头,浓眉大眼,一副谦和的样子。
如今这请客,坐座位是很有讲究的,一般情况下,主人坐主席,主人对面不是办公室主任,就是财务科长,总归这是埋单的位子,别人都避着那个位子的。如果主宾地位比主人高,则主宾坐主席,主宾两侧按地位高低依次往下坐。司机们都是人精,自然知道坐在哪里。甄恪的司机老方和局里的司机小黄,分坐在骆垣和秘书两边,任之良坐在他俩中间,正好面对骆垣,可以察眼观色,随时指挥服务人员倒茶添酒上菜什么的。
主宾落座后,骆垣郑重其事地把在座的客人又介绍了一遍,任之良礼貌地和甄恪以及他的秘书、司机一一握手,说了句客气话,便不再说什么了。
此人到底有舍神秘之处?任之良打量着甄恪。
菜上齐后,骆垣端起酒杯,站起来说:“好长时间没和甄书记一快儿坐坐了,今天甄书记赏光,给了我这么大的面子,啥话都不说,我给你给你敬上这杯酒,一切都在杯中了。”
甄恪端起酒杯,在嘴边碰了碰,算是喝了。骆垣就要甄书记再喝点,甄书记点点头,哼哈了哼哈,骆垣就说,和甄书记交流得少,不知深浅,就随甄书记的意吧。
骆垣连敬了三杯,任之良敬,甄书记仍然用嘴碰碰酒杯,并未进酒。主人敬完,甄恪站起来,说给大家敬个酒,这些年来,全仰仗大家的支持还主请大家多关照之类的话,又把酒杯碰碰嘴,示意大家喝下他敬的这杯酒。任之良注意到,在整个就餐期间,任谁敬酒,他都要端起酒杯跟你碰,之后凑到嘴边意思意思,整个宴罢,当初斟的那杯酒,还是那杯酒,滴酒未下,但他从未说他不喝酒或不胜酒力之类的话,可见社交场所功夫非同一般。
这样把酒换盏了一阵,宴席渐渐接近未声。骆垣给任之良使个眼色,对甄恪说,你稍坐会,我去去就来。于是他和任之良上了楼,等在那里的毛猫走过来,赶忙靠上去,嗲声嗲气地说:
“骆哥,好久没见了,又跟哪里的好上了,把妹妹我给忘了?”
“想骆哥了,是吧?”
“是呀,这还能有假。”
“哪里想了,怎么证明你想骆哥了?”
毛猫凑上去搂住骆垣的脖子,在他的脸上狠劲地亲了一下,说:“就这里想你了,还不够呀?”说着就要拉他进包厢,骆垣拍拍她的屁股,说不行不行,你还另有任务呢。接着又和她耳语了几句。这时,另两位小姐也凑过来了,骆垣一一过目后,就回到餐桌上。
饭后,骆垣说,任主任还有个安排,请甄书记赏光。甄恪的秘书和两位司机很识相,找了个借口,先后出去了。甄恪决意不去。品怡洋就说,就在这楼上的歌厅里跳跳舞,没有什么不健康的。甄恪又推让一番,见缠不过骆垣,很不情愿地上了楼。进了舞厅。他们在舞池边的椅子上刚一坐下,小姐们就围上来了。甄恪见状,有点不安,他说:
“你们这是搞得什么名堂?”
骆垣就说,这是本部门下属单位的女职工,不是社会上不三不四的女青年。甄恪有点不信,站起身就要走,骆垣指着毛猫,对她说:
“你给这位先生说说你是哪个单位的。”
毛猫就说:“骆局长,你怎么连你手下的职工都不认识了呀?”
骆垣就对甄恪说,都是单位的女工,不会假的。甄恪矁一眼毛猫,就信以为真,不好再说什么了。音乐响起以后,毛猫就上来请甄恪跳舞,甄恪搂着毛猫下了舞池,不一会就配合得天衣无缝,跳得十分滋润了。任之良心想,这位新来的副书记,不仅会演故事,看来舞也跳得不错呀!
跳了一会,甄恪要走了,骆垣客气了几句,也就没有坚持,送他下了楼。上楼之后,他把毛猫叫到一边,悄声问她,先生正在兴头上,为什么要走?毛猫说,先生的兴趣转移到下边了。骆垣就说,那你怎么不跟上去呢?毛猫说,谁来结帐呢,你得说句话呀!骆垣就在毛猫的额头上戳了一下,掏出烟盒,撕下一片纸,迅速地在上面写下一个地址,递给她,让她快去。毛猫到了楼梯口,又折回来,问骆垣,是一次还是一晚,能结多少?骆垣又好气又好笑,对她说,我的姑奶奶,这个都好办,你去就是了。毛猫就又回头走了。
这时,先前陪着骆垣跳舞的小姐挽住他的胳膊,一起进了包厢。另一位走到任之良跟前,任之良笑笑,说:
“你的任务完成了,你可以走了。”
小姐说:“怎么,你要换小姐了,我哪点不好?”
任之良笑笑,说:“你别误会,我是想下去透透风。”那小姐还想说什么,任之良就说,“你的台费我会给你结的,你去巴台上结就是了。”
他这样一说,那小姐再没有说什么,冲他笑笑,就去巴台上结她的台费去了。
任之良坐在大厅里,百无聊赖。这里灯光闪烁,正面台子上面,乐队正在演奏一首流行歌曲,有几对男女步入舞池,搂搂抱抱地跳在一起,跳得十分蹩脚。大部分客人坐在舞池两旁的台阶上,嗑瓜籽、喝啤酒、聊天什么的。
不一会,陪骆垣的那位小姐从包厢里跑出来,朝任之良这边走过来,坐到任之良的对面。任之良问她:
“你不好好陪着先生,跑这里来干什么?”
那小姐说:“那先生有病,本小姐失陪了。”
“为什么?”
“他咬人。”
“真的?咬你哪里了?”
这时骆垣也出来了,他坐到任之良旁边,笑嘻嘻地看了小姐一眼,那小姐一脸怒气,没有理他。骆垣马上变了脸,怒气冲冲地说: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哼!”
任之良说:“好了好了,她不愿陪你,我另找一个不就行了,何必生这么大的气!”然后把他拉起来,“你先回你的包厢去,我很快就去落实。”
骆垣骂骂咧咧地站起来往包厢里走,回头对任之良说:“要找就找个大方点的!”
任之良说:“知道了。”
骆垣的小姐很快就落实了,是个“大方一点的”,小姐一上来,拉着骆垣就往包箱里走。骆垣刚一坐下,她就坐在骆垣的腿上,抱着脖子亲上了。不一会,他们出了包箱,上了三楼,在三楼上,走过一段狭长的楼道,七拐八拐拐到了一处地方,小姐开了门,打开灯,粉红色的灯光照在屋子里,一股香味扑面而来。小姐把骆垣让进去,屋子里有一张小床,床上只铺着一条白色的床单,此时在灯光的映照下,粉红粉红的。床头边是一对简易沙发,夹在沙发中间的小茶几上放着香烟、安全套和春药,吃的抺的都有,方便得很。
床那边是用木板制作的淋浴间。坐了片刻,小姐问洗不洗身子了。骆垣说洗什么呀,天天洗呢。说着就把小姐抱起来放到床上,开始脱衣服。小姐闭了眼,轻轻地喘着气,一副可人的样子。骆垣脱了衣服,不知怎么的,在这节骨眼上,他突然想起了妻子王一丹,不知此时的妻子,正躺在谁的床上,对着哪个男人喘气呢。他在心里骂了句婊子,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从床上滑下来,瘫坐在沙发上。
小姐吭唷了半天不见动静,翻起身,坐在沙发扶手上,搂着骆垣的脖子,用嘴在他的身上蹭。骆垣觉的火辣辣的,蠢蠢欲动了。他闭了眼,在朦朦胧胧中看到王一丹在别人的身子下面扭动着,呻吟着。那玩艺儿猛地硬朗了起来,浑身臊热。他转身将小姐抱上床,就动作起来。
任之良没有回舞厅里去,那里的空气太污浊了。他在一楼大厅的沙发里坐下来,坐了一会儿,有人在他前面的茶几上放了一杯茶,他抬头一看,原来是大堂。他说了句谢谢。大堂客气了一句,问他怎么不在上面玩了。他随便应付了两句,大堂坐到他对面的沙发上,对他说:
“看你一个人冷冷清清的,我陪着你说会儿话吧。”
任之良笑笑,说:“你忙就忙你的去,我一个人坐会,等那位先生出来,我们就回。”
大堂说:“那位先生不会很快下来的。”
任之良问:“为什么?”
大堂说:“她常来这里,我知道他的‘消费’习惯。”之后她说,我给你说个故事,有天,恒昌县上去了一位领导,陪侍这位领导的是县上某局的局长,因晚上要活动,局长就对老婆说了晚上回来可能很晚的话。局长的老婆是从农村来的,不懂这些,就说吃呢吃了,喝呢喝了,什么活动还非要在晚上。局长说了个似是而非,不料老婆非让他说个明白不可,不然就不让他出去。局长只好把事说清楚了。局长老婆就说了,‘这种事搁在过去,是偷偷摸摸干的,唯恐叫别人知道了,如今这事,不仅在众人的眼皮子底下干,还要人去陪着。活了这么大岁数,听过陪吃陪喝的,还没有听说陪这事的。’你说她说得多精辟呀!”
任之良笑笑,说:“你可真会编呀,该去当作家,当这个大堂经理,真是屈才了。”
大堂也笑笑,笑得十分好听。任之良抬眼望着她。心想,她不可谓不美,细细的眉,天然的,看不出一点描画的痕迹;眼睛一闪一闪的,在明亮的灯光下,透着一股灵气;端庄秀气的鼻子,有棱有角;说起话来,丝丝入耳。白淅的脸庞在彩灯的照射下,光彩照人,令人爱怜。
大堂被他看得不好意思,就说:“来点啤酒如何?”
他说:“行。”
大堂走过去在巴台上拿了啤酒和杯子,走过来重新坐下,起了酒瓶,倒了两杯,端起杯子,示意任之良也小姐也端起来,他便端了起来,和她碰了一下,她说了声谢谢,喝了一口。她放下杯子问任之良:
“那个胖子是市委的甄书记,是吧?”
“请原谅,我不能告诉你。”
“不用你告诉,毛猫会说的。”
“毛猫是谁?”
“就是陪甄书记的那位小姐呀。”
“她很大方,是吧?”
“不仅大方,而且很会来事。”
“是吗?依我看,那丫头八成不识字的,有什么本事?”
“我可以肯定地说,用不了多久,她也许就成为你的同事呢!”
任之良一脸愕然,望着大堂,轻轻地摇了摇头。
“你不信?”
“也许,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就是毛猫作我的上司,都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对,因为她懂得交换。尽管她没有文化。”
他俩就这样聊着,时间飞快地过去了。任之良感到,她受过很好的教育,文化功底十分深厚,对这个世界和人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于是他忍不住问道:“冒昧地问一句,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她呷一口啤酒,抿嘴一笑:“我也不告诉你。”
任之良哑然失笑,说:“你还真会报复人呀!”
她说:“这不叫报复,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他俩就这样聊着,时间飞快地过去了。一会儿,骆垣和陪他的小姐也出来了,任之良就要上前去,却被大堂笑着拉住了。等骆垣出了门,她才对他说:“这下你也可以结账走人了。”
任之良结了账, 大堂递过来一张名片,交给任之良说:“我想我们还会见面的。”
任之良接过名片,看了一眼,说:“有可能,山不转水转,不定哪天就碰上了。”说着和她握握手,道了再见,出门拦了辆出租车,坐上去,一溜烟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