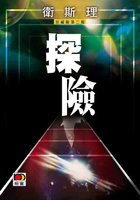杨振凤估计父亲已经知道了内情,便来了个灶神爷上天——照直禀报,说:“不用了,我已经送人了。”说完,两眼直直地望着杨万儒。
“送人了?送给谁了?”杨万儒一脸凝重,胡子一翘一翘的,尽量压低声音。
“聂细龙。”杨振凤很平静地说。
“送给他干什么?”杨万儒目光灼灼,脸色铁青。
“信物。”
“你……”杨万儒没想到平时少言寡语的女儿,此刻说起如此天大之事竟然轻飘飘得犹如一根灯草,真是叫人难以置信。杨万儒半天说不出话来,呆呆地看着似乎有点陌生的杨振凤,只觉得眼前发黑,身子晃了晃,差点倒下。
“爸!”杨振凤慌了,急忙扶住杨万儒,惊恐道,“爸,您怎么了?”
杨万儒稳了稳神,喘着气说:“可能是血压升高了。”
“爸,对不起,惹您生气了。”
“你还知道惹我生气了?你私订终身,我能不生气吗?你怎么也学《西厢记》里的崔莺莺呢?”杨万儒扶着椅子靠背,慢慢坐下,气呼呼地说。
“崔莺莺最后不是挺好么?”
“张生是个读书人,所以有翻身之日;聂细龙是个木匠,今后有什么出头之日?我们和他家门不当户不对呀,怎么能结亲呢?”杨万儒尽量心平气和地说。
“他人好。”杨振凤争辩说。
“人好?他敢私订终身,就不是什么好人!我不能眼看着你往火坑里跳而不管。你娘走了十多年,我怕你们姊妹受委屈,一直没有给你们找后娘。你怎么就不明白为父的一片苦心呢?你的婚事我也有打算,我想让你嫁给丰城南门口那个开当铺的陈老板的大儿子,怎么会让你嫁给一个穷木匠呢?你明天就问他要回小金牛!”杨万儒越说越动情,大大的眼袋微微地颤动,窄窄的眼眶里溢出汪汪的泪水。
“我不。”
“那就我去要回来。”
“您也不能!”
“你不能嫁他!”
“就嫁他!我抽了签,签上说我们该结婚。”
“签上的话你也信?”
“信!”
“你……”
父女俩越说越气,杨振凤气得抓起一把剪刀,剪下一把头发,哭着说:“您不答应,我就一辈子不嫁人,做尼姑!”
“你……”杨万儒扬起抖动的右手,“啪”地扇了杨振凤一个耳光,一把夺过她剪下的头发,大声叫道,“你这个不孝的东西,你是要活活气死我啊……”话未说完,脑袋往椅子后面一靠,脸色紫黑,嘴巴张开,只是呼呼地喘气,无法言语。
“爸,爸!您别吓我啊……来人啊……”杨振凤惊慌失措,大声哭叫起来……
……
聂细龙回到家,将小金牛献给父母看,高兴得语无伦次地说了半天,总算把意思说得八九不离十。父亲聂老根不以为然地说:“我们家这么一点点水,养得了一条那么大的鱼么?就算小姐愿意嫁给你,你养得起么?白马寨的小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过个天井要撑伞,哪是我们这样的人家养得起的?龙配龙,凤配凤,跳蚤配臭虫,我们只能娶一个穷人家的女儿,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知天高地厚!明天赶快把小金牛还给杨小姐。”
“杨振凤小姐很喜欢我。她会绣花、织布,我会做木匠,怎么养不活?”聂细龙也不以为然地说。
聂老根还想说什么,一向谨小慎微、唯丈夫马首是瞻的妻子聂陈氏接嘴了:“孩子他爸,你说的没错,我们细龙是配不上杨小姐。不过,姻缘分,天注定,老天注定他们有缘,也就分不得高低了。算命先生说了,细龙要和一个东南方向的属牛的女子结婚,杨小姐属牛,正好应了那句‘猪牛同栏’的话,这不就是缘分么?缘分来了,挡也挡不住。到时候结了婚,我餐餐吃粥,省给她吃,总该养得起吧?”
“你呀!你把嘴巴缝起来都是枉然!人家喝碗燕窝汤,就够你吃一年,你怎么去省?你们要信算命的就去信吧,我管不了就不管,随你们怎么办!到时候别哭得没眼泪哦!”聂老根生气地走开。
“孩子他爸,你莫生气唦,我说得不对你就权当我起烧打乱哇。再说,说不定女方家里也不同意呢。你何必先就气着等呢?”聂陈氏小心翼翼地说。聂陈氏嫁到聂老根名下二十多年来,总是丈夫说东,她不说西;丈夫说鸭,她不说鸡。说话前先看看丈夫的脸色,丈夫脸色高兴,她就说几句;丈夫脸色阴沉,她宁可话烂到肚子里,也不肯说出来。于是,人送外号“老公应声虫”。今天是因为儿子的婚姻大事,才斗胆多说了两句,看见丈夫气走了,心里突突的,一时没了主意。
聂细龙找来自己的挂件小银猪,用一块红布包好,要母亲缝在红腰带上,扎在身上。这比放在衣袋里稳当多了,怎么也不会丢了。可是,一连三天,连杨振凤的影子也没看见。聂细龙好生纳闷:莫非杨振凤害羞,躲着自己?从那天送小金牛看,她不是那种胆小之人啊!她不露面,小银猪怎么送给她呢?第四天,聂细龙看见杨振凤的丫鬟,见旁边没人,便悄悄地问道:“怎么几天不见你家小姐?”丫鬟说,她也不知道为什么,杨老爷四天前发了高血压,小姐被他锁在了房间里,餐餐送饭,不准出来。
聂细龙心中一惊:莫非是杨老爷知道了杨振凤送小金牛的事,不同意他们的婚事?果真如此,那该如何是好?聂细龙六神无主,心中茫然。
“振远居”虽然已经上梁,可并未竣工,杨万儒一家还住在一栋两进的老房子里。夜深人静,杨振凤躺在床上辗转难眠。已经第六天了,没有出去半步,整天囚犯一般关着。那天,父亲气得发了高血压,晕过去许久,醒来后,第一件事便是要大儿子杨振远将杨振凤锁在房间里,不准任何人与她来往,吃喝拉撒睡全部在房间。每天一早,杨万儒来到房间门口问一次:“想通了没有?”杨振凤回答得很简单:“没有!”天天如此。杨振凤心中着急,六天没见聂细龙,他会不会认为自己故意躲着他?他的挂件自己还没看见呢,手头没有他的信物,心中总觉得空空的,没有着落。每当这种忧愁难以排遣时,杨振凤便默默地背诵聂细龙喝彩的彩词,背着背着,眼前便浮现出聂细龙憨厚的笑脸,心里便稍稍得到一点安慰。
忽然,隐隐约约传来一阵布谷鸟叫声。杨振凤心下狐疑,四月都快要过去,怎么还有布谷鸟叫呢?正迷惑不解,又传来一阵喜鹊叫声。杨振凤恍然大悟,这是聂细龙在学鸟叫呢。他这深更半夜的学鸟叫,是何意思?肯定是几天来没有看见自己,心中着急,变着法子来寻找自己的。可是,自己被锁在房间里,如何出去?杨振凤爬起来,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手心里渗出一层细细的汗珠。忽然,杨振凤借着窗户照进的朦胧月色,看见门框边的炉钉,心中一亮,计上心来。她轻轻地捏着炉钉,用力往上拔。为了不弄出响声,不敢使劲拔,只好暗暗用力。折腾了半天,终于将上下两个炉钉都拔出来了。房门没有炉钉,杨振凤抓住门框,轻轻地往左移动,房门不声不响地开了。杨振凤将鞋子提在手中,光着脚,蹑手蹑脚迈出房门,借着天井里朦胧月色,悄悄地走到前后两进之间的耳门边,一点一点地慢慢抽开门闩,猫儿一般悄无声息地溜出了家门。
蹲在杨振凤屋后面的聂细龙,看见杨振凤出来,高兴得跺脚,说:“你可出来了!”杨振凤摇摇手,穿上鞋,三脚两步地扑进聂细龙怀里,眼泪哗哗地流出来,哽咽道:“细龙哥,总算见着你了……”巷子里顿时传来一阵“汪汪”的狗吠声。杨振凤牵着聂细龙的手,说声“快走”,穿过一条条弯弯曲曲的巷子,钻出了迷宫一般的白马寨。
深更半夜,何去何从?杨振凤和聂细龙毫无目标,两人相互依偎着,机械地挪动着步子,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北屏禅林的“放生池”边。杨振凤不想再走,在池边上一块平整的石块上坐下,说:“这里清静,没有狗叫,坐下来,好好说说话吧。”
聂细龙顺从地坐下,解开腰巾,小心翼翼地拿出那只银猪挂件,递给杨振凤,说:“小姐,你看。”
杨振凤接过挂件,在朦胧的月色下仔细看了起来。许久,将挂件挂在自己脖子上,摇头叹气道:“细龙哥,我们的事难办。”
“细龙是个穷苦人,你爸肯定不赞成。”聂细龙已经明白了八九分。
杨振凤点点头。
“大人反对不要紧,关键你要有决心。”聂细龙安慰道。
“你看看我头上的头发,就知道我有没有决心。”杨振凤低下头让聂细龙看。
聂细龙见杨振凤的头发剪掉了一绺,又感动又惊骇,摸着杨振凤的头,说:“你有如此决心,婚事一定能成。”
杨振凤还是一个劲地摇头叹气,说:“我好为难呢。我爸已经气病了。我若再坚持,万一他气出个好歹,我就成了罪人;不坚持,我又舍不得你。真是为难死了!”
聂细龙沉默了。许久,说:“既然你我都有心,干脆我们就私奔!”
杨振凤心中一动,沉思一会,摇头道:“不行。我要是私奔,我全家在白马寨都抬不起头。我爸会气死的。”
“既不能私奔,又不能结婚,真是难死人!”聂细龙垂头丧气道。
杨振凤想起前几天抽的签,心中似乎领悟到了什么,倒在聂细龙怀里,绝望地说:“细龙哥,看来我们今世无缘,来世才能成双。”
聂细龙惊得身子一挺,擦着杨振凤脸上的眼泪,说:“这话怎么讲?”
杨振凤将签上的谶语告诉聂细龙,说:“你想想,‘龙凤呈祥遨太空’,太空是天上,不是人间,岂不是说我们要归天后才能呈祥吗?‘苦尽甘来不受穷’,我们下辈子都到有钱的人家去投胎,不是就不要受穷了吗?‘猪牛同栏来生福’,要想猪牛同栏只有来生才有这种福分啊!我们今生都是善良之人,特别是你心地善良,这就是为了修来生的福啊!‘长伴暮鼓与晨钟’,是说我信佛,与佛有缘,能长期得到佛祖的保佑,不仅会保佑今生,还会保佑来生。你说,不是与佛有缘,我们今晚怎么鬼懵了头似的,来到这‘放生池’呢?‘放生池’是放生的,看来,我们就要在这里投生,这个‘放生池’就是我们今生的归宿。”
聂细龙听杨振凤如此一说,犹如醍醐灌顶,猛然惊醒,说:“你说得对呀!是啊,要不,我们怎么走到这里来了呢?那签上的谶语句句说得对。那我们只有来生成夫妻了。”
“我们怎么投生?”杨振凤问聂细龙。
“我们手牵着手,同时走进这‘放生池’。怎么样?”聂细龙这时完全忘记了自己是独子,也忘记了家中有父母要赡养,一心只想着归天后“龙凤呈祥”。
“我有一个主意:用你的腰巾绑着你的左脚和我的右脚,再同时走下去。这样,就像月下老人系的红线,我们来生就不会分开,会牢牢地绑在一起。”杨振凤提议说。
聂细龙一拍腿,说:“这个主意好!生生死死不分开。”说着,便动手绑起来。绑着绑着,聂细龙的手无意间触到了杨振凤的胸脯,顿时全身一阵酥麻,那手竟然神使鬼差地伸进了杨振凤的小衣里,慌乱地摩挲起来。杨振凤也全身酥麻,身子软得像抽掉了骨头,缩作一团。渐渐地,聂细龙下身那东西像冬眠的蛇苏醒了,慢慢伸展起来,一种本能的生理需求在全身激活了。猛地用嘴唇堵住杨振凤的嘴,右手颤颤地伸向她的大腿根,呢喃道:“振凤,我们临死前来一次……”
杨振凤突然受到惊吓一般,急忙扯开聂细龙的手,说:“不,我们没有拜堂,还不能做那事!我们要修来生福呢。来生再做那事吧。”
聂细龙像顿时兜头泼了盆冷水,全身凉透了,刚才还噗噗乱跳的心突然不跳了,大腿根部那东西瞬间回到了冬眠状态。说:“好吧,听你的,来生再做……”说完,继续绑起来。绑好后,两人手拉手站起来,搂搂抱抱,一步步走向“放生池”。
四月下旬,又是半夜时分,“放生池”里的水明显带着寒意。刚下水,两人不禁同时打了个寒战,但这仅仅是一瞬间的事,很快就适应了水里的温度。水,越来越深,从膝盖到大腿,再到小腹,渐渐地到了胸口。水温显得越来越低,冷得身子打战,心中有点发闷,呼吸急促起来。突然,杨振凤想起了卧病在床的父亲,有点后悔地说:“我们这样走了,我爸会气死……”话没说完,一脚踩进了一个深潭,咕噜噜地沉了下去,同时将聂细龙也带进了深潭。“救命……”聂细龙也突然有了求生欲望,大声喊叫,可后面那个“啊”字还没说出来,水已经没过了头顶,水随着张开的嘴钻了进去,立即响起“咕噜咕噜”的水泡声。聂细龙本来略微懂一点水性,会踩水,可是,左脚绑在了杨振凤的右脚上,没法踩水,只有任身子往下沉去……
北屏禅林的值夜和尚慧缘,在院子里巡视了一圈,来到门口的香火田边,看看有没有家畜、野兽来侵害庄稼。刚出院门,隐约看见“放生池”里有两个人,忽然一下子沉下去了,想跳下去救人,一想起自己不会游泳,撒腿跑进院子,撞响暮鼓,大声叫道:“救人啊,救人啊!”
顿时,寺里众僧道纷纷跑出来,乱纷纷叫道:“哪里救人?”
慧缘和尚指着“放生池”说:“‘放生池’里有两个人沉下去了。”
几个懂得水性的和尚迅速跳下水,游泳的游泳,扎猛子的扎猛子,一齐赶往“放生池”中央。经过一阵紧张忙碌的抢救,人们终于将两个“连体人”救了上来,放到路上。可是,任凭和尚们如何叫唤,两个“连体人”就是毫无声息。一个小和尚将手放到“连体人”鼻子下试了试,大声惊叫道:“不好了,仙逝了!”住持一听,也慌忙将手放到两个人鼻子下试了试,也大吃一惊。
这正是:
爱情之酒浓又烈,毅然殉情心坚决。
出家之人总行善,紧急关头逞豪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