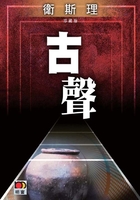王椿熠记得被送到爷爷奶奶身边的时候,只有三岁。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分配到“高寒禁区”的父母,革命工作豪情冲天,根本没有精力同时看护他和刚出生的妹妹。而病床上的爷爷也希望这唯一的孙子能够在他身边陪伴他。于是,顺理成章他就去了爷爷奶奶身边。
那里是北方另外一条巨大山脉的腹地,也是他童年的游乐场。野果是他的零食,雪橇是他的玩具,鱼虾林蛙是他的美味。担惊受怕的奶奶总是试图让他远离那些危险的河流高山,可她的“解放脚”却力不从心。在象征性的揍了他几次之后,奶奶也就专心的照顾爷爷,对他放任自流了。
十四岁回到父母身边时,他已经上了初中。就像一匹散养的小马驹被套上了笼头缰绳,说不出来的难受别扭。而与父母长期分离造成的隔阂使他的性格沉默而倔强。但很快他惊喜的发现,这里的山更高更绿,这里的水更深更清。
那片号召开发的山岭,在他高中毕业等待发榜的时候就曾去过,是跟鄂伦春族同学普列去的,去捕鱼。两只桦树皮制作的筏子扯着“趟网”顺流而下,把缓慢幽深的河水犁开两道细纹,河岸上伸出的树枝拂在身上,轻柔得像奶奶的巴掌。那一刻,他的内心是那样的平静安宁。河水炖出来的奶白色鱼汤,鲜美得梦里都会流口水。
开发这片远离城市的山岭,在王椿熠听来,简直是上帝送来的福音。他的脑海里立即出现美国电影中农场的镜头——主人公骑着高头大马或者开着隆隆山响的大轮农用车,牛仔帽下一双眼睛的雄性目光,自信地巡视着自己的农田、牲畜、山冈、河流。这样的生活原来以为只能在电影里看到,现在却触手可及。我要这样的生活!王椿熠熠在心里对自己说。
批执照的时候,他毫不犹豫的圈下了那条河流的沿岸部分,如同一个将军在地形图上圈下要进攻的目标,手势自信有力。2300亩!这庞大的山脉果然慷慨得出奇,那么宽广的一片土地将归他使用,将由他来命名。他将在那里生活,在那里耕作。梦想成真,原来确有其事。
“你走了,我咋办!”肖影的眼泪阻止不了他。
“你简直是疯了!好好的工作不要了,去山里遭那罪!”那个很看好他的胖局长,把重音狠狠的落在“简直”上,为自己的话做注解。
普列已经在帐篷里睡了三个晚上,可椿熠还没有回来。
就着摇曳的蜡烛,普列在桦树皮针线盒上用兽骨印下最后几个花纹。“这里的白桦树皮太薄,盒子做出来也不好看,你就对付着用吧。要是回来不给我带酒,你就把屁股准备好,看我不踢烂它。”普列自言自语。这几天太阳很好,鱼干晒得差不多了,挂在帐篷的顶部,把鲜腥的味道塞了一屋子。几串榛蘑在蜡烛影子里,如同非洲土着人摘下的项链。
踢开两个空酒瓶子,普列撩起帐篷的门帘走进凝固般的黑暗。还是南风,他在北边的树林边上痛快的撒了泡尿,抖了抖家伙,也不收回去,对着大山使劲地喊了一嗓子,群山的回声撕破了夜空的宁静。他总是试图寻找到最后那一声,可从小到大也没有找到过,山谷与耳朵似乎总是联合起来逗他,支楞起耳朵听,就总像是还有回声。
可这次他似乎听到了其他的什么声音,隐隐约约的,似有似无。再听一会,那声音越来越近了。对!是拖拉机的声音!那条他和椿熠用割灌机在树林中削出来的小道,就挂在对面的山梁上,凝目看去,那里已经能看见一晃一晃的车灯光来。
这小子回来了!把拖拉机也弄回来了!普列在黑暗中深一脚浅一脚的迎着那灯光跑去。
乡间公路的状况不好。有些公路上的小桥,司机要下来看了又看,确定没问题,能够承受汽车加上拖拉机的重量,才敢通过,王椿熠他们就行进得很慢。几个人饿了就吃椿熠带的面包,渴了就喝路边的溪水。到达离农场最近的公路边,已是第二天傍晚。
驾驶室很小,大胡子开车,王椿熠让亲戚跟于大爷坐进去,自己踩着门边的踏板,半边身子吊在车外。天黑了,拖拉机开得很慢,也不必寻什么路。草甸子、小河、矮树林、榛材窠子,一路碾压过去,径直行走。虽还没出三伏,山里的夜却已凉得刺骨。王椿熠把身子探进车里,在于大爷的推脱中把自己的外衣强给他套上,大爷局促得像个孩子。
进得白桦树林,椿熠寻到了那条前段时间跟老同学普列开辟的那条小道。机车在割灌机留下的树根桩子上剧烈的颠簸,大胡子把车开得更慢了。昏黄的车灯光像一把钝刀子,努力劈开前面的黑暗,呱嗒呱嗒的链轨板行走的声音在安静的山林中显得无比清晰。
“都说人老了骨头实,不怕冻,老于大哥,你冷吗?”山风吹过,大胡子的牙齿已经有点打颤了。
“不冷。”于大爷坐在大胡子与王椿熠亲戚之间,又披着王椿熠的外套,显得没那么冷。
“刚处暑就这么冷,这山里能种些啥?种黄豆就得种那些早熟低产的,种土豆子和小麦也不行,土豆子怕冻,小麦也不适合在这山地种。再说这路,运输也成问题!”大胡子的手已经抄在了袖子里,只偶尔伸出来调整一下拖拉机的方向。
“我看,种‘六十天还家’就行”于大爷说话的语气缓慢,但一板一眼的。“六十天还家”是平原地区黄豆遭了早霜,用来补种的品种,成熟得非常快,但分岔少,植株矮小,产量很低。王椿熠在之前参加过地区组织的农场主培训,对于农作物,也知道得不少。
“恩,就种黄豆,等冬天水洼子冻实成了,再拉出去卖。”王椿熠吊在车外的手臂,挡开扫过来的树枝。在前一年,已经有些开发户在山里开荒了,椿熠没少请教他们。
拖拉机爬到了山梁顶,山风更大了,直往人骨头缝里钻。下了这道梁,对面山坡上就是帐篷点了。普列这小子又在喝酒吧?想起老同学,椿熠咧嘴笑了一下,高中三年,他们是最要好的朋友。这鄂伦春小子喜欢的事物,他也都喜欢。连跟别人打架,他们都从没单独过。普列额头上现在还有块疤,那是与椿熠跟校外经常截肖影那帮流氓打架留下的。那块砸到普列额头的砖块,被椿熠拣起来,还给了三豺子,只是部位稍有偏差,直接脸上开花。三豺子掉了的那颗门牙,后来也没见他补上,说话总呲呲的,一直呲到进了监狱。
大胡子突然啊的叫了一声,拖拉机也停了下来。车灯光的尽头,拢住了一个高大的黑忽忽的影子。
“黑瞎子!”大胡子赶紧把自己一侧的车门拉严实了。黑瞎子是北方人给黑熊的称呼,因为它的视力很弱,百米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但它的耳朵和鼻子却特别灵敏,很远就能辨别出各种动静和气味,爬数游泳也都在行,昼夜行动自如。在山区,遭遇黑瞎子是件很可怕的事,据说它发怒了,速度可以追上汽车,力量可以轻易的拍碎骨头。
“操!你才是黑瞎子呢!”寂静的夜里,大胡子的声音传得很远,普列听得清晰,大声地回骂了一句。
“尾(发yi音)巴,你还不赶紧过来跟我说几句话!这些天憋死我了,连个人声也听不见!操,听见的第一句话,却说我是黑瞎子!”普列在车灯影里晃了过来。椿熠的印象里,这老同学是不说脏话不开口,尾发以的音,因为他们在学校形影不离,熠字又与尾字谐音,他便把椿熠说成是他的“尾巴”。但椿熠跟他去打猎的时候,这小子却连一个脏字也不蹦,他们民族很忌讳在出猎的时候说脏话。大自然赐予他们食物的时候,他们心怀感恩与崇敬。
“憋死你,我们正好吃黑瞎子肉,哈哈!”王椿熠跳下踏板,黑暗中一丛割剩的树根拌了他一个趔趄。普列在灯光中看不见黑暗里的椿熠,迷着眼睛循声细看,却冷不防被椿熠在肩膀上杵了一拳头。
“没以前有劲了。我的尾巴,这几天没吃饱吧?我可是每天吃不完的狍子肉,你要是想吃,就拿酒来换。”普列咧嘴笑了。两个人边走边说话,拖拉机在后面慢慢的跟着。这坡基本是一拶粗的小柞树,小道上的树根比白桦树根细小许多,拖拉机的颠簸声也小多了。
“还用我自己动手扒?没看见我穿得这么少吗!”进到沟底,椿熠一边扒普列的衣服一边嚷着。霜打洼地,沟底总是比山坡更凉,椿熠把外套给了于大爷,自己也有点冷了。
“吃点炖肉就不冷了,再晚回来一天,就没你们吃的了。”普列分开沟底小道边的高草,去找那个春熠他们早先发现的那个泉眼去了。椿熠知道那泉眼里一定有狍子肉。泉眼夏天也凛冽如冰,把打到的野物肉放在里面泡着,不但几天还新鲜,又能把肉里的土腥味冲掉,是夏季天然的保鲜柜。
不一会,普列把半扇狍子扔到了小道中间:“真他妈凉啊,这水。手指头快不听使唤了。”普列不停的搓着双手。椿熠拣起来掂了掂,把它甩到了缓慢行走的拖拉机前车盖子上。
椿熠知道,这一定是只母狍子。这个季节,是春天下生的小狍仔刚好能够稍稍离开母狍子,自己觅食玩耍的季节。而母狍子不放心幼仔,往往离它们不远,以便能够随时带孩子逃离危险。聪明的鄂伦春猎人用桦树皮做成拇指大小的哨子,用手指捏着一吹,那声音就跟小狍仔惊恐的声音一模一样,母狍会飞快的赶到发出声音的地方,却不知猎人就埋伏在附近。现在鄂伦椿人的猎枪都被政府收了起来,也就只好用套子来捉拿猎物了。
人类利用了动物高贵的母爱,来填充自己的肚腹。动物也用自己的行为,来教育智慧的人类。鄂伦春人非常尊敬长辈,没有听闻过谁与长辈吵嘴胡闹的。甚至若长辈吃饭,青少年是不得与他们同桌吃饭喝酒的,以示对长辈的尊重。猎人们从不会伤害怀孕的动物,也不会伤害幼小的狍鹿。
“这地方是个修炼的好地方。狐仙,老黄半夜不会来找我们吧?哈哈。”帐篷前,大胡子把车熄了火。黑暗寂静的山林中,他尖细的声音显得尤其突兀。于大爷解开车顶捆包裹的绳子,一件件递给大家。
椿熠把自己的包裹拎进帐篷,从里面翻出几瓶“嘎仙白”来,摆到桌子上。嘎仙,在鄂伦春语中是“猎人之仙”的意思。这酒也就如同大山一般的冷峻厚重,辛辣而沉稳,不会让脑袋难受。
“这么几瓶,够我喝的吗?尾巴,你不是想撵我走吧?”普列拿起一瓶酒,闻闻瓶盖。
“道远,没多带。这几天有机会下山,再给你买。老列,快给大伙整饭,饿惨了。”椿熠顺手揪下一条挂着的鱼干,嚼了起来。这种鱼干晒之前已经用盐卤过,非常有嚼头。如果烤着吃就更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