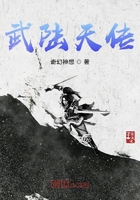可刺猬毕竟是有刺的,会扎动他的人,看他不爽,谁又敢来动他?扎到的人只能是缪冲。
“有多少次机会,你为什么不带她远走高飞?”
缪冲瞪他一眼,“还不是为你!要没有你,我们早逃走了。”没说几句,两个人已恼了。可恼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又开心地聚到一起,聚齐肃王元哲和尚书令王赞等人,到外面打野味。
“丞相,你的车夫好像换了。”除了王赞坐车,其他人都是乘马。
“啊,换了,原来那个打发回乡下办事去了,过几天还回来呢。”王赞的回答没有丝毫磕拌。
元哲想起画画的事,问,“小宁,你那些画怎么样,一春天能不能全赶出来?”
“还能怎么样,我又不会画,不过是起个沟通联络作用,全仗着霍先生。那老爷子你还不知道,有酒才有画,成天醉醺醺,睡不醒的样子,进度慢的很。再说还有五位应画的将军在外地,得等换防时来洛阳才能画,很是误事。”宁贽一副无可奈何的懊恼像。
“那就慢些画,反正画完也是放着,不能往墙上挂。”
这倒是真的,选中的18位将军,除了已战死的元泰,其他都在50岁以下,人生百年,连一半还没过完,这项任务很得熬宁贽几年。
“我有些想邺城那些兵了。”宁贽缓缓吐出几个字,“等春猎结束,我想和小玉回去,把积下的政事处理一下,毕竟担着个太守的名儿,留下霍都在这里等人画像。”
听他这么一说,元哲等人也不好强留。洛阳这个地方,是宁贽的伤心地,少年时做过几日花鸟使,为救他,姐姐不得已自元府进宫。才跟着大将军元泰过了几年舒心日子,人家夫妻俩偏又没了。住半年,已是勉强,再让他长住下去,真比杀了他还要难受。
“真的要走吗?你走了,我连个可以说话的人都没有。”王赞也很伤心。自进入洛阳,只有小宁真心帮过他,其他人不过是见面的交情。人过了四十岁,很难有勇气去结识新朋友,好不容易遇到知己,偏又要走。
缪冲凑到王赞和肃王元哲中间,轻轻说,“想让他多留些日子,很容易,那个路承,很让小宁不爽,想个法子治治他就行。”
“听说他有两个儿子?”肃王笑着问。
王赞正色答道,“是啊,可惜都在外地带兵,这样就不能把他老子弄死,只能小来来。”他的脸色凝重严肃,说这等诡诈算计人的事儿,神色没半点异常,仿佛在念一篇先贤大儒的道德文章。
缪冲坏坏地笑一声,“明白。”转回身,小声与王赞讨论起计划施行的细节。
宁贽知道他们几个不喜欢路承,准是思谋着对付他。
他不想报复,经历过战场的人,一般不愿再见杀戮。封候拜相时的得意与冲天豪气,不过是俗人的想象,真实情况,往往是静默零泣。一将成名万骨枯,多少鲜血,才能渲染出凌云阁的十八名将!可别人要帮他收拾仇人,总不好拦着。肚里暗自笑笑,与元哲说些别的事,由着缪冲和王赞两人捣鬼。
尚书令王赞的帐篷与龙城太守路承为邻,两人晚上常在一起闲坐聊天。策马奔驰一天,路承打到一只野兔和两只野鸡,架起火烤了,进一只鸡给魏王,余下的与尚书令王赞共享。
王赞带了一坛自酿的桂花酒,命人做几样下酒小菜,送到龙城太守帐中。
酒至半酣,路承说,“听说王兄会看手相?”
“你听谁说的?”王赞警觉地睁大眼。
“今儿打猎的时候,听缪冲那小子说的,他说你测得很准。”
王赞松了口气,“雕虫小技,不值一提,哄小孩子玩罢。说来好笑,家师紫阳真人,云游前曾留下一个锦囊,嘱我前往洛阳,说到那里自有结果。我当时问他,能有什么结果?我这样的,无非是位极人臣,还能怎样。
他却说,在这乱世,做君做臣都是缘分,还说这锦囊遇到姓路的将军方可打开。”说着,从腰中解下一个火漆封口的锦囊,当面打开,里面是一张已发黄的棉纸,上写两列小小的梅花篆字,“三路神兵,济世安民。”
这句话让路承夜里折腾许久,他再也睡不着了。能做出那等灭绝人性的事,自不是什么良善忠贞之人。跟着魏王做事,不过是为官位名利,真要是放个江山大业的鱼饵下去,准准的上钩。
“王赞这人已不凡,他的老师更是大名鼎鼎,人家说的话,无疑是神一般的预言。一句话里,包含自家的姓,还有两个儿子的名。尚书令进朝时间不长,人头儿不熟,想来不是蓄意捏造。或者路家真得上天眷顾,能成就一方霸业。”
这日太子遣人送信,说柔然部派人护送公主前来,一行十余人,想拜见魏王,已打发人送他们前来点苍山猎营。接到消息,王赞忙命手下司礼的官员安排食宿事宜。
傍晚时分,柔然这些人才赶到。公主穿一身绿色的衣服,身量苗条,脸部遮着纱巾,一双露在外面的手葱白般娇嫩,想来是个美女。
魏王在大帐中接见,通常是赐座,说些客套寒暄话,呈上礼物,转了半天,才到重点,这个柔然公主,来这里是想在大魏国宗室子弟中挑个驸马爷。这事草率不得,魏王表示得考虑一下,过几天才能定下人选。
对方本也没打算立刻就得到答复,那样显得太不郑重,又说会儿话,请公主去歇着。
“王公,你看这次让谁去和亲好些?”这事从未发生过,以前都是送宗室女子过去,这次人家要的却是男人。魏王此时有些后悔,那年真不该把兄弟侄子们都喂了鱼,早知道有这事儿,该留几个年轻的,预备着和番。
王赞很为难,眼前贵族公子们不少,可谁也不想去和番。别说让皇子们去,就是一般男子,恐怕也不愿去,设法让这个柔然公主嫁进来,或者还行的通。
“陛下,这事容臣再与使臣协商一下,一来问问这公主肯不肯留在洛阳,二来相看一下公主,看长相学问如何。急不得,暂时还没到定驸马人选的时候。”
肃王与王赞、宁贽在篝火前负手站着,看手下的人在烤野猪肉刷调料,香味撩人,肉上的油滴答进火里,不时蹿起一个火苗。宁贽冷静地分析,“太子是不用说的,自然不能动。其他皇子都有正妃,只有你没有。”
肃王不乐意听这话,“没有正妃,也不能拿我去和番当驸马呀?就是想嫁给我,也得看看长相人品,歪瓜裂枣别想塞过来。冲这是是非非,也得早日定个王妃,省得别人老惦记着。”
此时有人来报,说国舅的小跟班豹雏与柔然使者打起来了。
大伙忙过去拉架,这小豹子不是个爱找茬儿的,平时话都懒得多说一句,怎会跟别人打起来?还是外来的使者?
“住手,怎么回事?”宁贽严厉地问。小豹子此时已打倒两个,正与其他人缠斗,见主人过来,闪到一旁。
“这些使者放着安排好的帐篷不住,非要住咱们的,我自然不肯,他们就恼了,几个人一起打我。”
“有这样的事?”宁贽摸一下鼻子,那上面有几颗汗珠,想是刚才在火边太热。王赞见出了这样的事,自去责怪司礼的官员,命他们再去协调解决。
柔然公主此时已立在旁边,一双温柔如水的眼睛细细打量宁贽。“我们以前见过。”她主动答话,说完,解开面纱,精致秀美的脸,眉目焕映生辉,却又暗藏游猎民族儿女的豪侠气概,恰似四月间春水荡起的幽幽碧波,洋溢着故人重逢的快乐。
“是吗,我怎么不记得?”一脸茫然,眼前女孩子的潇洒气质很像长阳郡主雍容,宁贽觉得,与个****快乐的人相比,自己徒有一个柔美的外表,内心却如阴沟里穿行的魑魅魍魉般惶惑不安。
“那是十一年前,你抱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在邺城郊外骑马,我就在城门口,差点被马踢着,你跳下马安慰过我。”又初充一句,“那年我十岁。”
“说笑话吧,一个堂堂公主,去邺城做什么?”
“那时我父亲还是个将军,我也不是公主,只是一个普通女孩子。”
宁贽忽然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误,没有戴上面具,面具不仅能威吓人,更能掩盖脸上的不安。在这个需要美男子献身的大关口,没戴面具真是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想躲起来,不让一丝阳光雨露进入。
不敢再纠缠下去,见鬼一般找借口溜走。他不想借柔然的势力复兴中山国,更不想报什么仇,能瑟缩地活下去,已是难得。说到美女,家中那三个小妾已能唱一台戏,实在没兴趣娶什么柔然公主。能与小玉安然回邺城是目前的愿望,最好不要出现什么枝枝蔓蔓的事,打乱计划。
此举让柔然公主很疑惑,低声问跟随的使女小蛮,“我很丑吗?怎么他一见到我扭头就走呢?”
使女小蛮笑笑,“怎么会,公主是我见到过的姑娘里最好看的,他想是没洗脸怕羞吧,急着回去收拾干净再来拜见。”
龙城太守路承今夜能睡个好觉了。他发现自己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竟然未婚,长得还很体面,文才武功一流,拿出去给柔然公主做驸马,完全合乎要求。真是上天注就的缘分,不信命不行。
睡醒了他就去找王赞,想让他设法玉成此事。
王赞被他堵在床上,缓缓地穿衣着裤,结发系带,仍是一副不紧不慢的样儿,神闲气定,细细分析着此事的利弊,表明自己的态度。
“我是不赞成送出去的,毕竟是异族,离家又远。小路将军在大魏已是一方守将,功成名就,既非皇亲,又不是个文弱之人,送出去做驸马,别人会耻笑的。”
这话说的在理儿。不过良言难劝该死鬼,路承还是一心想办成这事。
“既这么着,我丑话说在前面,这事你决对不能主动,否则依大王的脾气,定然会联想到别的事上,说不定会说你想与柔然勾结,里应外合,图谋造反。”说完,一双眼亮闪闪地盯着路承,看他是什么反应。
其实路承就是这么想的,可他不能承认。朝堂上与他交好的,确有虎威将军姜遵等几个成名的大将,可那都是寻常交情,真要造反,那是谋逆之事,人家未必肯帮忙,还是自己儿子靠得住。
“是个道理,那咱们就撑着,等轮到头上,迫不得已时再接下这单生意。”见到有利可图,有美好的愿望可憧憬,路承的眼光变的很柔和,全没了恶狼般贪鄙的神色。若此时让霍都画像,必不会引起魏王的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