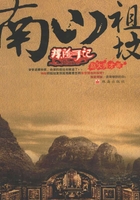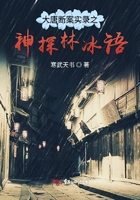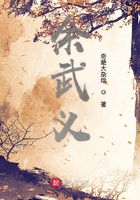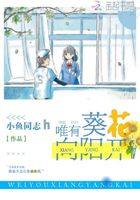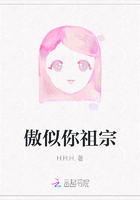冯玉祥本人在我们到达之后才来郑州,这也许是偶然的,也许是他出于对自己应有的威望的考虑。这后一种做法外国人难以理解。这样,他在车站受到了赴会的所有显赫人物的欢迎,而他们自己则只受到冯玉祥部下的欢迎。他故作俭朴地从一节货车上下来,他的发言人告诉我,他坐货车是“因为我的士兵兄弟也坐货车”。很久以后我才听说,冯玉祥在郑州的前一站才上了那节货车,在这以前他一直坐在同一列火车的一节舒适的私人包厢里。冯玉祥的俭朴,是故作的姿态,但比单纯的姿态更具深意:这是个有用的军事策略。他在郑州执行这样一条纪律:禁止举行任何每盘菜价值一元以上的宴会。这样就防止了中国官员通常在宴会上浪费时间和钱财的现象。用俭朴的名声来节省开支总比被说成吝啬要好听些。(《千千万万中国人》,第72页)
6月10日,郑州会议在郑州陇海铁路车站附近的陇海花园正式举行。武汉方面与会者有二十多人。会议由汪精卫主持。会议决定把豫、陕、甘三省党政军大权交给冯玉祥。冯玉祥故意把蒋介石发给他的电报拿给汪精卫看,骂蒋是“狼心狗肺”。不过冯不同意讨蒋,而是规劝武汉方面“息争”,主张宁汉联合继续北伐。
斯特朗后来写道,冯玉祥离开最后一次会议时,由他的外事代表把他对斯特朗书面问题的答复转给了她。他宣称对武汉政府和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绝对忠诚,还宣布他的部队将要改组成为国民党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斯特朗写道:“带着客客气气得来的胜利,火车向南驶去。我们这些旁观者以为联合成功了。”然而,几天之后,冯玉祥赶到了徐州,与那里的蒋介石举行了会谈。最终,他选择了与蒋介石的合作。
在徐州,蒋介石的实力,以及“雪中送炭”的姿态打动了冯玉祥的心。冯玉祥的秘书高亚兴回忆,双方会面后蒋介石“马上就拨给他几十万块钱,以济燃眉,并允以设法接济”。在此之后,南京确定每月救济冯玉祥军两百万元。
6月21日,徐州会议结束。冯玉祥乘车离开徐州,回到了河南郑州。同一天,吴稚晖代拟了一电稿,经冯玉祥再三修改后署名发出,即《劝汪谭诸氏速决大计电》。电文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反对工农运动、阶级斗争,敦促汉方加速“分共”;二是宁汉合作;三是继续北伐。25日,冯玉祥在郑州发出《通告各部队时局近况电》,除再次重申与蒋介石合作的政治立场外,宣布反共、清共的方针,并电请武汉国民政府驱逐鲍罗廷顾问,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冯玉祥将自己军队中的共产党员以及他管辖地区内的地方党员共两百多人调到郑州,先请他们吃饭,然后讲话说:“你们到我这里帮了忙,你们要反蒋,我是不能干的,我要和蒋介石合作反对张作霖。在我的军队里穿二尺半的不能反蒋,你们要反蒋,愿意到哪里去就去哪里吧!”随后,冯玉祥送给刘伯坚一千元,科长以上的每人一百元,其余每人五十元,用一个闷子车皮把二百四十多人一下子拉到武胜关,让他们下车离开自己的地盘。冯玉祥以这种“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在宁汉之间作了选择。
在此之后,冯玉祥分别电告南京与武汉国民党政府,要求化除意见,努力北伐,凡妨碍北伐者即反革命。冯玉祥的举动,给武汉政府以极大压力,迫使汪精卫政府迅速右转,7月15日,武汉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取缔共产党案。第三十五军何键部在汉口作反共示威,占据汉口汉阳各工会,并搜捕吴玉章等共产党人。
8月,按照蒋介石与冯玉祥事先约定,他们在郑州举行了第二次会谈。冯玉祥在讲述他们之间的会谈情况时,曾这样叙述——开始时,蒋介石派了马福湘将军带去一个友好的消息:“蒋愿意和你结拜为兄弟。”冯玉祥的答复是“太好了”。冯玉祥接着叙述:于是,蒋和我彼此交换了生辰八字,成了结拜兄弟,那次会上,我们相互叩头四次。蒋问我:“现在我们已经成了最好的朋友,你准备怎样开导我呢?”我告诉他:“人民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应该做他们所希望的事。”“还有别的吗,大哥?”蒋又问道。我说:“如果我们能做到刚才我说的那些,那我们就可以实施孙中山博士的三民主义了。既然你再一次问我,我就这样告诉你,我们必须毫不含糊地与我们的士兵同甘苦,共患难。他们吃什么,我们吃什么;他们穿什么,我们穿什么。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革命就会成功。”蒋回答说:“很好,我们必须这样做。”
美国开始支持蒋介石
1927年12月1日,对蒋介石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他与宋美龄的婚礼在上海的大华饭店隆重举行。
《时代》报道了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礼。宋美龄的名字第一次出现,以后她还多次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时代》的报道题为《宋氏姐妹》:两千名衣着豪华的中国人,上周在上海参加了蒋介石元帅的婚礼……
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结合,不仅仅是宋美龄与“征服者”普通意义上的结合,它的意义甚至可延伸到很多方面,因为新娘是完全西方化的“现代女性”。在中国,“宋氏姐妹”是着名的政治女性:大姐是孔祥熙夫人,孔先生家传尊贵,是孔夫子直系后裔。二小姐是享誉中外的夫人,是民族主义运动“神圣”的奠基人孙逸仙的遗孀。这场婚礼传递的一个信号是,国民党的实际一号人物蒋介石正谋求与英美缓和关系,而且,这个以革命起家带有某种黑社会性质的人物,正在与中国的资产阶级谋求联合。在此之前,蒋介石给人的印象一直是国民党中的左派,以排斥西方亲近苏俄而着称。美国的《芝加哥论坛报》在1926年11月23日的社论中就把蒋介石列为中国的激进人物之一(英文的radicals在当时是有特定指谓的)。《纽约时报》记者亚朋德(HallettAbend)后来回忆说:“1926年时的蒋介石是以从内心里讨厌所有外国人而着称的。”
《蒋介石传》作者布赖恩·克罗泽这样写道:1927年5月,上海政变后不久,蒋正式向宋美龄求婚。宋家为此召开一次家庭会议。宋霭龄赞成,宋子文完全不同意。尽管宋氏姐妹独立性很强,而且追求解放,但宋美龄已明确向蒋说明,没有宋母的同意,她不会结婚,而宋母并不怎么重视这一婚事。在这次家庭会议中大家还提出了很多问题。用中国社会的标准来衡量,作为一个士兵,蒋是属于传统的低层次的人,此外他结过婚——一次,或许还有一次——除非他可证明他已离婚。随后,宋夫人又听到了一些有关蒋介石生活中的其他女人的传言。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蒋不是基督徒。
导致蒋介石如此坚定地求婚的原因究竟是爱情,还是政治野心呢?或许二者兼有。胡霖(《大公报》创办人之一,该报普遍被认为是1949年以前中国唯一独立的报纸)在一次谈话中说:“蒋的婚姻是一次精心预谋的政治行动。他希望通过成为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宋子文的妹夫来赢得他们。那时,蒋也开始考虑寻求西方的支持。如果美龄成为他的妻子,他便在与西方人打交道时有了‘嘴巴和耳朵’。此外,他一直十分欣赏子文在财政方面的才干。但是,如果说蒋没有爱上美龄,那是不公平的,蒋显然把自己视为一名英雄,而在中国历史上自古以来都是英雄爱美人。出于政治的考虑,蒋可以做任何事。在当时的情形下,娶一位新妻子对蒋来说是非常合理的。”
这一场目的复杂的婚姻给蒋介石带来了很多东西。除了西方的承认,延续正统的承认,婚姻本身还为草根蒋介石收获了一个大家闺秀,因而产生足够的信心。1927年12月26日出版的当年最后一期《时代》报道说:
很快,到了1927年年底,一批称自己是国民政府的中国人在上海通过了一项与苏联决裂的决议。他们的领袖是原北伐军总司令、打下了半个中国的蒋介石,他说:“我欲竭尽全力实现国民党地区的和平,重整国民政府,提供充分军备以与张作霖(中国北方的统治者)作战,只有将他消灭,中国才会和平。”
蒋介石的崛起,不仅是依靠军队,依靠西方的支持,还因为他通过对苏俄的学习和借鉴,找到了一个凝聚人心的方式和架构,用主义和政党构建了他的忠诚体系,这一个忠诚体系使得他的力量更加强大也更加紧密,从而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在此之前,美国驻华全权代表马慕瑞于1926年6月派遣驻华使馆的二把手梅尔(FerdinandMayer)到南方考察,以掌握第一手材料,从而针对那里“惊人的事态发展”提出制定相关政策的推荐性意见。梅尔征求了美国驻广州、香港、汕头等地领事的意见,与所到之处的国民党官员进行了较广泛的接触。梅尔关于此行的报告长达六十页,最主要的建议是对南方政府采取更现实和更灵活的政策。梅尔提出一种双向新举措:美国一方面在维护条约的神圣性方面对南方采取强硬立场,但同时又取消对现存北京政府的承认以取悦南方,因为国民党方面肯定会认为这将削弱北方的力量。在阅读了这个报告后,马慕瑞敦促国务院“顺应”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建议美国应带头与英、日一起不承认北京政府,并且表态说如果英国和日本不支持,则美国应独立地采取此项行动。这样的行为,强烈地释放出一个信号,意味着美国对于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抛弃,也意味着中国格局将发生重大改变。
与蒋介石的迅速崛起形成对比的,是北京政府的不断衰落。此时的北京政府已过渡到战时格局,军阀武力当政,舆论遭到强奸,共和议会体制不再,一切已离早期设想的共和国越来越远。对于英美来说,北京政府偏离共和宪政所做的一切已让他们由衷地反感,已失去存在的必要,变得可有可无。列强们开始将目光和注意力转换到新生代的中国枭雄蒋介石身上,试图跟这个慢慢改变着的民族主义者进行合作。至于北京政府的临时执政张作霖,他们更愿意将他看作是一个真正的军阀,一个绿林出身的将军,一个没有现代民主政治意识的传统中国人。
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想象张作霖的孤独和郁闷了——西方列强彻底地抛弃了他,日本人也越来越对他不满;与此同时,对张作霖异常仇恨的苏俄正寻求对其进行报复。一直自诩为东北虎的张作霖此时就像一只被抛落在荒原的饿虎一样,只落得个四处觅食的局面。风雨飘摇中,觊觎他的,是不远处张着血盆大口的陷阱。
吴佩孚入川
1927年4月22日,吴佩孚五十四岁生日。细雨霏霏中,龟缩在河南巩城的他百无聊赖地提笔写下七律一首。一以贯之表露的是颇为矫情的悲天悯人:
民国军人皆紫袍,为何不与民分劳,
玉杯饮尽千家血,红烛烧残万姓膏。
天泪落时人泪落,歌声高处哭声高。
逢人都道民生苦,苦害生灵是尔曹!
吴佩孚写这首诗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新力量蒋介石意气风发指挥军队所向披靡之时。在此之前,由于吴佩孚不同意张作霖部南下抗击北伐,双方一度闹翻。兵强马壮的张作霖强行南下,接连与吴佩孚和靳云鹗的军队发生冲突,吴佩孚面临南北军队夹击的局面。节骨眼上,曾被吴佩孚罢黜的靳云鹗又与冯玉祥合作,众叛亲离之下,吴佩孚一下子成为孤家寡人。
进入1927年5月之后,形势对于吴佩孚来说更加逼仄了,冯玉祥的国民联军已从陕西进入河南境内,张作霖的东北军也进入河南,双方即将在河南展开大战。吴佩孚仅剩下一点人马,在双方的夹击之下变得岌岌可危,只得率卫队自巩县逃到南阳躲避。6月4日,国民联军方振武自襄城联合右路军孙连仲、南路军岳维峻又向南阳之吴佩孚残部发起攻击。吴佩孚部属于学忠部军心涣散,投诚奉军,情急之下,吴佩孚只得逃出南阳。无路可走的吴佩孚打电报给曾受过其重恩的四川督军杨森说:“我已无路可走,不论你允许与否,我都只有入川一途了。”当年被誉为“最有希望统一中国”之一代枭雄,此刻已落到了无家可归的惨淡结局。
吴佩孚是从鄂北的小路进入四川的,途经保康、秭归、兴山等地。这是一条荒僻山路,除了土匪,人迹罕至,艰难如三国时邓艾偷渡阴平。每过一个匪寨,吴佩孚就命向导持一张大红帖子,上书“吴佩孚”三字,高举手中。在豫鄂交界之灰店铺,吴佩孚的秘书长张其锽被土匪戕害。张其锽是吴佩孚的幕僚,当年吴佩孚那些煌煌电文,有很多就出自张其锽笔下。
有一天,吴佩孚和部下走到一个叫黄柏坪的地方,地面稍为宽敞,有几户人家。一个老道观有点面粉和绿豆,听说吴大帅来了,主人做了白面饼和绿豆汤来招待吴佩孚一行。饭还没有吃完,追兵来了,跟吴的士兵交上火。有人骑着马摇着一面白旗来送劝降信。吴佩孚嚼着饼,端着绿豆汤从庙里走了出来,接过劝降信看完后面无表情。参谋长蒋雁行在一旁流着泪说:“咱们也算对得起国家了,就是到南京去,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如果这样向外冲,必有大祸。”吴佩孚听后大怒,两只黄眼睛像冒出火来一般,用力将蒋雁行推开说,“跟我走,我不知道什么是大祸!”说罢不顾一切地顺着山路向前冲,送信人如木鸡一般闪在一边。吴佩孚一口气走了一个多小时,在半山腰稍停,等后面部队到达后,又沿着山路攀缘而上,是夜宿于山上。
吴佩孚一行历经千险终于在7月13日抵达四川巴东。杨森这时已受任国民革命军第廿军军长,吴佩孚此时还不知道杨森已易帜。15日,杨森携妻子暨高级将领数十人,由防次万县乘兵舰直驶巫山迎接到吴佩孚夫妇,然后乘舰溯江而上,入瞿唐峡,泊白帝城,至永安宫。
吴佩孚这次入川,艰苦万分,九死一生。受到惊吓最重的,是他的夫人张氏。张其锽之死,偷渡襄河的枪战,让张氏投襄河自尽的心都有了。张氏多次向吴佩孚表示,自己实在不愿如此担惊受怕,纵不求死,只愿削发为尼。劝告吴佩孚从此下野,不问世事,出家为僧以度晚年。泪随声下,吴佩孚为之动容。吴佩孚曾写道:“生死两难悲末路,夫妻垂老泣牛衣。”如今只有这两残句,未见全诗,大约因为词句太过悲惨,故意不留。吴佩孚还留有入蜀诗一首,可见英雄末路之哀,诗曰:
曾统貔貅百万兵,时衰蜀道苦长征;疏狂竟误英雄业,患难偏增伉俪情。
楚帐悲歌骓不逝,巫云凄咽雁孤鸣;匈奴未灭家何在!望断秋风白帝城。
还有《白帝城怀古》一首:
落日荒城剩野蒿,参天古木树旗旄。君臣遇合欢鱼水,禅术分明非俊豪。
祚运只教归在汉,河山那肯署为曹。江声不尽英雄恨,流到瞿塘浪涌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