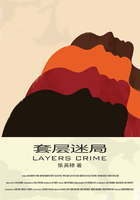就在急救室的门外还只有我一人之时,我想:要不要告诉她和他们真相?如果老太太救不过来,就没人知道了,是吗?有人看见吗?也许只有那条狗才闻到了空气中尚未散尽的硝烟。可如果救过来了呢?你是想她活还是想她死呢?一个快人快语的与我挺对脾气的老太太,她喜欢我,不用说,眼睛就告诉了我。我想报警,或者叫做自首更恰当些。狗娘养的子弹没弹头,一定是,或许他已不想要我的命了,只想毁了我的生活。是他还是她的主意?收买不了的杀手,为郑海生抱不平?还是甘为郑海燕去死的性奴?江童又打来电话,找不到急救室,越说越急,怪我说的不清楚,怪我没看好老太太。我想去接她,她厉声喝道:“不用!”电话便挂掉了。很快,她就出现了,头发乱得像散了捆的麦秸草,围巾一边短一边长,都快掉了地上。第一句话就是--“姥姥怎么样了?”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也说“不知道”?可不说“不知道”,说什么?没等我想好,她又说:“你不知道姥姥有心脏病?你都跟她说什么了?你就不能让着她点儿……”她问的问题没有一个我能答得上来,好在她的电话又响了,是她大舅的。用不了多久,这里或站或坐的将会全是她们家人,我在这里,多余。我不知道这里是不是还用得着我,我已交了钱,接下来也不知还要不要再交钱。可是,不管是死是活,交不交钱又有什么用呢?我是多余的,在死亡面前,我总是多余的,而谁,又不是多余的呢?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我想去厕所,不是拉也不是尿,就是想去厕所躲着,就像小男生躲避小女生的追捕。她打完了电话,我很是害怕。她的情绪稳定了许多,问我:“你是怎么搞的,连姥姥都照顾不好?”
“本来,我不想让她走的,我想让她留下来吃饭,可她就是要走,她的脾气你是知道的,我就给她送下了楼。这时,有人叫我,我回头,就是那个想要我命的人,他向我开了两枪,姥姥就躺在了地上。”
“那人呢?”
“跑了。姥姥身上没有子弹,我也没有。”
“你为什么不报警?”
“对,对,”我这才想明白,“我为什么不报警?为什么不报警?早干吗来着?”我掏出电话,拨了110,她冲上前来,要夺我手机,我没让她得逞,她说我疯了,我拦住了她,我说:“不,我刚刚明白!”这时,慌慌张张地跑进一个年轻人,江童管他叫哥,他又是疑惑又是鄙夷地看了看我,我自惭形秽地躲到一旁,趁她不注意,离开了。
我不知道老人是死是活。我去自首了。我把电话关掉了。
警察问我为什么当时不报警,我说当时没想好,其实是根本就没想起来。警察又问没想好什么,对啊,我没想好什么?想说明白这个问题,只好从头慢慢说起了。要不要从还没上学说起呢?我得好好想想。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我的事,除了江童的姥姥,因为她去世了。
警察去了胶州,找到了郑海燕,也去了我家。他们调查的结果,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我不知道的:郑海生的日记和课本是埋在他的坟里的,至于怎么到的那个人的手里,郑海燕不知道。
江童搬了回去。她妈骂过我,还想打我,被警察拦住了。老丁说我多余报警,我哥也这么说,我要不说,没人知道老太太的死跟我有关系。老丁够哥们儿,陪我说了好多话,我也感觉轻松了许多,他说这事情不怨我,我也渐渐如此认为了。江童一直都没理我,一个多月了。老丁说:“不着急,你俩不会因为这点事分手,她离了你,活不下去。”想和她说说话,也不接我电话,只好写下来,隔三差五发一封,还短信提醒过她,她也不回。去过她单位,也去过她家,老远的看着她,一个人,神情落寞的。她心中想的是什么,我不知道,只知道她离我越来越远了。
我想,或许江童再也不会理我了。我的噩梦才真正上演,我和她一起,只能毁了她的生活。翻来覆去,想了好久,也和老丁探讨过。最好还是决定,写封信,告诉她:结束吧,彻底分手吧,再不来往了!
没有打电话,只是发了封邮件,不知道她看了没有,其实,看与不看已无甚分别。
郑海燕对警察的解释是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她的所作所为令我越想越恼。我跟老丁说:“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秘密,以前总是躲避,迷惑,既而又是躲避,今天,必须解开。”老丁不想我走,可也没办法。我说:“放心,完事就回来。”他说:“相信你,不信我自己也信你。”奉承我,听得出来。
除了老丁,没跟任何人说。下了火车,直奔郑海燕家。半夜,敲了半天门,没人开。在附近找了家旅馆住下,一早,又来,还是没人。她的邻居开了门,说她家孩子得了白血病,现在去了青岛,也不上班了,好像连车都卖了。我给我哥打了电话,他又通过林聪打听到郑海燕的消息,说她跟她闺女正在青岛海军医院,她前夫也不管,因为一检查才知道,孩子不是他的。我没回家,因为我哥以为我还在北京。
在病房的走廊,她和大夫说着话,边说边哭。我一直观察着她,一直等他们说完话。大夫走了,她目送着大夫,也发现了我。我就这么站着看她,看她怎么看我。她擦干了眼泪,撩起凌乱的头发,悲伤的目光渐渐变得坚强,强装的坚强,不过是死前无望的虚荣。我就是这么看着她,没有一点动作,没有一丝表情的变化。最终,她向我走来,问我:“说吧,想怎样?”
“说说你闺女吧!”
“我闺女关你什么事?”
“关谁的事呢?”被我问得一时语塞,我说:“先说说你闺女吧,我身上还有点钱,看我能不能帮上你。当然不是为你,也跟你我之间的事没关系,跟郑海生也没关系,只是冲孩子。”她还是没说话,眼神里全是迷惑,我又说:“我说过的,你太不了解我。”
“你……”
“如果你连问题都没想好,就不要说话。你放心,我不会报复你的。我和你不一样。”
“你到底想干吗?”
“救你孩子命!”
“为什么?”
“为什么?你连这个……我操,”那一刻,我暴怒,二十多年来的怨气,自打认识了郑海生就积下了的,那一刻,全都化作了漫天的唾沫喷到了她脸上。我说:“你说,你懂什么呀?你一什么都不懂,你还有脸跟我这么多年没完没了!你懂什么呀?你拿什么跟我没完?操,你真逗!你这叫什么狗屁人生啊?人为什么活着,你懂吗?你懂个屁!你丫狗屄都不懂,还跟我这儿没完,你配吗?你弟弟跟我们之间的故事,你知道吗?他当年是怎么欺负刘长年的,你见过吗?连刘长年是谁你都不知道,你还他娘的……你就是他妈的……操,你妈!”我捏着脑袋,闭着眼,冷静了好久,她也一言不发。之后,我说:“我来呢,就是冲孩子来的。救你孩子呢,也不单单是为这孩子,也为我。救别人的性命,是救自己的灵魂。操,跟你说这个,你哪儿懂啊?赶紧吧,带我看看孩子。”
看她的表情,她是听晕了,也被骂晕了,目光是半信半疑的,脚步却是向前的。
小姑娘认出了我,很有礼貌,奶声奶气地说“叔叔好”。比上次见她,瘦了好多,脸色蜡黄。真要在幼小的年纪就离开人世吗?连自己的父亲是谁都不知道,谁又知道她的母亲是怎么编织她父亲的谎言呢?匆匆地来,匆匆地去,尚不及一只小麻雀经过的寒暑交替,又何苦来这一遭呢?
我问郑海燕,她说只好骨髓移植了,需要二十多万,或者三十万,或者四十万。我问她还有多少钱,她说八万多。真是不可思议,我还以为她会有几千万呢。我让她放心去配型,不够的钱我来出。她问我:“条件呢?”
“条件是:把孩子培养成一个正直的、善良的人。告诉她,努力地和身边的每一个人,相亲相爱。只是别他妈的乱来。”
很幸运,配型成功,我给了她十五万。接到钱,她才信了我,眼泪汪汪的,我说:“过去的恩怨,一笔勾销吧!”眼泪再也抑制不住了,像是大雪化后屋檐滴下的水。
治疗还算顺利,只是化疗时受了些罪,吃的饭都吐了出来。成功度过了排异期,又在医院做了一段时间的康复治疗。我又给了她十万块,她一番推辞之后,还是留下了。放下了钱,我们谁都没说话,她知道我在等什么,她说:“那个人确实是我找来的,可我没让他要你命。真的,不骗你。”
“你要我永远躺床上,半死不活,是吧?”
“真的对不起!”又是这句话,又是泪如雨下,我都感觉不到诚意了。
“向我开枪又怎么解释呢?”
“我从来就没命令过他向你开枪的。”
“你真的不坦率,我很失望。你当我是傻子,认为我比你傻,是吗?你给他的任务就是要我的命,能撞死我是最好,半死不活也接受了。就算警察破了案,大不了判个肇事逃逸,你再托托人,给他捞出来,或是少判两年。没说错吧?算了,算了,至于开枪的事我也不想深究了,你说没有就没有了,我情愿相信你。”
她连说对不起,又说:“打他撞你之后,我就再也不许他找你了。真的,拿我女儿的性命发誓。后来吓死老太太的事,事先我真的不知道。好多年没有他的消息了。”
“现在也没有吗?”
“没有。他的电话早就换了,本来我也不认得他。”
“不认得?”
“是潘强帮我找的。”
“潘强呢?”
“死了,死了好几年了。”
“知道他名字吗?”
“只知道他姓黄,像是本地人,可我从没在胶州见过他。”
“在别的地方见过他?”
“也没有,只见过他一次,好多年以前。”
“明白。还有,最初,你是怎么知道我在北京的?”
“一个杂志……”
“明白,没想到,好大发行量!《时代周刊》一样。”
“还有一个人。”
“谁?”
“范福林。是他跟潘强说,你很可能在北京。”
“为了让黑蛋儿放过他,所以他这么说?”
“对。”
“明白。乱七八糟的一堆人,见都没见过。他现在干吗呢?死了还是活着?”
“你最好不要去,他现在很厉害的。”
“后来再没听我哥和大聪说起这个人。”
“林聪可没法和他比。不过,他也只是说了那么一句话,跟小黄不太可能认识。”我一瞪她,她一怔,忙说:“对不起,我瞎猜的。”
“别再和我说对不起了。我不打郑海生,郑海生可能到现在还活着,要是肯上进,兴许还是个不错的歌手呢。到现在,常常想起他唱的歌,真的很好听。”
她又哭了。短短几个月,像是把一生的眼泪都哭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