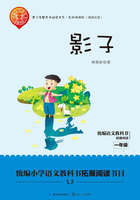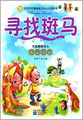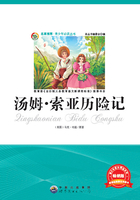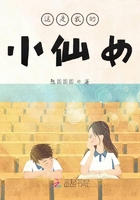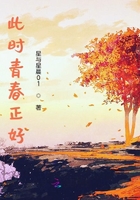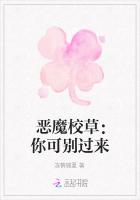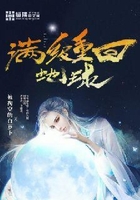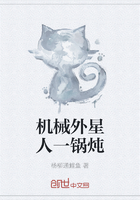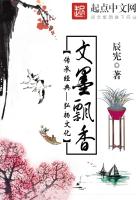1.学会全面识人
知人,慧眼识人,是智慧中最根本的内容。只有认清别人,才能妥善处理好与别人的关系,也才能做到正确地用人。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
孔子说,我不担心别人不了解我,只担心不能认清人。
樊迟在问老师什么是“知”(智)的时候,老师就说了两个字,叫做“知人”。也就是说,如果你懂得天体物理,懂得生物化学,或许你都不是拥有大智慧,你只是拥有了知识;真正的智慧有一个重要标准,就是面对人心,你拥有什么样的判断力。
在一个充满迷茫的世界里,真正深沉的智慧就是我们能够沉静下来,面对每一个人以及他背后的历史,能够顺着他心灵上每一条隐秘的纹路走进他内心深处的那些欢喜和忧伤,那些心灵的愿望。
那么,怎么样才能了解人呢?孔子告诉我们说,你看一个人,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这话什么意思呢?所以:所做的事情。所由:所走过的道路或所使用的方法。所安:所安的心境。廋:音sōu,隐藏、藏匿。
孔子说:“(要了解一个人)应看他言行的动机,观察他所走的道路,考察他安心干什么,这样,这个人怎样能隐藏得了呢?这个人怎样能隐藏得了呢?”
“视其所以”,从一开始你要看到他为什么这么做。看他做一件事不在于他在做什么,而在于他的动机是什么。
中间“观其所由”,你要看他做事的经过和他使用的方法又是什么。
最终是“察其所安”,一个人做一件事,什么叫结束或者没结束?不在于一件事情物理过程的终结,而在于他的心在这个结果上终于安顿了吗?有些事情完了,但人心仍然不安,意犹未尽,他还要做;有些事情没有完,但是有人可以说,雪夜访戴,我乘兴而来,兴尽而返,我到了朋友门前,我可以不敲门就走,因为我的心已经安了。
所以看一个人做事,不要看事情的发展过程,而要看他心理上的安顿。这就是给我们一个起点,“视其所以”,再给我们一个过程,“观其所由”,最后给我们一个终点,“察其所安”,那么就会“人焉哉”,人还往什么地方去藏起来呢?
当你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的分析,你说这个人还怎么能藏起自己的真实面目呢?这个人的心你弄明白了。
2.听其言观其行识人
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论语·公冶长》)
孔子说:“从前我听了一个人的话,就相信他的行为,现在我年纪大了,人生经验多了,听了一个人说的话,还要观察他的行为。这个改变,是宰予给我的启发。”
孔子自己增长了正确识人的一个经历,也告诉给我们一个正确识人的办法:听了他的话还要看他怎样去做,重在观察他的行为,而不仅仅听他说得如何好,还要看他做得如何好。
任何会言者都可以言,而言语能力强的甚至可以言得“天花乱坠”。因为,言只是一种声音而已,言之后,言已经消失,不论这种“言”“空洞无物”也罢,还是“言之确凿”也罢。我们又何必对自己的“言”那么认真。
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
孔子说:“君子不因为某人的话说得好就推举他,也不因为某人不好就否定他的一切言论。”
因为“有言者不必有德”。话说得好的人不一定品德高尚,所以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不能够只听他说得好便以为一切都好,轻易地去推举他。
另一方面,一个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好,甚至简直就是个魔鬼撒旦,但只要他说的话有道理,就应当采纳接受,而不应该以“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断然否定。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里说得好:“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还有一种情况是,一个人原来荣耀显赫,如日中天,“咳唾成珠玉,挥袂出风云”。说出的话都是金玉良言,句句是真理。后来星移斗转,风流云散,甚至身败名裂,原来所说的一切似乎也都成了反动言论,成了粪土,批倒批臭,任何人不得再说。阴差阳错,倒是免费给了那人以专利权。
这也是一种典型的因人废言。在圣人看来,不是君子风范。
3.不能用别人的好恶作为识人的标准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
子贡问孔子说:“乡亲们都喜好他,怎么样呢?”孔子回答说:“不可以。”子贡又问:“乡亲们都讨厌他,怎么样呢?”孔子回答说:“不可以。这两种情况都不如乡亲们里品德好的人喜好他,品德不好的人讨厌他。”
重点在于既反对好好先生(即孔子多次批评的“乡原”),又反对做事让所有人都不喜欢的行为。说这才是君子之道。
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
众人厌恶他,一定要仔细审查;众人都喜欢他,(也)一定要仔细审查。就是说一个人无论是受到大多数人的厌恶还是欢迎,我们都应该仔细分析他受欢迎或被讨厌的原因。深一层的含义是,君子应当明辨是非,不从众。
4.认清这一副嘴脸
借一双慧眼,拂去层层迷雾,请你认清这一副极易令你心动的嘴脸。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
孔子说:“花言巧语,一副讨好人的脸色,这样的人是很少有仁德的。”
“巧”字大部分是指高妙、聪慧、灵巧、美好之意。如《诗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甚至和“言”在一起时,《诗经》:巧言如簧。亦是指言辞巧妙动听,犹如笙中之簧。这些都是指好的事物。
“令”字亦是指好的、善的。《诗经》:如圭如璋,令闻令望。郑玄:令,善也。所以令色亦当指美好、和善的神色态度。
因此巧言、令色这两个字面上都是好的辞,为何在此180度大转弯,弃明投暗了呢?合理的推论是这里应该隐藏了一点言外之意。
现在看出来巧言令色四字所隐藏的言外之意了吗?对了!就是“一点也不诚恳”。所以孔子之意应为有目的、不诚恳、不合宜的巧言令色是不好的。
“巧言”一词在《论语》中还另外出现过两次,除此处及公冶长篇之外未出现于《论语》其他篇章。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
此二处应亦是与本章的巧言令色相同的,是指有目的、不诚恳、不合宜的巧言。
孔子所喜欢的,是简单、淳朴、实在,简称“简朴在”。
孔子所讨厌的,是巧舌如簧、溜须拍马、心口不一。
看得出,孔子对“巧言令色”的人深恶痛绝,用铿锵有力的语言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巧言令色”的人,很少能做到“仁”。孔先生是对学生们提出了警告,也是为后人敲响了警钟。你们要时时刻刻注意那些“巧言令色”的人啊!
孔子的警钟敲了2000多年,他的后人真的觉醒了吗?对不起,孔先生,也许真的让您失望了。2000多年过去了,“巧言令色”的人不仅没有消失,而且无处不在。欣赏“巧言令色”的人更是大有人在。“巧言令色”似乎成为人生的阶梯,成功的必修之课。
20世纪,一个叫李宗吾的人写了一本名为《厚黑学》的奇书。书中说,凡要成就一番事业的人,必须要具备两门功夫,一是脸皮厚,二是心肠黑。李先生写书的目的本是为了讽刺官场弊病,使国人从愚昧中猛醒。没想到,书一出版,竟成为人们争相学习的官场必读。厚黑二字竟被许多人奉为处世的经典、人生的座右铭。
李先生所说的“厚”与孔先生所说的“巧言令色”其实是一回事。请大家闭眼试想一下,一个花言巧语,一副讨好人的脸色,不正是一个典型的伪君子的画像吗?伪君子的显著特征就是脸皮的“厚”啊!
一般来说,脸皮厚的人抗击打能力比较强,对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较强。他们为什么要“巧言令色”?因为他们没有骨气,没有廉耻,没有自尊,他们以功名利禄为尺度,以利益得失为准绳。孔先生感叹了,这样的人“鲜仁矣”。
然而,喜欢“巧言令色”的却大有人在。很多领导只喜欢逢迎的下属,只欣赏满脸堆笑的表情。其实,在这些“巧言令色”的语言和表情下,隐藏的只有私心和利益。所以,直到今天,我们仍要牢牢记住孔先生在2000多年前给我们的忠告,时时刻刻小心那些花言巧语,满口颂歌,一脸媚笑的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