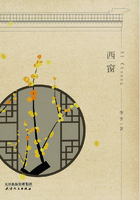杨杏园一肚皮的疑团,恐怕连何剑尘夫妇,都为这个事怪他,无精打采的走了出来。刚一出门,顶头碰见一个人往里走,他看见杨杏园,却请了一个安,往后退了一步,然后站住了。杨杏园一看,原来是刘厨子。这人原是何剑尘家里的老佣人,后来改了行做厨子。便不在何剑尘面前当差。有一次,刘厨子掉了事情,曾求着杨杏园写了一封信,在一家俱乐部包饭,很赚了几个钱,所以他见了杨杏园十分恭敬。杨杏园便问道:“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刘厨子道:“现在闲了好几个月了,今天是特意来见何先生,打算请他老人家赏一碗饭吃。”杨杏园道:“我听说你都发了财了,还没有饭吃吗?”刘厨子含着笑容道:“没有的话。还想请您提拔提拔呢。”杨杏园道:“你要是找何先生,你可空跑了,他和他太太都不在家呢。”说着自上车子去了。
刘厨子碰不着何剑尘,十分懊丧,心想从北城老远的跑了来,不但找不到机会,连人也会不着,真是倒霉。这里到草厂胡同小翠芬家里不远,不如到那里去会会老李,也许碰着什么机会。主意想定,便到小翠芬家来。这老李搬了一张方凳靠着大门,口里衔着旱烟袋,手里拿着一份《群强报》,看小说讲演聊斋,正自有味。刘厨子走上前便喊道:“李头儿。”老李一抬头,看见是刘厨子,忙站起来道:“大哥!您好?”刘厨子也答应道:“好。”老李道:“大哥你是不常到城南来的……”一句话没说完,只听见呜呜的一阵汽车喇叭响。老李说道:“余老板回来了。”车到了门口,停住了,汽车夫打开门,走出一个二十来岁的少年。这人身穿宝蓝大花统霞缎夹袍,外套黑缎子小坎肩,胸面前,一排红亮珠扣子,头上戴一顶瓜皮帽,红绒球帽顶。帽子前面,安了一片带点绿色的玉石,玉石上面,又有一颗圆圆的红宝石。这人瓜子脸儿,漆黑的一双眉毛,眼睛虽然睫毛很长,可是黑白分明,十分流动。厚厚的嘴唇,却也白里翻红,一说话,露出嘴角上两粒金牙齿。他走身边过,脸上的粉,雪白的一层,衣襟上的香气,走动起来,往人鼻子里直钻。他下了汽车,走进里面去了。那汽车里面,却另外有个少年,没有下车,就坐着汽车走了。刘厨子看见,便问老李道:“刚才进去的这人就是余老板吧?”老李道:“是的。”刘厨子叹了一口气道:“咳!人要发财,真是料想不到的事。当他在科班里的时候,我们常到后台去玩,他穿着一件蓝市布的旧棉袍子,清鼻涕冻得拖到嘴边,很是可怜,我们还买糖葫芦送给他吃呢!那个时候的小翠芬,和现在的小翠芬,真是天上地下了。”老李道:“天下事,就是这样没准。你还不知道呢,昨天晚上在常小霞家里推牌九,三条子牌,就输了一千多。做官的,几个有他这样阔?”刘厨子道:“什么?三条子牌,就输一千多么?那末,半个月的戏份,都白扔了。”老李道:“他自己哪有那些个钱输?自然有人替他会账啦!”刘厨子再要问谁替他会账时,小翠芬的包月车夫王二,拖着一辆空车,慢慢的走过来,他们就停住了话没说。老李道:“你怎么不拉车进来,就停在门外头?”王二道:“还要走啦,拉进去做什么?”李老道:“拉到哪里去?”王二道:“听说常老板,今天晚上给咱们老板邀头,就要上那里去,恐怕要闹一晚上呢。”老李道:“刚才不是常老板送咱们老板回来的吗?为什么不一直去?”王二道:“常老板送咱们老板回来,就要去接胡春航总长,所以咱们老板,不能一直就去。听说咱们老板,还得回来换衣服呢。”刘厨子一边听了,记在心里,心想他们唱旦角儿的,都能和总长来往,我不如在这里面想想法子,也许能够碰得着一点儿机会。主意想定,便只管和老李王二两人,谈了下去。
过了一刻儿,小翠芬又出来了,果然换了一件葱绿色的长袍子,腰上还系了一根白色的绫子腰带。一脚登上车坐着,先踏了几下车铃,当当的直响,王二扶起车把,飞也似的跑,不一刻工夫,就到了椿树上九条胡同常小霞家里。这里是小翠芬极熟的地方,他下了车,一直就往里走。走到会客室里去,只见一个老头儿在那里打电话,正是胡春航,他笑道:“你来吧?今天虽是绮余的主人,其实是替翠芬凑个小局面,不好意思不帮这个忙,公事不要紧,留着明天办得了。”胡春航把电话挂上,一回头看见小翠芬,笑道:“你刚来吗?今天的《双铃计》,你演得真好,现在见你,我还有些怕你。”小翠芬道:“干吗怕我?”胡春航道:“你在台上,活像一个又漂亮又狡猾的泼妇,真教人疼又不是,恨又不是。当你在茶铺子要钱的那一场,我要是掌柜的,我也要被你驳倒呢。”说到这里,常小霞走进来了。他穿着雨过天青色物华葛袍子,外套电光绒马褂,四周滚着金边。他的衫袖口上,露出一路花边,大概是汗衫袖子上镶的。他下面穿着鱼白色丝光袜,尖头花缎鞋,轻轻的走了过来,在小翠芬肩膀上一拍,笑道:“你这孩子,怎么也不做声,就跑进来了。”小翠芬回头一看,拍着胸道:“可吓着我了。二爷,可得管管他,越大越胡闹了。”胡春航笑道:“你的胆也太小了,这样拍一下子,就吓倒了吗?”说着,伸手在烟卷筒子里,抽出了一支烟卷,在茶几上顿两下,常小霞连忙找了一盒火柴,擦着了一根,俯在胡春航身边,给他点烟。胡春航瞅着常小霞的脸,笑道:“你瞧,回来这半天,脸上的粉还没有洗掉。”常小霞瞟了胡春航一眼,说道:“你别瞎说了,我脸上就是这个样子。我还要问你的事呢,前天我荐给你的两个人,你发表了没有?”胡春航道:“这几天,部里正在裁员,怎样好添人?过几天再说罢。”常小霞道:“那不行,你非发表不可,今天你就得发表。”胡春航道:“我今天晚上,不是在这里打牌吗?我怎样发表?”小翠芬插嘴道:“那也不要紧呀,打个电话到部里去,叫他们发出公事去,那还不行吗?”胡春航笑道:“孩子话!”说到这里,早听到门外汽车噗噗哧哧的响。一会儿一个人嚷进来道:“春航!春航!你好快活,在这里打牌。”看时,卢南山带着两个马弁一直冲了进来。小翠芬认得他是陆军总长,便走上前,斜着身子往下一蹲,请了一个安。卢南山走进屋来,两个马弁看见两个小旦在这里,他们就退了出去。卢南山却弯着腰笑嘻嘻的上前,将小翠芬的肩膀一拍道:“你这孩子今天穿得这么漂亮。”常小霞也就立刻走过来招呼。卢南山道:“小霞呀小霞,现在胡春航硬给你孝顺得糊涂了,一从部里出来,就到这里来了。他的太太可不是容易说话,你仔细挨打。”说着挽住常小霞的手,拉他同在一张沙发椅上坐了。常小霞道:“胡总长到我这里来,太太就不答应,他现在天天晚上到胡同里去,怎样太太就不问呢?”卢南山用手一摸胡子,对胡春航笑道:“春航,你听见没有?他话里有话,还要吃点醋呢。”胡春航靠在椅子上,却只是微笑。坐了不到一刻钟,交通次长孔亦方,财政次长钱青化,烟酒督办金善予也来了。胡春航道:“人已经够了,我们就动起手来。我明日一早还有事,牌不要打得太晚了。”这时,常小霞把他们又引到一间精致些的屋子里去,这里共是两间。外面是一个小小的客厅,四周陈设了上等外国器具,那也不算什么,只是里面那个屋子,有一张铜床,辉煌夺目。床上挂着湖水色秋罗帐子,用银帐钩挂着,床上面铺着四五寸厚俄国虎斑绒毯,叠着一床水红和一床鹅黄色的绸被。四个蓝缎子金线绣花的鹅绒枕头,放在两头。床中间,端端整整放着一大部书,两截竖着的洋钱,却是人料想不到做什么用的。常小霞走上前,将那书函打开,翻过来一看,原来是套木制的烟家伙,里面烟灯,小油壶,剪子,烟签子全有,而且全是银制的。他再把那一截洋钱拿在手里一扭,翻过来一看,却掀出一个盖子来。原来这一截洋钱,是个模型,中间是空的,只有上面的盖,和下面的底,是两块真洋钱,中间却是一个特制的烟缸子。常小霞将烟家具摆好,便问哪位玩一口?都说:“不必!我们就打牌罢。”说时常小霞的兄弟常幼霞,捧着一盒象牙骨牌进来。他穿着一件绛色的袍子,周身滚着白边,也没有戴着帽子,脑袋上前面梳了一蓬刘海,后面披着半截漆黑的头发,长长的瓜子脸儿,溜圆的黑眼睛珠子,倒很像一个旗装的女孩子。卢南山看见,一手扯了过来,便搂住在怀里,把鼻子凑着常幼霞的脸,一阵乱闻,口里嚷道:“那里跑来这么一个小姑娘?好香的脸。”常幼霞挣扎不脱,涨得满脸通红,手一撒,把捧着的牙牌,哗啦啦一响撒了满地。胡春航笑道:“小孩子害臊,你就别和人家闹罢。”卢南山只当没有听见,依旧搂着不放。常幼霞趁他不防备,却一扭身子跑了。卢南山拍着两只手,哈哈大笑。这时早有小霞家里的用人,将骨牌捡起,放好在桌上。胡春航便问道:“谁推庄?”卢南山道:“自然是你推,我们随便押一个方向。”胡春航对孔亦方道:“亦方先生推几条子试试看。”孔亦方笑道:“这一个月也不知什么缘故?我的手气总不好。前次在钱次长那里推牌九,摸了一副天杠,要吃一个通,偏就碰到胡总长一对五,吃了两家,还赔出去一千八,推庄我是不敢来。”胡春航笑道:“那回我只赢五千块钱,结果一个也没落下。”说着对常小霞指道:“给他买了一辆车子了。你今天何妨再摸一副天杠?”又笑着伸手拍了小翠芬的肩膀道:“也许孔次长送你一辆汽车呢。”孔亦方笑道:“若是那样送汽车,就送一百辆,翠芬也不见我的情呢!”小翠芬笑道:“我就不是那样想,随便哪个送我一辆汽车,在这儿的人,我都见他的情。这话怎说呢?因为没有您五位,牌就打不成功,打不成功,就没有人赢钱送汽车给我,所以说起来,都是有人情的。”卢南山笑道:“伶牙俐齿,你瞧他这一张嘴。”大家都说:“这孩子真会说话,怪不得《双铃计》,他演得那样活灵活现。”胡春航走到桌子边,用手抚摩着牙牌,说道:“谁推庄?快来,不要谈天了。”大家都说:“还是胡总长推罢,真是胡总长输得太多了,我们自然有人接手。”常小霞道:“胡总长在我这里耍钱,没有输过。”金善予道:“你总是帮着胡总长。”卢南山道:“这才叫疼不白疼,像刚才我疼一疼幼霞,就一撒手跑了,那才是白疼呢。”说着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