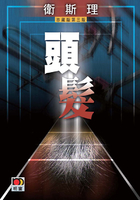1
鉴真从岭南往北行走,率领弟子们经吉州,又登上庐山东林寺,再走陆路到江州(今江西九江),然后顺江东下,终于抵达润州江宁(今江苏南京),住进了瓦官寺准备过江返回扬州。
江宁县到处都是伽蓝,现存的江宁寺、弥勒寺、长庆寺、延祚寺,都是三百多年前梁武帝时代修建的,座座气象庄严,建筑精美,雕塑细致。瓦官寺也是那时候的建筑,寺内登宝阁,阁高二十丈,微有倾损。传说有一夜,风雨雷电,似乎要摧垮这登宝阁,结果天降四位天神来到阁的四角扶持,使登宝阁安然无恙。天亮后,人们在阁的四个角上发现了天神留下的印迹,随后在四个角上塑造了四位天神像以示纪念。
鉴真返回的消息不胫而走。恰好,大弟子灵佑正住在江宁的栖霞寺,师父第五次东渡失败他已有所闻,内心万分痛惜却因不知行踪而无能为力。虽然他曾经策划了扬州寺庙的长老联合上书官府,以阻止鉴真东渡的事件,最后以自己站在门外忏悔六十个夜晚而取得鉴真的原谅。这一次师父为时三年,走了半个中国才得以返回,他老人家又是经历了怎样的痛苦呢?想到此他一刻也不能怠慢,从几十里外火急赶来迎接师父。
当他走进瓦官寺,正好看到鉴真在法进的搀扶下迎面走来。
“师父!师父!”他喊叫着扑了过去。
鉴真停住侧耳细听。
灵佑禁不住哽咽难语:“师父!”
鉴真听出声音,惊异地问:“是灵佑?灵佑,是你?”
灵佑一下五体投地扑倒在师父面前,顶礼膜拜,把脸贴在鉴真的脚上,痛哭流涕:“是的,师父!我是灵佑呀!……”
鉴真弯下身子用手摸着灵佑的头,表情酸楚。
灵佑悲泣道:“自从师父离开崇福寺远渡日本,我就以为今生再无缘仰见师尊,聆听训诲了,想不到今天还能在此相逢。真像戒灯重明,驱散了笼罩在人间的阴沉之气啊!”
鉴真拉起灵佑,叹道:“戒灯可以重明,而我的眼前永远是一片黑暗了。”
灵佑像遭雷击一样,全身剧烈抖动一下,他抬起头仰视师父,只见师父一脸倦容,双眼已没有一点往日的神采。
“啊!师父,你眼睛怎么了?怎么会这样?”
鉴真平静地告诉他:“荣睿、祥彦都相继迁化了,普照也走了。我的眼睛失去光明,这也是佛祖对我的考验吧!”
灵佑悔恨地:“师父,是我害的你呀,当初要不是我纠集江淮诸寺三纲,把你从旅途中硬拉回来,也许您早已顺利地抵达日本,了却你的夙愿了,也就不会受这长达三年的流离跋涉之苦,两位师弟也不会迁化,师父也不会失去双眼了,师父呀,现在一切都来不及了,是我害了你呀……”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不要再提它了。”鉴真伸出手摸着灵佑的脸、肩膀,亲切地问:“灵佑,你现在好吗?”
灵佑含着泪点头:“我现在住持栖霞寺,听说师父归来,特意赶来江宁请师父到寺里住些天。”
“好哇,栖霞寺以三论宗高僧慧布、慧峰曾居住而闻名。”
灵佑补充道:“师父,你的弟子睿光、希瑜、昙仳等人亦曾经在寺里居住过。”
“是吗?那我与栖霞寺有缘了。”
就在鉴真与灵佑会面的时候,思托却在一个寺庙里见到陆达。因为江宁的寺院古建筑多,其绘画和雕刻也独具特色,鉴真便让弟子们去四处观摩,不放过每一个学习的机会。思托本来就很活跃,凡听说有特色的地方都要跑到,边看边画在纸上。
那天,他正在一座古庙里观摩,不小心与一位男子相撞,刚要道歉,两人都惊呼起来。
“是思托法师?”
“陆达兄!”
两人禁不住拥抱在一起。
陆达身背包裹,一副行脚打扮,他迫不及待地问:“你怎么会在这里?师父呢?”
“师父在瓦官寺。”
陆达说:“我后来听说你们的船漂到了南面的岛上,也听说周画师他遇难了。这是真的吗?”
思托点头:“是真的。”
陆达悲痛异常:“唉,因为是传说而不能确定,周画师遇难的事我也没有告诉琼花,但她也知道你们没有走成,在南方漂流,她还抱着希望等父亲回来呢。”
“陆达兄,你知道吗?我们在回来的路上,荣睿、祥彦也先后迁化了。”
陆达一把抓住思托,瞪大眼:“你说什么?荣睿和祥彦也……”
思托点头。
陆达如五雷轰顶,呆若木鸡……
陆达又听说鉴真双目已经失明,执意要随思托到瓦官寺去拜见师父,不想师父已被灵佑请到栖霞寺安歇去了。他不再犹豫,迅速坐船过江,此刻,他特别想见到琼花,虽然周士杰在临走时把女儿许配给了他,但他知道琼花是个只要钻到牛角尖就出不来的痴女子。自己与她有情无缘,也是人间“求不得”之苦。他索性放下情缘,真诚相待,两人渐渐地倒像是兄妹般往来了。想到她的父亲和心仪的表哥都先后离世,留下她一个人在这个世上,陆达就禁不住悲从心起,他要去告诉琼花这不幸的消息,让她在见到鉴真的时候,免得过于悲痛。
2
陆达来到扬州琼花的住宅,侍女秋莲前来开门,殷切地问道:“陆达君,你回来了?”
“回来了,小姐在吗?”
“在。”
琼花在绣坊指导着几个绣女刺绣,她一身素装,见陆达来,忙出来将他迎进客厅。
“达兄几时回来的?”
“刚从江宁乘船过来。”
“你走这一趟远门有半年多吧?”
“半年多了。”
琼花注视着他:“你怎么了?”
陆达欲言又止:“琼花……”
琼花疑惑地望着他。
“琼花,我在江宁见到思托了。”
琼花惊喜地跳了起来:“真的?师父他们都回来了?”
陆达点头。
“见到我爹了吗?”琼花急切地问,她见陆达没有表示,上前一把抓住陆达的胳膊,声音颤抖:“你没有见到我爹?”
“你爹……我师父他……他在南海的岛上遇难了。”
琼花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你说什么?”
“他已经过世三年了。”
琼花像被电击般呆住,紧紧抓着陆达的手无力地垂了下来,她的意识还没有从重创中醒过来,陆达又给了她重重的一击。
“祥彦他……前不久也在吉州迁化了。”
琼花再也承受不起这连连的打击,她像一截木桩般直直地倒了下去……
琼花再醒来的时候,陆达在家里已经给父亲周士杰和祥彦设了灵堂。
她来到堂前跪下,想到父亲临走时苦心将她托付给陆达;想到祥彦归去时魂魄不散与她梦中告别时的情景,她犹如万箭穿心,放声大哭……
晚上守灵,陆达劝琼花去歇息。琼花起身来到佛堂,从案上拿起血书的《心经》,打开来低头看着看着,耳旁仿佛听到祥彦诵经的声音:
“……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色、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垂;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罣碍;无罣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她跟着祥彦的声音轻轻诵读,读着读着佛祖的话就像甘露般一滴滴洒进她的心田,失去亲人的伤痛感也仿佛渐渐修复,她的心变得异常平静通透。
阿弥陀佛。她知道她该做什么了。
第二天一早,陆达没有见到琼花,四处找寻,秋莲才吞吞吐吐地告诉他小姐去了尼姑庵。问去做什么,秋莲说:“小姐不让我告诉你。”
陆达知道坏事了,他疯了般向尼姑庵跑去。可惜,他晚来了一步,他看到琼花跪在殿堂的地上正在接受一老尼姑剃度,她原本秀丽的长发一缕一缕飘落在地上……
陆达转身走了出来,他虽然能理解琼花的心境,但也很生气,这么大的事情,她竟然不和他商量一下,就自作主张削发为尼了。
再见到琼花时,她已是比丘尼的打扮。
“琼花!”
琼花纠正道:“我的法号叫智首。”
陆达检视她的双眼:“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达兄,父亲为弘法客死南海,我心也没有任何牵挂了。”琼花从衣袖里取出祥彦送给她的《心经》递给陆达:“这是祥彦临走时送我的《心经》,是他用血抄写的。”
陆达接过来看,颇为震惊。知道这是琼花最为珍视的经文,因为她从来没有给他看过。
琼花说:“祥彦往生的时候我已有预感。从那以后我天天都要读这部《心经》。后来,我突然领悟到了祥彦的良苦用心……他是在用心血将我这迷惑的心灵度出烦恼的世界。”
陆达看着她平静的表情,知道出家为尼是琼花必走的人生之路了。
鉴真在栖霞寺住了几日,灵佑便护送他过江入新河岸,住进了既济寺。八年前第一次东渡,这里是存放粮食物品的地方,可惜如海告官被查,荣睿也被捕役从池塘里掳走关进了监牢。如今,荣睿的骨骸已永远地留在了端州,而东渡的僧人们却又回到了起点。鉴真触景生情,难以入眠。
第二天,扬州城举行了重大的庆典,迎接归来的鉴真大和尚。古人记载:“江都道俗,奔填道路,江中迎舟,舳舻连接。”真是盛况空前。
在夹道欢迎的人群中,不时有人冲到鉴真面前叩拜,诉说对他的怀念。琼花也从尼姑的队伍里冲出来,拜倒在鉴真的脚下,大声喊道:“弟子智首拜见师父!”
鉴真安祥的表情顿时惊异了:“智首?听声音是琼花……”
琼花控制不住地抱住鉴真的双腿,大哭:“师父……”
鉴真眼里涌出了泪,他伸手去摸,再也摸不到琼花的一头秀发了。
灵佑、思托、法进等人不由得为之动容……
至此,鉴真从南海振州再辗转回到扬州府,为时三年,行程万里。所经州县,立坛授戒,有求必应。他外秉威仪,内求奥理,把《律抄》、《轻重仪》、《羯磨疏》等律学经典向诸州僧众反复宣讲。即使在双眼失明看不见文字的情况下,也靠着过人的记忆一丝不苟地传达出去。讲授之余,造立寺舍,供养十方众僧;造佛菩萨像,也是其数无量。
虽然第五次东渡看似以失败告终,但是鉴真随缘弘法,以他坚强的意志,慈悲的心怀,为人们拨亮心灵的明灯。一千多年过去了,在他留下足迹的许多地方,人们仍然保留着供奉他的寺庙;在海南岛,当代人为这位伟大僧人和弟子们塑造的巨大群雕屹立在三亚的海边,让他的精神光照千秋……
3
唐天宝九年,在大海彼岸的日本,孝谦天皇发布诏书,任命了第十次遣唐使团。在唐天宝十年春天,从难波津出航的四条大船和五百多名乘员,七月在明州平安登陆。秋末,遣唐使团进入长安。
正是中秋节,长安外宾下榻的四方馆外灯月交辉。
街上,西域人在表演杂技,波斯艺人们跳着舞蹈;还有舞剑的、击鼓的应有尽有。他们在向来大唐的各国使节和商人、游人展示着技艺。
各种小吃和小商品也都向游人招徕着生意。
遗唐大使藤原清河和他的部下随从们在晁衡的陪同下在街上任意行走,赏月游玩。大使第一次来大唐,眼前这繁华的景象让他不禁连连赞叹:“八方来客,歌舞升平。大唐真是了不起啊!”
副使大伴古麻吕对晁衡说:“自从皇帝召见以后,阁下奉旨陪我们四处旅游参观,这些日子我感受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目不暇接。”
副使吉备真备是第二次来大唐了,看到初来乍到的大使们对什么都那样惊惊乍乍,欣喜若狂,心想,你们看到的大唐仅仅是冰山一角啊。
晁衡见到吉备真备,感慨万千:“吉备君,当初我们一起来大唐留学,你回去已经是十八年了。现在又重游故地,而我还在这里苦苦思乡呢。”
吉备真备一笑,说:“那是大唐天子对你恩宠有加,不放你走啊。我还记得你当时写下了四句感伤的诗哪!‘慕义名空在,偷忠孝不全。报恩无有日,归国定何年?’”
“唉,有什么用?还是回不去啊。”
“阿倍君现在结亲长安,又身为唐朝的重臣命官,立功友邦,也是为日本争光啊!”
“可我年龄越长就越思念故乡啊!”
走在一边的藤原清河说:“阁下客卿唐朝,承恩多年。如今我国师唐兴邦正需大才,理应再请唐皇恩准东归返航。”
晁衡一听此话,又来了信心:“我一定会上表陈情,与大人同船回国,一报天皇。”
一直安静守候在明州阿育王寺的普照得知日本遣唐使船到达明州,兴奋得不能自己,不顾一切地跑到海边去观望,远远看到遣唐使的大船,眼泪就禁不住往下流,他真想扑到跟前去相认,可是看到遣唐大使及随行官员们,一个个锦衣华服,威风十足;那些随船而来的年轻的留学生、学问僧也都衣着亮丽,朝气勃勃。而自己呢?一个半老的学问僧,穿着寒酸,在大唐十八年一事无成。还有什么脸面迎上去说自己的来历呢?看着同胞在唐朝官员的热情接待下乘坐一辆辆华贵的马车离开码头,他自惭形秽,心想在那些年轻人的眼里,自己的样子恐怕就跟当年到长安,见到拼命抄写经文的智行时的感受一样吧。
遣唐使船的到来,让普照看到了请师父东渡的希望,他打消了在明州拜见遣唐使的念头,更何况在这里他也没有与他们相见的机会,因为遣唐使们很快就北上了。普照决定启程,他要在京城面见日本大使,希望遣唐大使能以日本官方的名义亲自邀请鉴真大师去日本传法。
前去长安的路并不好走,普照舟车兼行,一路化缘,数月后才风尘仆仆赶到京城,住进了早年修学的崇福寺。
这一天,他走在街上,斜对面走来一位四十多岁的僧人不停地扭过脸打量着他,普照也注意地看着他,终于认出他是道航。
道航先开了口:“请问,是普照师兄吗?”
“道航法弟!”普照忙向道航施礼。
道航更为惊讶:“你们还在大唐?”
普照点头,百感交集:“还在……”
道航一把拉住普照的手:“荣睿呢?”
普照的眼圈先就红了:“荣睿他……已经葬骸于端州。”
“阿弥陀佛!”道航念了一声佛后,沉默片刻又问:“我师父呢?”
“听说他已经回到了扬州。”
道航半天说不出话。他带普照来到一家茶庄,坐下细谈。
“师父东渡几次失败的事情我也有所耳闻,但没想到是如此艰难。唉……”道航感叹着:“当初把他介绍给了你们,而我却因为一次失败逃回了长安,让他老人家受了这么多的磨难,我此生已无颜再见师父了……”
普照也是一脸惭愧,他说:“第五次失败后,我也离开了师父。因为我不忍心再看着师父为东渡日本而受苦受难了。我想只要我一走,师父就会没有那么大的压力;跟随他的弟子们也会回到各自的寺院里去了……可是,离别的那一刻,师父他拉住我的手说,不管遭遇什么,他东渡弘法之志不移。”
道航听了,感慨万千:“师父他……真是常人难以比拟啊!”
普照点点头说:“我这次赶来长安,就是要面见大使。我和荣睿的心愿没有了却,我要请求大使通过正当的外交途径,正式礼聘鉴真大师东渡日本。”
道航一怔:“哦?你还要请师父去日本吗?”
“对。我遗憾的是,如果遣唐使船早来十年,师父也就不必经历这么多天灾人祸,荣睿也就……”
“是啊,世事难料……不过,你想过没有?师父已经不是当年的师父了,那一年,他才五十五岁,现在十年过去了,师父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且双目失明,东渡之事恐怕也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普照的口气不容置疑:“我了解师父!他不会放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