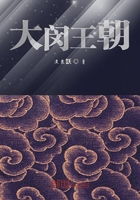旅途生活,在我的印记中是寂寞的。可这回行脚于陕北高原,使我感到特别有意思。时而盘旋于馒头似的山岭,时而跌落于深幽的沟堑,时而长驱于狭窄的川道,其变幻无穷,景致异迥,令人目眩。
在陕北高原上,除了偶尔从头顶掠过的客机,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恐怕就数汽车了。三边的盐,延长的石油,瓦窑堡的炭,还有塞上的毛皮,已从一部分脚夫赶的毛驴、骡子、骆驼的背上,转移到了各类牌号的汽车上。而打远赶集、串亲、逛县城的庄稼人和远途的旅人,就指望往返还算频繁的公共汽车了。
远路来的旅人,随便问起要去的路,就会有人热心地详细指点。偏僻山沟里的人,头一回搭上车,不免感到新奇,眼里闪着惊喜的光。有时显得冒失,甚至不知道怎样打开车门,同车人的取笑也总是善意的。一位披老羊皮袄的考人,买票的动作很缓慢,一双青筋暴鼓的茧手,从内衣里掏出布包包,仔细地打开,笨拙地数着钱,颤巍巍地递过去,然后坐在行李上默默地抽旱烟袋。
陕北高原有些地方人口较稀少,长途汽车站与站之间的距离较长,为了便民,操着陕北口音的司机,喜欢常停下车来“捎脚”。有的是相识的,有的则是陌生人。只要车子没有超载,凡人扬手招呼,司机都乐意停车。似乎,沿途处处是站,处处有相识的亲人。
这天,我坐的汽车沿途停了三次。
山岭上,一个拦车的老人挡住了车,向背洼洼里直吆喝,—个年轻婆姨许是老人的儿媳,抱着娃娃跑来上了车。老人的老伴儿也跟着跑过来,手里扬着红头布。车开动了,不料老人的老伴儿又从小路上跑来,手里扬着一个小包裹,于是车又停下。等老大娘把包裹递给车上的儿媳。当拦车老人同老伴儿招着手,为走娘家的儿媳送别时,感激司机的神情在脸上闪着。
车子刚趟过一道滚水桥,抱着两条洇润的辙印又停下了。司机下了车,帮一个提着手扶拖拉机轮胎的后生上了车。是拉化肥的手扶拖拉机半路抛锚了,这后生是急着去镇上修理的。
后来,又有一个衣着整洁的年轻女人挡车。上车后,兼管售票的司机问她去哪儿,看去挺文雅大方的她,却“呀呀”地说不清话。噢,是个哑巴。她把手伸到靠门口的后生面前,在掌心比划了两个字,原来是去佳县的。司机笑着,一手操着方向盘,一手接过转递来的车票钱,答应到站给她补票。哑女似乎听懂了,嬉笑着,揩着鬃角的细汗,掏出苹果让车上的人们尝鲜。
沿途车子停得多了,有的旅客会发出埋怨的叹息,可司机总解释着,尽可能给大多数乘客以方便,准时到达各站。大多数旅客不仅能体谅这种情况,而且对司机同志从内心深深地赞许着。谁能没有过候车的急切感受呢?
车子又飞上高高山岭,贴着山脊在疾驰。脚下,是质朴、敦厚的黄土,是贫瘠而宝贵的土地。远处,黛色的、褐色的、晶白的公路时隐时现,细练般萦绕在波谷浪山之间。汽车变得小了,轻舟似的浮荡着,浮荡着。
《人民日报》一九八二年二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