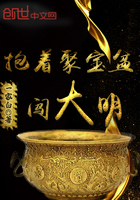第五十三章杀戮与点化
师徒两人行至东门,便被守卫的清兵拦住了他们,任凭罗浩宇怎样解释,清兵们拒不让他们通过,双方正在僵持,冷不然范一统从身后冒出来了。
“哟!是柳老前辈呀,想到山上去转转吗?”
柳一江冷眼一扫,理也没范一统一下。
范一统一看就知柳一江师徒不买他的帐,对此他大手一挥,叫来一个清兵说:“这老少二人是总兵大人的朋友,不是反清复明会的人,放他们走吧!”
几名清兵听了范一统的话,就放他们出了东门。
而柳一江急着去看望老朋友,顾不上与这条恶狗纠缠,拉着罗浩宇走了。
范一统拄着拐杖,暗暗紧跟在他们身后,一直望着柳一江师徒朝龙潭寺那条路走去,他点着头,自言自语:“明白了——是去龙潭寺找那老和尚。”
回到镇上,天已经黑下来了,范一统无精打采地走进一家小酒楼,点了一盘牛肉,二两花生,半斤白酒。
喝着、喝着、他自己喝红了眼珠子。
这酒、也是火——仇火,恨火,欲火,同时在他狭隘的胸膛里翻滚着,也许,只有在此种情况下,人才会露出原形。
范一统他在伪装,伪装下的他变得更加疯狂了。
他怀恋蜀香园里的阿娇,可那一切都变得遥远了;他仇恨柳一江一家人曾给他带来痛苦和死亡的威胁。
也迷恋柳雪萍那娇艳的花容月貌,一种兽性的欲望早已在他的污血中流动着。
可他也害怕过,怕自己的性命早晚会丧在对头手中——年羹尧、苏聪、柳一江,还有罗浩宇。
“哈哈!天赐良机!”他疯狂到了极点,忽然想入非非,他想他所烦恼的对手,竟然全不在家,夜色又给他制造了发疯的好条件。
“到药铺去捞一把,即使讨不着多大便宜,也好让他们过得不安宁。”他在酒梦中打定主意。
跌跌撞撞地回到他的狗窝,范一统换了一身夜行服,又找了块破布,紧了紧腰带,并随身带了一把蒙古短刀,然后一路歪斜地朝着药铺走去。
清兵的到来,已把这座小镇压得矮了许多!
夜幕,又把它裹得严严实实。
此时的天荒坪小镇,在黑夜中伫立无声!
夜风,在鸡鸣山前瑟瑟呼啸。
范一统带着七分醉意,象幽灵般地来到天荒坪大药铺的门前,只见那大门关得严实的,他又钻到阴影处,摸着冰冷的墙,找到了药店的后门。
凭着他在江湖中的鸡鸣狗盗经验,他二话不说,拔出短刀,插进门缝中,上下一划,找到了门栓。
他使劲拨动,可却纺丝不动。
看来,柳一江那老家伙早有防贼之心。
范一统人醉心不醉,腿断手没断,他打不开闭着的门,立刻改变主意,在那两屋之间不高的墙上打主意。
五年前,他曾受多立宝堂主指使翻墙入内欲捉拿昔日那个叫做吴剑锋而现在叫做年羹尧的人。
五年后,他又重操旧业,不过今夜他是为了他自己那****,想找柳雪萍发泄。
只见这时的他丢下手中的拐杖,倒退几步,一个纵身双手已攀上墙石上,只是一条腿断了,使不出劲来。
“叭”的一声摔在墙下。
可他没放弃。
一连三次,终于爬上了墙头上。
他朝院里看了看,只见屋里的灯已熄灭了。
范一统心中大喜,跳下墙来,看了看西屋的门口,随后直扑北屋的窗下。
他扒在窗边,将手指蘸了一下嘴里的口水,然后轻轻的将那窗纸撕开一个小口,再顺着那撕开的口子望去。
只见蜡烛光下,柳雪萍正在低着头做女红,不知不觉下,范一统他的口水顺着胡子流在了窗子上。
当他认定,整个院落中对他没有多大威胁时,登时胆大包天。
他离马上就离开这道窗户,轻轻地转到屋门外,伸手推了推,门却是虚掩着——看来一定是柳一江妻子给丈夫留着的门儿。
范一统心中不由大喜,他用破布把头蒙住,趴下身子,伸手轻轻一推,门便无声地开了条大缝儿。
他缩了缩身子,一下挤进了屋里。
“娘,是爹回来了?”柳雪萍听到声音,放下手中的针线,抬眼一看时,不觉吓了一跳,只见一个黑衣夜行人已经窜了进来。
“娘、、、、、、”柳雪萍惊叫一声,那夜行人却象条疯狗一样,劈头盖脸地朝她扑了上来。
她只感到一股恶臭的酒味呛得喘不上气来,身子不由的向后一倒,就被一个黑影重重地压在床上,无论怎样,也动弹不得。
可柳雪萍的喊声惊动了东屋里的欧阳冰倩,等她赶到柳雪萍这儿时,差点吓得昏了过去。
“畜牲!”欧阳冰倩冲到床边,挥动拳头朝那恶狗拼命捶打,并惊慌地呼喊:“抓贼呀,快来抓贼呀!”
范一统并不害怕两个女人的反抗,继续在床上与柳雪萍搏斗。
“嗡嗡”的声音从外面飞来,打断了门窗,是血滴子!
范一统知道这是年羹尧夫人柳兰芝被惊动了,并使出了那要人命的暗器血滴子,顿时吓出一身冷汗,他知道,此时不走,性命难保。
于是,他推开柳雪萍,顺势一滚就下了床,站起来夺门而逃时,后身却被人死命地抱住了,叫他怎么也挣不开身子。
范一统的酒一下就醒了大半,他听见西屋门栓响动,又吓出一身冷汗。
突然,他拔出腰间的那把蒙古短刀,回手就是一刀,只听“扑”地一声,一个身影倒下了,他急忙就势挣脱而去。
柳兰芝手提短剑来到北屋时,只见床上的柳雪萍昏迷不醒,地下血泊中倒着一个甚至——是欧阳冰倩。
“婶娘——婶娘——”
欧阳冰倩的心脉被刀尖扎断了,她是永远也听不到呼唤了。
、、、、、、、、、、、、、、、、、、、、、、、、、、、、、、、、、、、、、、、、、、、、、、、、、、、、、、、、、、、、、、、、、、、、、、、、、、
龙潭寺的觉明大师果真病得厉害,当柳一江赶到寺中时,他已是昏迷不醒,师徒俩一阵紧忙,号脉、灌汤药,直到下半夜才稍有好转——喘气均匀了。
熬到天亮之前,他终于清醒了,借着蜡烛的亮光,那无神的眼珠,认出了坐在眼前的柳一江,嘴唇动了动,低微的吁喊道:“兄弟,你终于来、、、、、、、、、”
“老哥,我守着你,有什么话就说吧!”柳一江急忙俯下身子,将耳朵贴在觉明大师的脸前说道。
觉明大师喘了几口气,断断续续地说:“兄弟,我一时死不了,咳、心绪不宁、看来还有点难见佛祖。”
“老哥,你还有什么牵挂之事,尽管说吧!”
觉明大师嘴角动了动,又说:“我一介出家之人,六根清净、四大皆空,与凡尘早断了瓜葛,要说牵挂之事,唯对兄弟放心不了!”
“我?”柳一江不由地惊问:“老哥,何事不放心。”
觉明大师说:“知弟者,兄也!弟一生坎坷,可你最讲究、诚直、善良——诚以处世、善以待人、善者,德也,正所谓积德行善爱惜生灵,扶此弱小、治病救人,视功名利禄如粪土,弟不极是一代大侠也。”
“既是如此,弟又错有何处?”
觉明大师道:“世事茫茫,一言难尽,然善恶有别,****宜分,弟却引狼入室,最近还将招血光之灾!”
“啊!”柳一江闻之大惊,觉明大师这最后一句话,恰与梦中的话相吻合,这是他始为不及的。
觉明大师眼皮动了一下,长长地出一口气,继续说:“兄弟,我虽身在佛门,却不远人也,有句话讲出口来,还望弟莫见怪!”
“老哥,尽管讲吧!”柳一江朝前探探身子。
“满清人与我汉人一脉,也讲究‘至仁、至义、至诚、至善’以此而论,不令智者、仁者、善者。可惜,当今雍正皇帝新登基,听信于那位大难不死的年羹尧,让清军杀到鸡鸣山来,残害黎民百姓,这年羹尧的诚在哪里?义在何处?报小恩而结大仇,与他不利,与弟也不利!”
“这言之极是,老哥说得有理!”
觉明大师说:“恶狗进镇,家无宁日!兄弟你该当机立断。”
“老哥,兄弟我知道了。”
觉明讲完这些话,如释重负,闭目不言。
天亮之后,觉明大师又服过柳一江的药,他就像卸掉了沉重的包袱,轻松坦然地睡着了。
柳一江给小和尚留下药,又再三叮嘱,然后带着罗浩宇匆匆下山。
“师父,觉明大师给你念的是什么经文?”罗浩宇边走边问。
“金玉良言经文!”柳一江胡乱应着,脚步越来越快。
柳一江经过觉明大师的点化,他似乎明白了许多善恶的事,他原本对年羹尧的报恩感到耻辱,又被路民瞻说的那番话,此时让他打定了自己的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