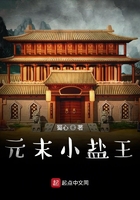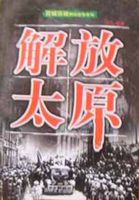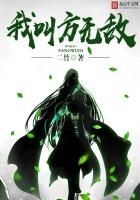(十四)
眼前的这份奏章,此刻居然使杨广眼前一亮。那笔墨凝重,形神耀目的恭正隸书,端庄华贵,转瞬间就把心不在焉的杨广吸引住了。这杨广,平日自命文武兼备,风流儒雅,酷爱书法,尤喜隸篆。大凡古今名家新秀的作品,对之品头论足是其一大嗜好。朝臣学士中擅长隸篆者,他颇为留意。他不禁暗自思忖:这份奏章的书法十分眼熟,好像出自自己亲点的进士房玄龄之手。然后,他翻转查看落款,由不得得意地一笑,果然一猜即中。可是,当杨光的目光一接触到奏章的内容时,那短暂转晴的脸上又堆上了阴霾。这时候,把一切都看在眼里的义成公主,在一旁小心翼翼的插了一句:“看来,父皇很欣赏这奏章上的一笔好书法。父皇果真好眼力,据说时下这京城里,像房学士这样的隸书,称得上极品,一字都难求呢。”
杨广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心想:小小学士竟然名动京城了,那就看看他的锦绣文章吧。由于心存挑剔,杨广目光再次在字里行间移动时,心神专注了许多。
国事三议。又是东征高丽,开河南巡,和亲突厥,不能换个题目做做吗?才气哪儿去了?杨广摇了摇头,鄙夷地一笑,还未哼出声来,就诧异地怔住了。
这房玄龄果然出手不凡,他开门见山就指出征高丽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打与不打,已经无须争议。现在的困境是,已经陷进了旋涡,不打亦难,如何在损兵折将之后,减少损失,比较体面的退出这场战争。这些话对杨广来说自然逆耳,但它却十分巧妙地抓住了他兵败之后,已经怯战,也想体面一点结束战争的心理。于是,杨广的鼻子在不知不觉中被牵住,不得不留神读下去。见此情景,义成公主竟感到几分意外。
那里知道,恰在此处,房玄龄的笔锋一转,竟突然写道:要体面退兵,还必须在转变危局,至少在军事上获得小胜之后。为此,当以前事为师,认真分析此前兵败原因,从中找出今后求胜之道非常重要。这样的转折手法,峰回路转,实则引向了对杨广用兵高丽的批评,这时竟没有引起杨广太大的反感。
房玄龄在奏章中痛陈高丽兵败的前车之鉴主要有三:
出师无名,打的是一场注定失败的不义之战。高丽与我朝唇齿相依,历来友好,不相侵扰,乞今竟借其与新罗有隙,内乱纷争,而刀兵相加其于危难之中。如此,持强凌弱,为战不义,已失胜算。何况,一战而把多年的友好邻邦变为强敌,从长远看也非常失策。
劳师远征,打的是一场扬兵耀武的耗损之战。远征高丽,本当以精锐之师,速战速决。朝廷却自以为必胜,将其作为炫耀国威的游戏。征发士卒劳役上百万,动用举国的田赋和府库钱粮,折腾得旌旗蔽野,国库空虚,民穷财尽。结果却无能战之旅,难建尺寸之功,天朝雄师竟不堪一击.
指挥混乱,打的是一场攻战盲目的糊涂之战。两军对垒,本来是我强敌弱。可每攻一城,在守敌难以支持时,只要守敌提出免战议降,我军就必须听命朝廷的统一指挥停战议和。这种一成不变的策略,造成敌人可乘之隙。敌方难以困守时,就免战议降,保存实力,借机补充力量。如此反复,一旦耗尽我军锐气,当出现有利于敌的形势变化时,敌方就抓住时机,集中兵力置我于死地。这种战略目标不明,被动挨打的战法,那有不败的道理呢?
房玄龄的这些分析,一针见血,处处刺中要害。明着陈述的是朝廷的失误,实则进谏的是要皇上自省。杨广当然对此心知肚明,由不得心中怒火升腾。可是,没有等到他发作,房玄龄的如神妙笔就又一次把他的注意力引向了自己在奏章中要阐明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