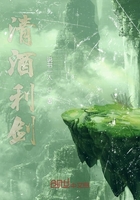面对履癸的决绝,华琰一下便跪在大殿之上,满脸的无可奈何,“王上!孋娘自知妹妹冒犯王上!可妹妹本性是个纯善之人!父亲去世的早!是孋娘教导无妨,才至今日!只是,请王上顾念昔日情分,给苕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孋娘定当好生教导,绝不再犯!”
履癸倒并未因为华琰的话而心生怜悯之意,话语依旧冷冷,“你既是如此姐妹情深,那就去冷宫一道儿陪她吧!”
妺喜一惊,履癸何以说出如此冷漠的话语来,和妃蛮横,纵使入冷宫,她也没觉得什么,只是,华琰贤德,也曾为履癸诞下太子淳维,对于履癸来说,华琰竟也是这般,说丢弃便可以丢弃的,着实叫人心寒。
华琰屡次的出手相救,妺喜感怀在心,虽说这一切都是和妃造成的,但终究还是与华琰无干的。
妺喜上前,“王上三思!王后娘娘贤惠仁德,诞育太子劳苦功高,请王上念及年幼的太子!和妃娘娘虽是王后娘娘的亲妹,但这本就是不该王后娘娘受的无妄之灾!怎能由王后娘娘受过!罪妾请王上法外开恩!”
妺喜来自有施,又是乞降国女子,履癸本对妺喜并没有半分的好感,但今日弋阳长公主几番说来,如今又如此的为王后求情,实属难得,若非真善心,那就是城府深,履癸笑笑,“北姬果然宽宏,方才王姐已经说明了,你去佛堂之事确属有人假意通传,所以你不是罪妾,不必如此称呼自己了!”
妺喜抬头,始终参不透履癸眼中的那一抹笑意,可她不能让王后白白的搭进去,她也曾帮过自己,她不能忘恩,“王上……”
履癸抬眸,静静的看了一眼妺喜,食指搭于唇上,妺喜噤声,只见履癸忽的转身,笑意浓浓,“华琰!孤王给你一个选择,如何?”
华琰不作声,但心中大体明白,这个选择必定很是艰难的,履癸玩味一笑,“要么,你去冷宫陪苕琬,要么,你亲自给苕琬斟一杯毒酒!”
妺喜诧异极了,履癸竟会让王后做这样的抉择,王后本就心善,别说苕琬,就是个寻常妃嫔,她也愿意用自个儿的一生来换她一条命,这样的抉择对于华琰,太不公平。
跪在地上的华琰在地上一步步挪动着膝盖,移动到了履癸的脚边,华琰的双手搭上了履癸的袍子,泪水一点点的滚下,“王上!您知不知道!孋娘在这世界上已经只有三个亲人了!一个,是王上!一个,是淳维!另一个,就是苕琬!”
履癸依旧无动于衷,可弋阳长公主毕竟是个女子,她能明白华琰对苕琬的维护,华琰的字字句句,更是触动她的心,心中亦有了一丝的侧影之心,闭上双眸,无奈的摆了摆手,“罢了罢了!送王后回宫吧!”
弋阳长公主话落,王后便跪着挪动着膝盖来到她跟前磕起头来,“谢长公主宽宥!本宫感激不尽!”
妺喜看着眼前的华琰,心酸的想要流泪,她是王后,是这个王宫后庭的女主人,竟为了这个不争气的妹妹,跪在长公主的面前,如此的狼狈,要知道,按宫规礼制,是该长公主给王后行礼的。
此事总也算是了了,妺喜虽是得以回泰安殿,但不过一日,妺喜的心里头已经五味杂陈,发生太多了,履癸的无情,王后的仁善,和妃的狠毒,一桩桩一件件,无不让人心寒。
刚过酉时三刻,弋阳长公主在泰安殿用过晚膳便启程回夫家了。妺喜一个人呆愣的坐在榻前,思绪百转千回,却终究是乱如麻。
“娘娘!”
听到怀亦的叫声,妺喜才恍然回过神来,“娘娘这是怎么了?奴婢都叫了您好几回了!”
妺喜勉强一笑,“没事,不过想的出神,不必担忧!”
怀亦呵呵一笑,妺喜也附和了一笑,主仆二人在泰安殿欢声笑语的,一会儿炎公公便来通报,“北姬娘娘!王上今夜宿在泰安殿!请北姬娘娘好生准备着!”
还未及妺喜答话,怀亦已经是高高兴兴的谢恩了,反倒是妺喜,眼神恍惚的坐在榻上,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似的。
妺喜畏惧,她明白,自个儿已经没有那么多的好运再次逃过履癸了,今日弋阳长公主又如此说,履癸对这红珊瑚珠又志在必得,侍寝是早晚的事,能拖延到今日,也确属不易了,只是,她究竟该如何?
妺喜心中畏惧,更是忐忑,此时此刻,满脑子浮现的,竟然都是和子履在驿站时的情景,那样一个温和的男子,如此的呵护备至,比起履癸,似乎更是一个合格的夫君。
“你说,获取天下时,必娶我为妻!可是真心?”咸涩的泪水从眼角一滴滴的滑落,妺喜伸手,泪水滴在掌心,妺喜用掌心的泪水沾湿手指,在案几上写下两个字‘子履’。
泪水渐渐的干涸,案几上只隐约的留下个‘履’字,恰好,履癸进殿,妺喜却未发觉,只听身后一句,“北姬果然学识过人,这字更是写的娟秀!”
妺喜惊醒,忙用手涂开了案几上的水渍,忙转身跪下,“妾参见王上!”
履癸面带笑意,心中总觉得方才妺喜案几上的那个‘履’,是她尚未写完的履癸二字,心中有些得意,更是把妺喜的惊慌视为是女子家的娇羞之态。
履癸亲自上前,扶起了妺喜的身子,妺喜站起身时,履癸更是拉近了妺喜,面对履癸的突然靠近,妺喜有些惊慌失措,履癸轻声在妺喜耳边呢喃,“不必如此惊慌!孤王特许你可以写孤王的名讳!恕你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