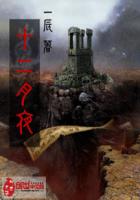鸳鸯姓金,也真有一颗金子般的心:高贵,纯真,刚强。在贾府所有大小丫鬟中,她看似人大面大,却极端鄙弃“攀高枝儿”的奴性心理,保持了作为奴婢的人格尊严——她堪称一位尊贵的卑贱者。
鸳鸯是世代为奴的“家生”奴婢,身份最卑贱,本应属于等级森严的贾府最底层,但是,她在贾府平时人际交往中,地位却似乎很不一般,不仅是天字第一号的头等大丫鬟,连主子们也要敬她三分,有求于她时,更要格外讨好她、奉承她。比如鸳鸯与凤姐虽是主奴关系,但平时似乎形同姐妹,凤姐一贯以姐姐相称;藕香榭酒席上,她们开玩笑之亲昵与放肆,几乎使人忘记了二人原是当家少奶奶与一个丫鬟的关系(第三十八回)。第四十四回王熙凤过生日那天,尤氏、众姊妹和嬷嬷们“轮流”敬酒,她已感到不胜酒力,当鸳鸯等人“也来敬”时,她便连连告饶,鸳鸯说她不“赏个脸”,“倒拿起主子的款儿来了”,话说得很重,说完就要走。“凤姐儿忙赶上拉住,笑道:‘好姐姐,我喝就是了。’说着拿过酒来,满满的斟了一杯喝干。”不要说丫鬟,就是主子中也不是谁都敢这样重话顶撞王熙凤的,被顶撞的王熙凤更不是对谁都会这样反赔笑脸满干一杯的(对“众姊妹”的“敬酒”,她也只是每人“喝一口”应景而已)。第七十二回,贾琏借口荣府公用“还得三二千两银子”,为求鸳鸯将贾母的“金银家伙偷着运出一箱子来”典当,对她“姐姐”前,“姐姐”后,一客气,二恭维,对她的到来说成是什么“贵脚踏贱地”,还骂小丫头:“怎么不沏好茶来!快拿干净盖碗,把昨儿进上的新茶沏一碗来。”
这哪里像主子对丫鬟的态度和口气,分明是巴结讨好,曲意奉承。
鸳鸯在贾府的特殊地位,当然不是因为自己身份高贵,而是来源于她所侍候的老祖宗贾母,这是奴以主贵现象。王熙凤、贾琏等人对鸳鸯的谦恭态度,不由得使人联想到封建时代一些王公大臣对受皇帝宠信的太监的态度。太监被称为阉竖(意思即是被阉割了的小人),身份是很卑贱的,但若受皇帝宠信,其特殊地位、特殊作用与巨大能量,往往使声势显赫、权倾朝野的王公大臣也要畏他三分,敬他三分;有求于他时,更要枉驾屈尊地同他拉关系、套近乎。贾母不是皇帝,但仅就她在贾府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点而言,也与皇帝或太上皇差不了多少;鸳鸯也不是太监,但她之于贾母,也与受宠信的太监总管之于皇帝的关系有相似之处。请看被称为“大菩萨”的李纨对鸳鸯与贾母关系的评说:
老太太屋里,要没有那个鸳鸯如何使得。从太太起,那一个敢驳老太太的回,现在她敢驳回,偏老太太听她一个人的话。老太太那些穿戴的,别人不记得,他都记得。要不是他经管着,不知叫人诓骗了多少去呢。那孩子心也公道,虽然这样,倒常替人说好话儿,倒还不依势欺人的。
这一评说不带私心和偏见,比较客观“公道”。鸳鸯虽深得贾母信赖,在贾府这位老祖宗面前说得起话,但她尚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也待人宽厚,“常替人说好话儿”。就连有权有势的王熙凤,在被故生“嫌隙”的邢夫人扫了面子“又气又羞”时,鸳鸯也能在贾母面前说些“好话”,澄清真相(第七十一回)。鸳鸯对下面的小丫鬟,也从不像晴雯那样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即使对别人“过失”也持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宽容态度。就在第七十一回,“已是起更时分”,鸳鸯从晓翠堂探春处回来,刚至大观园门前,无意碰见司棋与表弟潘又安在园中幽会。尽管她也认为男女私下幽会是“奸盗相连”的丑事、坏事,但一想到这“关系人命”还“带累”“别人”,宁可违背自己的道德感、是非感,并冒着包庇奴婢小厮偷情通奸的风险,始终对此事保持缄默,信守了自己对司棋的承诺(后来抄捡大观园时,因从司棋处抄出她给潘又安做的鞋和潘给她的“字帖儿”,二人的私情才暴露无遗)。
“不依势欺人”,心眼儿好,能包容人,这正是鸳鸯人品尊贵,值得人们尊重的地方。而鸳鸯金子般人品最闪光的表现,莫过于她的拒婚、抗婚行为(第四十六回)。
贾府名为“诗礼簪缨之族,温柔富贵之乡”,其实,行礼如仪的繁文缛节,温情脉脉的薄薄面纱,都掩盖不住背后种种触目惊心的荒淫无耻和罪恶行径。荣府文字辈长房贾赦,便是领着世袭官职、披着一张人皮的老色狼,其凶狠霸道(为一把扇子,弄得石呆子“坑家败业”、死活不明),连他不争气的儿子贾琏也颇有微辞;其好色贪淫,珍琏蓉辈浪荡子弟与之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他虽然“如今上了年纪”,“胡子苍白了”,对女色仍然“贪多嚼不烂”,丫头中“略平头正脸的,他就不放手了”,现在竟然色迷心窍,连“孝敬”母亲那点假面也撕下了,打起贾母身边唯一“可靠的人”鸳鸯的主意,想纳她为妾。但,直接向贾母要人,又担心贾母“要说不给,这事便死了”,于是采取曲线要人、逼母放人的策略,即让其不中用而又好使“左性”的老婆邢夫人出面先说服鸳鸯,“再和老太太说”,让贾母即使“不依”,也“人去不中留”,不得不放人。在邢夫人看来,鸳鸯“收在屋里”,“进门就开了脸”,封“姨娘”,“又体面,又尊贵”,难道“不愿意不成?若果然不愿意,可真是个傻丫头了。放着主子奶奶不作,倒愿意作丫头!”邢夫人及其主使者贾赦恰恰是打错了算盘看错了人。任邢夫人怎样花言巧语诱劝,鸳鸯始终一言不发,以沉默加以拒绝;鸳鸯嫂子奉邢夫人之命前来说服,更被鸳鸯一顿臭骂,自讨没趣;她哥哥金文翔专门接她到家去传达贾赦旨意,她也“只咬定牙不愿意”。鸳鸯拒婚如此坚决,原因在于她压根儿瞧不起那种把给主子作妾视为丫鬟“攀高枝儿”阶梯的奴性心理。她虽然与平儿、袭人私交不错,但却人各有志,道不相同,对她们心安理得,“自为都有了结果了,将来都是做姨娘”的“乐过了头儿”的想法很不以为然,更不屑效法。她高傲地宣告:“别说大老爷要我做小老婆,就是太太这会子死了,他三媒六聘的娶我去作大老婆,我也不能去。”这是身为奴婢的鸳鸯人格上的自尊自重,更流露出她对身份高贵的“大老爷”极端鄙视和厌恶的感情。
贾赦诱劝不成,便来威逼,公开要金文翔传话给鸳鸯:一是若嫌他老,“恋着少爷们”,趁早“歇了心”,他都要不来的人,“此后谁还敢收?”“第二件,想着老太太疼他,将来自然往外聘作正头夫妻去。叫他细想,凭他嫁到谁家去,也难出我的手心。除非他死了,或是终身不嫁男人……”这是公开威胁,要断鸳鸯一切退路和后路:不管乐意也好,不乐意也罢,除了答应贾赦作妾,别无他路可走,除非是要么今后不想活,要么终身不嫁人。厚颜无耻,穷凶极恶,竟至于此!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鸳鸯要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和个人意愿,已别无退路,只有抗争到底,但她深知自己势孤立单,人微言轻,要保护自己,还必须惊动尊神,借助权威——而在荣、宁二府,唯一能够镇住“大老爷”贾赦的尊神和权威的就是贾母。于是,鸳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从被动拒婚转而为主动抗婚,来个告“御状”,把对抗公开化。这正是鸳鸯刚烈如火、敢怒敢骂而又临事不乱、很有心计之处。那天,面对哥哥的奉命威逼,鸳鸯装作回心转意,要“他嫂子即刻带了他上来见贾母”。“可巧王夫人”等“都在贾母跟前凑趣儿”,“鸳鸯喜之不尽,拉了他嫂子,到贾母跟前跪下,一行哭,一行说”,把从邢夫人的诱劝到贾赦的威逼等事情原委一五一十告到贾母面前。这等于把贾赦之流推到被告席上,迫使老祖宗作出决断。最后,针对贾赦的恐吓威胁,她坚决表示:
……我是横了心的,当着众人在这里,我这一辈子莫说“宝玉”,便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着我,我一刀抹死了,也不能从命!若有造化,我死在老太太之先;若没造化,该讨吃的命,伏侍老太太归了西,我也不跟着我老子娘哥哥去,我或是寻死,或是剪了头发当尼姑去!……
她“一面说着,一面左手打开头发”,右手拿出剪子“便铰”,众婆子、丫鬟“忙来拉住,已剪下半绺来了”。
与贾赦的威胁恐吓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她下定破釜沉舟决心,宁可自断今后一切退路与活路,绝不屈服于贾赦的淫威。“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些古语、格言,用于此时此刻的鸳鸯是再恰当不过了。她当之无愧。
就现实结果看,鸳鸯的抗婚当然取得了胜利,鸳鸯的凛然正气压倒了贾赦的邪恶之气。这固然首先在于鸳鸯自己抗婚坚决,既不为利诱所动,也不被威胁吓倒,但如果她不聪明地借助贾母这位贾府最高权威的震慑和裁决,谁也不可能遏制住贾赦的淫威和恶行,鸳鸯的坚决抗婚很可能演成一场现实的血淋淋的悲剧(比如像她自己所称“一刀抹死”之类)。贾母出面干预,虽客观上起到扶正压邪作用,但其主观动机与其说是出于对鸳鸯的疼爱和同情,不如说主要是为了维护她自己的切身利益。谁都知道,鸳鸯是贾母房里丫鬟中唯一离不得的人,贾母的衣食住行、梳洗起居、饮酒玩牌直至财物掌管,都得依靠她一人,贾母对鸳鸯有一种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适应性和依赖性。正因为如此,贾母在训斥了邢夫人“由着你老爷性儿闹”之后,又要她转告贾赦:“他要什么人,我这里有钱,叫他只管一万八千的买,就只这个丫头不能。”可见她对贾赦淫恶行为本身并不怎么反感,认为他另买侍妾可以,只是不能给鸳鸯。鸳鸯抗婚结局恰好证明:贾母对鸳鸯主要有一种生活上的依赖,而鸳鸯对贾母则是一种人身上的依附。
不过,这一看似乐观的结果,远不是事情的终局。鸳鸯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贾母已是风烛残年、行将就木之人,一旦寿终正寝“归了西”,鸳鸯人身失去了这唯一依附和保护伞,只要那时贾府未败、贾赦未死,那么,对鸳鸯怀恨在心的贾赦是绝不会放过她的,正如她自己预想的那样,那时除了“寻死”、出家,是别无出路的,甚至出家也逃不出贾赦“手心”,因而实际上只有死路一条。
一个花样年华的姑娘,不仅要长期“伏侍”一个风烛残年的贵族老太太,还被迫一辈子“横竖不嫁人”,白白牺牲自己青春年华和一生幸福,这已经非常可悲。在老太太寿终正寝时,还不得不赔上自己年轻的生命,成为其殉葬品,这更是惨无人道。高鹗续写的第一百一十一回写贾母死后鸳鸯上吊自尽的终局本不算错,但描写鸳鸯之死毫无生动感人之笔,却有照章(即原著前八十回有关描写)敷衍之嫌;写鸳鸯上吊前,由吊死鬼秦氏示范,教她“死的法儿”,则更是浅薄拙劣的败笔。
可见鸳鸯在贾府似乎地位特殊,受人尊重,实际这不过是奴以主贵的暂时表象或假象,从根本上说,她和其他“身为下贱”的奴婢没有任何区别。唯一可能的区别是:她也许比某些丫鬟人品更尊贵,而命运却比某些丫鬟更悲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