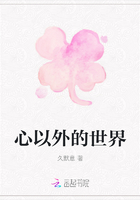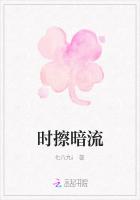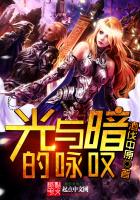来吴哥的外地游客,着迷于看华美雄峻的建筑,着迷于看精细繁复的雕刻,目不暇给。每日匆匆忙忙,满眼看去都是伟大的艺术,大概没有很多人有心思去想:当地一般老百姓是如何生活的?
吴哥王朝留下的建筑雕刻,都是古代帝王贵族所有的神庙皇宫。当时的一般老百姓住在哪里?当时的一般人民过什么样的生活?他们的衣食住行究竟和这伟大的艺术有什么关系?我心里疑惑着,不得其解。
Ming,我看到每一日围绕在我们四周的小贩、乞讨者、儿童、战争里受伤的残障,男男女女,他们面目黧黑,瘦削,衣衫褴褛,卑微地乞求着一点施舍。忽然觉得自己在艺术上的陶醉这样奢侈,也这样虚惘。
大部分到吴哥的游客害怕当地人,一堆小孩、乞丐、残障拥过来,团团围住,伸手向你要钱要东西。你的好心慈悲会引来更多的乞求者,像烈日下驱赶不完的苍蝇蚊虫,弄到最后,只有落荒而逃。对自己的无情残酷深深忏悔自责,对悲苦的现实又丝毫没有助益,许多观光客的“悲悯”、“教养”、“善心”都在这里受到了最大的考验。
“艺术源自于生活”,也许是一句轻松又冠冕堂皇的话。真正要深究艺术与人的生活之间的关系,或许并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楚。
埃及的金字塔是帝王的墓葬,四千年以前陪葬品的精致,令人叹为观止。图坦卡蒙(Tutenkhamon)只是十八岁去世的年轻国王,墓葬中出土的金银饰品,手工捶揲的精美,宝石镶嵌技术的繁复,色彩搭配的准确和谐,造型的丰富创意,今日的美术工艺也只有自叹弗如。也常常使人疑问:这些工匠的创造力与审美品质,远远超过今日美术的专业工作者, 那么,我们大费周章的美术教育专业训练所为何来?
如果埃及的社会结构正是一个金字塔式的层级组织,所有我们今日欣赏的埃及艺术,其实是金字塔顶端最高层级、极少部分人所享有的生活内容。也可以想见,一个长达一千年的时代,绝大部分人的生活只是随波逐流,在时间里淹没,没有留下一点痕迹。他们用手制作出技术惊人的金银器皿,但是他们一生无缘享用,他们生活里可能只有土木制作的器物,只有草和树皮编制的物件,这些物品随时间腐朽风化,无法保留,留下来的是不朽的金银珠宝,是巨大的石造建筑。
用社会史的角度去看艺术,艺术的不朽或许只是一小部分的精英拥有的特权。追问下去:希腊的雕像与谁有关?宋代的山水画是哪些人在欣赏?如同我常常在想:台湾2300万人中,有多少人一生没有进过故宫博物院和音乐厅?
假设两千年以后,今天的台湾文明像吴哥一样被发现,我们有什么可以被称为“艺术”的遗留使后人赞叹吗?
我在蜂拥而至的乞讨者包围下胡乱地闪过一个巨大的疑问:为什么在这样大的吴哥城,我看不到任何庶民生活的痕迹?
在印度教的信仰影响下,整个吴哥城的重心都围绕着宗教打转。巨大高耸的寺庙无处不在,历代统治者都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修筑祀奉众神的庙宇。
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记录了他看到的吴哥王朝的庶民生活,有一句话说:“如百姓之家,只用草盖,瓦片不敢上屋。”
关于帝王的宫室,周达观记录:“正室之瓦,以铅为之;余皆土瓦,黄色。”
遗址的挖掘,铅瓦、黄色的陶瓦都有发现,至于百姓居住的“草盖”之庐,当然经历了数百年,早已腐烂风化、荡然无存。
无论寺庙或皇宫,所有的雕刻装饰也以神佛为主,很少以真实的人间生活为主题。
值得特别一提的例外是巴扬寺。这所由阇耶跋摩七世修建的陵墓寺庙,在四围的石砌墙壁上刻满浮雕,其中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庶民生活的图像。
在寺庙四围,围绕长达1200米左右的浮雕饰带,主要是以高棉人(Khmer)在12世纪和占婆人的战争为主题。阇耶跋摩七世打败占婆,吴哥王朝国势达于巅峰,这所由他修建的寺庙,也因此留下了这一场战役的历史景象。笃信佛教的阇耶跋摩七世,改变了部分印度教信仰对众神的崇拜,使艺术的内容从诸神的故事转移到人的历史。
战争的主调像一部电影缓缓进行。大象、车子驼载着货物,士兵手持长矛,列队而行。树木繁茂扶疏,鸟雀在树上鸣叫跳跃飞翔。男子都裸身,仅胯下缠围一布,像台湾达悟族的丁字裤。
这数量庞大的浮雕风格特殊,和其他寺庙表现神佛的庄严崇高不同。巴扬寺的浮雕传达出庶民生活的活泼自由,雕法写实而又丰富,长达几十米的战争主题,层次如叙述诗一般,缓缓行进。树林自然成为大衬景,让人感觉到生活的愉悦幸福。一棵树姿态婉转,树茎树叶平面展开,鸟雀布置其间,形式像汉代的画像砖,但更多为写实细节。
戴着头巾、留着络腮胡的占婆兵士,被高棉军人用长矛刺杀,倒毙在地。高棉军人孔武有力,身体骨骼肌肉的表现及动态的掌握都十分精准。这种以生活现实为主题的美术创作,来自对生活细节的认真观察,也一定充满了对现实人生热情的关心与投入。
庶民的生活借着战争的史诗被记录了下来,也许要仔细特写,才看得到浩大壮观的战争历史场景里,活跃着细小不容易被发现的人民存活的快乐。
作坊里一名陶工正专心在辘轳上用手拉坯,制作陶器,制好的陶坯正要送进窑中去烧。他们忙碌着,好像那战争与他们无关。
战争归战争,庶民百姓还是要努力使自己开心生活。他们趴在地上,手里抱着公鸡,两人面对面,吆喝着公鸡上场互斗。许多人看到这个场景不由会心一笑,直到今日,斗鸡仍然是南洋一带庶民男子最常见的日常游戏。
有人在市场木棚屋顶下卖鱼,有人牵着野猪互斗,有人腹中阵痛如绞、正要生产,有人悠闲地静静坐着下棋。
巴扬寺的石壁浮雕使我徘徊流连,那些朴素单纯的庶民生活如此引人深思。
Ming,我走出吴哥域,在今日的暹粒市闲逛。大部分的柬埔寨人仍然居住在树叶草秆搭建的屋子里,草棚用两三公尺的木柱架高,有梯子可以上下,上层睡人,下层堆放货物。
长年炎热,许多人就在户外树上拉一条简便吊床,睡在树间,自在摇晃,怎么翻身也掉不下来,令人羡慕。
有一种树如棕榈,10多米高,当地居民在树干上凿孔,引树汁流入桶中,桶满,将树汁置铁锅中熬煮,用木勺慢慢搅拌。待水分蒸发,将稠黏的液体一小勺一小勺倒进竹片围成的模具中,凝固成围棋子大小的棕糖,十数颗一串,用棕叶包裹,拿到市上售卖。
我看他们制糖,谈谈笑笑,不慌不忙,像在巴扬寺的石壁浮雕里,天灾人祸都没有使他们惊慌忧愁。我品尝着棕糖的甘甜,觉得生活幸福美好,好像可以到寺庙叩拜,感谢神恩。
空中宫殿与象台
周达观描写国主在夜晚独自登上天宫,与代表神、天、土地或生殖的女蛇交媾,这是民间对此仪式神秘性的传说,也使我对这座建筑产生神圣的感觉……
周达观在西元1296年到吴哥窟,停留了一年多,撰写了《真腊风土记》。这本书是西方人在19世纪研究吴哥城的最重要资料。有许多段文字的记录,在现场和今日还可见到建筑物的对读印证,还有十分真切的感觉。
周达观正式的身份是元成宗铁穆耳派往真腊王国的特使团团长。但也有传说,当时元廷有野心进攻真腊,周达观极有可能负有侦察军事机密的任务。他的书里对吴哥城的城墙长度高度、城门宽度、护城河河宽与桥梁,都有精确的记录,的确使人怀疑《真腊风土记》隐藏着机密的军事情报在内。
《城郭》一章的内容经过现代考古的比对,几乎完全正确:“州城周围可二十里,有五门,门各两重,惟东向开二门,余向皆一门。城之外巨濠,濠之上通衢大道,桥之两旁各有石神五十四枚,如石将军之状,甚巨而狞,五门皆相似。桥之栏皆石为之,凿为蛇形,蛇皆七头,五十四神皆以手拔蛇,有不容其走逸之势。”这一段描述,今天去吴哥旅游的人,在城门前可以做最现场的印证,也说明周达观观察与描述的精细。
《宫室》一章描述当时吴哥王朝的行政中心,也有许多细节。
“国宫及官舍府第皆面东。”吴哥王朝是崇拜太阳的,主要建筑物的入口都朝向东方。事实上,吴哥建筑、寺庙的平面多以印度曼陀罗为蓝图,四方形,一层一层加高,突显中央的须弥山。在四方形的四边多有门,门以多重结构装饰,特别强调门楣的华丽,称为“塔门”(Gopura),但的确一般都以东门作为最重要的入口。因此,东门前多有很长的“引道”,成为敬拜的仪式性空间。
一般游客现在造访吴哥,游览的地方多半是寺庙、陵寝。皇宫的部分多已不完整,只剩台基遗址。
周达观书中写到“莅事处”,是和当时真腊国的行政中心有关的记录:“其莅事处有金窗棂,左右方柱上有镜数枚,列放于窗之旁;其下为象形。闻内中多有奇处,防禁甚严,不可得而见。”周达观指的“莅事处”,应是今日的“象台”。
“象台”是皇宫前宽350米的一处平台,非常像举行阅兵大典的观礼台,面对正东一片大广场。
“象台”以石砌,高两三米。朝外的部分雕刻成大象的形状,故名“象台”。事实上,大象只雕出三个立体头部,头上戴宝冠,象牙向外突出,身体的部分是以平面浮雕技法来表现。象鼻下垂,着地,像一根一根列柱。吴哥王朝的雕刻,观念非常活泼,在结构功能要求下,兼具写实和抽象的表现法,混用浮雕和立体雕刻的两种手法,“象台”是最明显的一例。
“象台”四周的雕刻事实上不只是象,也有“飞狮”和“神鸟”(Garuda)造型,高举双翅,挺胸站立,厚实雄壮,的确是国王“莅事”、“朝觐”或“阅兵”的气派。
从平面来看,“象台”是皇宫对外的窗口。“象台”后方就是皇宫,一定也兼具防卫的功能,所以周达观才会说:“内中多有奇处,防禁甚严,不可得而见。”
至于周达观叙述的“有镜数枚”,现在当然都不存在了。早年石砌的台基上应该是木构造的宫室,也大多无存,只有参考古遗址中发现的一些铅瓦、陶瓦,和周达观的描述相合:“其正室之瓦,以铅为之;余皆土瓦。”
皇宫中被周达观描述最详细的是“金塔”。“金塔”即是今日一般俗称的“空中宫殿”。
“空中宫殿”原名Phimeanakas,是由Vimana和Akasa两个梵语合成,直译也就是“天宫”。
“天宫”是皇宫内现存较完整的建筑,是三层加高金字塔造型,四面有石阶可以攀登,东西长35米,南北28米,只有12米高,但因为角度的关系,感觉非常陡峻。
“天宫”是罗贞陀罗跋摩二世(Rajendravarman II,在位944~968)在位时修建。这座石造高塔非常神秘,当初只有国王可以上去,周达观也记录了这座塔的神秘性传说:
“其内中金塔,国主夜则卧其下。土人皆谓塔之中有九头蛇精,乃一国之土地主也,系女身,每夜则见;国主则先与之同寝交媾,虽其妻亦不敢入。二鼓乃出,方可与妻妾同睡。若此精一夜不见,则番王死期至矣,若番王一夜不往,则必获灾祸。”
周达观这一段神奇的描写,使我拿着书站在“天宫”前,有了很不同的感受。
真腊的国王是神的化身,他们在人间的统治,虚拟为天神的附身。“天宫”或许是国王夜晚祈祷奉祀上天的所在,整座建筑陡峻庄严,也特别具有仪式的意味。“蛇精”九头,应即是印度教宇宙初创的龙形大神“哪迦”(Naga),国王与她的交媾,也便是另一种形式的“君权神授”的象征吧!
事实上,吴哥寺庙中到处还看得到印度教信仰对于“性”的原始崇拜,象征阳具的圆柱“林珈”(Linga),和方形水槽象征女性阴器的“优尼”(Youni),组合成神殿中重要的膜拜空间。
在吴哥城外科巴斯宾山(Kbal Spean)暹粒河(Siam Reap River)发源的河床谷地,也发现了刻满阳具与阴具的符号,在浅浅的河床巨石上,以生殖的图像祝福河水流向人间,繁殖绵延,成为富饶生命的象征。
Ming,人类或许离开原始的生殖崇拜已经很远了。许多人会对吴哥文化中的性器崇拜觉得好笑或猥亵,已经很难理解初民在崇拜生殖的仪式中,寄托着对生命萌生的庄严祝福,与今日发展成感官刺激的性,是很不相同的吧!
周达观描述的国主在夜晚独自登上天宫,与代表神、天、土地或生殖的女蛇交媾,或许只是民间对此仪式神秘性的传说。经过周达观的记录,今日矗立在一片废墟中的天宫,更增加了神秘感,使我对这座建筑产生神圣的感觉。
象台的东北端,有一处高7米的台基。台基上原有的木构造建筑已不存在,但台基四周的雕刻非常精美。这一处平台上,有印度教死亡冥界负责审判的大神“牙麻”(Yama)的像,因为石材的变质,身上显出苔斑,仿佛皮肤病,因此俗称为“癫王台”(Terrace of the Leper King)。但民间也传说,此台修建于耶轮跋摩一世时代,而这位创建吴哥城的国王,的确后来得麻风病而死。
“癫王台”的说法无法考证,但“象台”此处似乎的确与昔日吴哥王朝的“审判”、“诉讼”有关。
周达观《真腊风土记》的《争讼》一章留下可贵的记录:“两家争讼,莫辨曲直;国宫之对岸有小石塔十二座,令二人各坐一塔中,其外,两家自以亲属互相提防。或坐一二日,或三四日,其无理者必获症候而出:或身上生疮疖,或咳嗽发热之类,有理者略无纤事。以此剖判曲直,谓之‘天狱’。”
现代人的司法观念,大概很难了解“天狱”。“天狱”是相信上天有一种公平的审判,所以双方有诉讼,无法判断对错,就把原告、被告各自关进皇宫对面的小塔中。由对方的亲属监视,不准出来,一直关到其中一方生病,或生脓疮,或发烧咳嗽,便说明此人有罪,已得上天惩罚。
周达观的记录虽然神奇,但现在“象台”东西广场上还留有着12座小塔,原本都不知道功能,因为周达观的记录,留给后人一条思索的线索,颇为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