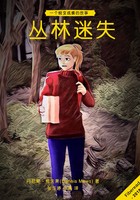寿仙宫一片慌乱。
苏妲己在大悲大痛大惊大怒之时都会犯病,昨夜受到惊吓,旧病复发。因帝辛在外,苏妲己显得孤苦伶仃,无人怜悯。辛怜认定苏妲己是圣道姊妹,对昨夜之事充满歉疚,早早来至寿仙宫。宫女们不认识辛怜,又个个手忙脚乱,无人上前招呼。
一黑一白两个太医匆匆来到,只冲内室卧榻上的苏妲己瞧了一眼,便悄悄退到厅堂品茶。白脸太医道:“今日你我二人当班,若非陛下远征,此时你我的人头早就落地了。”黑脸太医道:“老兄说话小声点儿,苏娘娘亦能置我二人于死地。”白脸太医呵呵一笑,道:“她不是在昏迷之中嘛。”呷了一口茶,把玩着茶盅说道:“我这张嘴有口福呀,今日尚能在此品茶。”
辛怜再也按捺不住,喝道:“你们两个狗屁太医,怎么还不诊治?”
黑脸太医对白脸太医说道:“老兄,还是赶紧诊治吧。”白脸太医为辛怜是个宫女,自然没把她放在眼里,慢吞吞说道:“诊治不诊治还不都一样,若诊治就能医好苏娘娘,哪还会有许多太医被杀?”辛怜气得咬牙切齿,道:“狗眼看人低!陛下不在,你等竟敢见死不救。”朝苏妲己再望一眼,悲悯之意塞满胸膛,眼圈竟红了。
这时,耳听费仲、尤浑说道:“臣费仲、尤浑求见苏娘娘。”
值日女官道:“苏娘娘凤体欠安,二位大人请在厅堂稍坐。”
两个太医慌忙站起,垂手恭立,二人自然清楚,只要费仲、尤浑给帝辛或苏妲己一丝进言,二人的小命就会立马被阎王爷勾销。
费仲、尤浑躬身进门。尤浑一眼看见案几上的茶盅,站直了身姿,嘿嘿笑道:“二位太医好雅兴。”黑面太医顿时魂飞魄散,双腿打颤,跪倒于地,“砰砰砰”乱磕响头。白面太医脸色更加惨白,吃吃说道:“我……该死!”费仲阴阴地道:“二位太医叫什么?”如果报出姓名,就等于写在阎王判官的生死簿上了,黑面太医闻听,登时昏厥。白面太医语无伦次,道:“没名,不不,有名……”费仲瞧了一眼辛怜,不阴不阳地道:“原来御妹在此,下官有礼了。”因辛怜来自西岐,是被姬昌所荐,二人对辛怜自然毫无好感。白面太医突然“啊”了一声,道:“她是御妹?”心想适才又对御妹无礼,哪里还有活命?目翻白珠,昏死在地。
忽听宫女喜道:“苏娘娘醒了!”
苏妲己转醒,在梦境里定是进了左门,眼神之中凶光乱闪。黑尤叫声欢快,依偎在苏妲己身旁,动作亲昵。苏妲己一眼看见辛怜,道:“怎会是你?”辛怜一跳,担心昨夜女扮男装被她认出,忙道:“怎么?”苏妲己紧紧抓住辛怜的手,道:“妹子,你怎么来了?”辛怜怯怯地道:“我是御妹……”
值日女官道:“启禀苏娘娘,费仲、尤浑大人求见。”
苏妲己在辛怜搀扶下,来至厅堂。费仲、尤浑跪地磕头,齐声说道:“臣等来迟,请苏娘娘恕罪!”苏妲己道:“爱卿平身。”一眼看见地上昏死的太医,奇道:“这是……”尤浑道:“这是两个太医……”辛怜恨恨地道:“该杀!竟敢怠慢姐姐。”苏妲己道:“那就杀了吧。”
尤浑朝门外兵士招了招手,过来几个兵士,像抓小鸡一样拎着两个太医走了。
苏妲己坐了,转向辛怜细看,她已听帝辛说过西岐献美被封御妹之事,道:“御妹的相貌举止,与本宫的妹子几乎一模一样,年龄也相仿,难怪让本宫认错。”说罢自笑了,拉着辛怜的手,又道:“今后你与本宫就以姐妹相称。”辛怜顿时想起被娘亲疼爱时的情景,顿时热泪盈眶,此时真想说声“对不起”,话到嘴边,自然不能出口,轻唤一声“好姐姐”,便已是哽咽。苏妲己见状,手拉得更紧了。
费仲道:“苏娘娘,臣等有要事禀告。”说完看了辛怜一下,意思是让辛怜回避。辛怜哪里懂得这些,丝毫未动。苏妲己道:“御妹是我刚认下的妹子,无妨。”摆摆手,让宫女退了。
费仲轻咳一下,道:“昨夜余妃和一个男子同床被杀……”
苏妲己喝道:“丢人现眼!如何处置的?”
费仲道:“比干王叔同姜娘娘商议后,姜娘娘下了懿旨,把二人悄悄葬了。”苏妲己冷笑着说道:“怎能一葬了之。”尤浑道:“臣等以为,这是朝廷的奇耻大辱,就该灭余妃的九族!”
苏妲己淡淡地道:“爱卿去办吧!”
之后,费仲、尤浑将余妃和那兵士的九族全部诛杀,结果此事弄得天下尽人皆知。
费仲压低嗓音说道:“刺客早也不来晚也不来,恰在陛下远征期间,臣等猜测,余妃会不会是被刺客误杀?”辛怜心头一跳,忙偷眼观看苏妲己。苏妲己道:“不错,刺客是冲本宫来的。”辛怜又是一跳,暗道:“我该转守为攻了。”佯装气恼,说道:“哼!今天一早比干王叔气势汹汹带人围了我的寝宫,说昨夜那刺客肩头被射中一箭,要验我是否有伤。”苏妲己、费仲和尤浑一齐朝辛怜肩头望去,辛怜活动几下筋骨,道:“如果妹子有伤,百口莫辩,早被他捉了去了。”
费仲面无表情,道:“只怕是有人贼喊捉贼!”
苏妲己道:“比干到处散布流言蜚语,对本宫恶语中伤,早晚叫他死无葬身之地。”
辛怜暗道:“苏妲己果然是圣道姊妹,负有祸乱殷商之使命。”再瞧瞧费仲、尤浑,一个道貌岸然能言善辩,一个见风使舵巧言令色,二人一唱一和,翻云覆雨,正是天生绝配,一言能使江山倾覆。辛怜不动声色,继续听三人谈论。
费仲装出一幅悲天悯人模样,道:“苏娘娘,非是臣等危言耸听,时下朝廷浊浪翻滚,只怕会地覆天翻。宫中近日所发生之事,陛下丝毫不知。臣等以为应如实禀报陛下,请陛下扫除阴霾,重振朝纲!”苏妲己道:“正该如此,速速禀报陛下!”费仲、尤浑道:“臣遵旨!”
原来,比干监国,二人深感危险迫近,正好利用此事,让帝辛早日回朝。
帝辛亲征东海造反隶人莫老五,料定莫老五会在沂山之荷荷谷设伏,依攸喜之计,表面上每天跟一根葱周旋,一日只走五十里,暗地却差晁田、晁雷兄弟统帅六万大军,直扑荷荷谷,想杀莫老五一个措手不及。
晁田、晁雷昼夜兼程,这日傍晚来到荷荷谷前。
荷荷谷恰似一个大葫芦,四面山岭,小口大肚,隐于密林深处。晁田冲谷内张望一回,道:“隶人还真会选取设伏之地。”晁雷道:“哥哥,你堵住谷口,我带人往里冲。”一摆手,兵士递来两坛酒,兄弟二人各自捧了一坛,往肚子里猛灌。饮毕,二人已是红头胀脸,将酒坛扔于地上。不料,晁田的酒坛原地打了个转,并未粉碎。晁雷以为不吉,冲兵士一努嘴,喝道:“砸了呀!”兵士飞起一脚将酒坛踢碎,因用力过猛,手捂脚面,单脚乱蹦,痛得龇牙咧嘴。晁雷高声令道:“冲!”
攸喜道:“慢!将军没喝多吧?”
晁雷瞪着一双醉眼喝道:“你想说啥?”
攸喜道:“二位将军,请先派小股人马探查,而后再令大队人马跟进。”晁田面带不屑,道:“打草惊蛇,还如何突袭?岂不闻兵贵神速。”晁雷道:“出其不意,不正是你的主张吗?”攸喜依然不紧不慢说道:“战场情势瞬息万变,敌变则我变。我等来得突然,按理说隶人应在谷内歇息,怎会不见一个人影?”晁雷道:“陛下尚有四五日才能来到,莫老五若提前到此,只能吃露水喝山风,隶人也不傻,也会算计!”晁田点点头道:“不错,也许再过两天莫老五才会来到,我等正好先在此预设埋伏,这就叫‘反客为主’。”攸喜幽幽地道:“只要王师不入山谷,谷内纵有十万伏兵亦奈何不得。事关六万将士性命,不可大意!”
晁田显得很不耐烦,回头喊道:“谁去探查?”
一员偏将带了十个兵士进了山谷,不一时回转禀告:“将军,谷内并无异常。”
晁雷斜睨攸喜,大声“哼”了。攸喜道:“怪哉!按常理莫老五布置停当后,才会派一根葱前去诱敌,这时候怎会不在设伏之地?”用马鞭指了指,一字一句地道:“我料其中有诈。”晁雷按捺不住,叫道:“我弟兄身经百战,屡建奇功,难道还辨不出隶人这等小小伎俩?休得再说!”攸喜已被革职,目前仅是一员偏将,晁雷自然不再把他放在眼里,故而厉声呵斥,言语之间毫无恭敬之意。攸喜暗道:“谁敢蔑视攸喜,就叫他不得好死,你二人等着瞧吧!”此时不动声色,说道:“二位将军,请再派人探查!”晁田道:“已经探查过了,谷内并无一兵一卒。”将手一挥,令道:“进谷!”
大队人马徐徐而入,不一时尽入谷内。
荷荷谷一片寂静,偶尔传来几声鸟鸣。
晁雷道:“哥哥,请传令兵士,太阳落山前在四面山头布好埋伏……”
忽然响起一声螺号,从谷口两面山头上飞落块块巨石,将谷口堵住。四面山头出现黑压压一片片隶军兵士,难计其数。战鼓震天动地,滚木雷石呼啸而下,王师将士尽在谷底,无坚可守,形同俎上鱼肉,任人宰割,惨叫声中死伤无数。
晁雷登时酒醒,大叫一声:“糟,中埋伏了!”
这时,从幽谷深处传出马蹄声,倏忽间飞出一匹青马,马上之人青脸素目,说道:“请晁田将军出来答话。”
晁田、晁雷对视一下,晁田出马上前。
那人在马上拱了拱手,道:“我是义军上将军‘擀面杖。’”想必这人出生时,父亲正在擀面,故得此名。晁田打了个酒嗝,腐酸之气破喉而出,道:“怎样?”擀面杖忙用衣袖捂住口鼻,道:“殷商朝廷什么都缺,唯独不缺‘酒蛤蟆’,刚刚打走一个,现在又来一个,整天泡在酒缸里,怎么能打胜仗?”刚刚打走的乃指曲直。
晁田喝道:“那就大战三百合!”
擀面杖淡然一笑,道:“你等已被团团包围,数万人马生死一念,请你认清实务,归顺我义军帐下。莫老五大哥仁德宽厚,定会善待你等。”晁田厉声喝道:“住口!你等世代被隶主豢养,不思报主大恩,却扯旗作乱,杀主掠财,忘恩负义之辈有何颜面在此口吐狂言?”擀面杖并未气恼,依旧心平气和,道:“隶人世代为奴,被主盘剥,动辄惨遭杀戮,无端身首异处。官逼民反,莫老五大哥举义三载,屡挫王师,今你已中埋伏,若不投降,只能自取灭亡。”晁雷气得鼻眼错位,叫道:“反贼,认得你爷爷吗!”催马挺枪直刺擀面杖。擀面杖架住晁雷的兵器,道:“我是来劝降的,不是来厮杀的。”说罢拨转马头,扬长而去。
晁田气得兀立当地,大喘粗气。
擀面杖回归本阵,战鼓轰鸣,箭羽铺天盖地。箭杆上绑着引燃之物,点燃王师辎重车帐,烈火浓烟冲天而起。王师将士又被射死、烧死无数,陈尸满地。晁田两眼冒火,令兵士猛攻东面山头。不料,兵士爬至半山腰,箭如雨下,兵士连死带伤滚滚而落,哪里攻得上去?攸喜道:“二位将军,请下令停止进攻。只要王师不动,隶人就不会攻我。莫老五占尽地利,灭王师于谷底并非难事。但他是想用我等引诱陛下,而后再一网打尽。”
晁田当即传了令,荷荷谷果然恢复平静。
晁田道:“速速派人突围,给陛下报信。”晁雷道:“谷口已被堵住。”攸喜道:“谷口未被完全堵死,可差人从缝隙间冲出去。”晁雷道:“隶人居高临下,弓弩于上,谁能出得去?”攸喜道:“莫老五自然会让道。”晁田选了十个精壮兵士,再三嘱咐:“将荷荷谷情势细报陛下。”攸喜道:“万不可让陛下再来!陛下不来,我等自会想方设法突围出去;陛下若来,都会陷入绝地。”
隶人果然只做了象征性阻击,仅射杀三个兵士。
攸喜突然说道:“不好!六万将士之生死,陛下哪能不顾?以陛下性情,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定会义无反顾前来救援。”
晁田闻听,又打了一个酒嗝。
且说姬昌。
姬昌在朝歌期间,访比干、箕子和微子“三仁”,贿费仲、尤浑以重金,并得帝辛恩准,回程时走北路。当时,中原通往西岐之路共有两条,一南一北,南路是经“三关一河”的官道;北路经冀州、燕亳上黄土高原。冀州包括今河北大部、山西一部,是当朝国丈、苏妲己之父、冀州侯苏护的封地。燕亳包括今北京,以及河北、山西一部,是北伯侯崇侯虎的封地。姬昌选择北路,就是想顺道打探北伯侯崇侯虎的虚实,知己知彼,有备无患。
姬昌、闳夭、蒙秋和土行孙,带着二十个兵士一路向北,而后折向西北,这日来到“坨坨岭”,岭的另一头就是冀州。放眼望去,只见坨坨岭虽不险峻,但林木高深,中间一条羊肠小道。
众人走了一回,眼前突然开阔,原来坨坨岭腹地有一块不小的平坦地段。就在这时,响起一通锣鼓。闳夭叫道:“留意!”蒙秋紧了紧浑天棍,等候厮杀。不料,锣鼓响了一阵,骤然停止,未见一个人影,一片死寂。
众人尽知凶险就在眼前,个个如临大敌。
土行孙故意说道:“或许这就是苏国丈的迎客礼仪。”
土行孙,大头大脸大蒲扇脚,小鼻小眼小芝麻牙,个头不足三尺,上身奇长下身奇短,黄眼珠黄胡须,一年四季无论春夏秋冬不分白天黑夜均身着黑色夜行衣,只是狐臭非同一般。土行孙长相虽怪,武功却高,生就一副侠肝义胆,性情桀骜。说话奶声奶气,却爱口出狂言。土行孙擅长奔跑,攀缘走壁如履平地,所以在神话里是个一日土遁一千里的神人,足见后人对其非凡本领之敬畏。
这时,铜锣声又响了起来,足有百面锣鼓,“咚咚咣咚咚咣”整齐划一,极有节奏,隐约中还有笙箫之音,悦耳动听。树丛中斜出十面黑色大旗,每面旗上都秀有一个巨大的“阴阳鱼”,正是道家吉图。旗摆空中,整整齐齐,要左都左,要右都右。尽管看不到旗手,但从旗姿上可以看出,旗手经过了严格的训练,动作有严格的规范。
姬昌等人惑目相看,闳夭道:“定是邪道无疑!”
从林中闪出五百多人,个个衣着黑袍,高举兵器,十面黑旗横遮正中,杀气腾腾。有人喊了一声清脆的号子,大旗依序分开,露出一匹瘦马。马上之人一身黑袍,白须飘然,生得鸠形鹄面,但双目炯炯,故意拿捏着在戏台上才能看到的架势。跨下之马瘦得只剩几根骨头,一步一颠,慢吞吞走向姬昌等人。
土行孙笑弯了腰,闳夭喝道:“兔孙子,你犯病了?”
土行孙道:“你看看,这马像一条瘦狗!”
马上之人笑着说道:“笑便是得了道,粪土之中亦有道,何况这丑人也是人。”土行孙敛住笑,喝道:“敢骂你爷爷,你可知爷爷是土行孙!”那人笑道:“那我可得离你远点。”土行孙十分得意,道:“知道爷爷的厉害是吧。”那人道:“我怕臭。”土行孙气得“你”了一声,便要动手,那人道:“得道之人怎会如此急切?看来你这丑人尚未得道啊。”说话间已然来到,喊了一声号子,瘦马无精打采停于当地。
那人说话的腔调,说话时的表情,酷似戏台上的表演。适才喊的那声号子,就像戏台上的叫板,难怪刚才敲锣打鼓都有固定节奏。若他生于后世,定是一个铁杆戏迷,或许还能登台演出,可惜当时还没有出现戏曲。
那人一板一眼地道:“锵锵锵,西伯侯听令。”
土行孙终于忍不住,“噗”一下笑了,口水喷得闳夭满脸。
姬昌道:“你是邪道的水圣使吧?”那人道:“我是水圣使,但我道乃圣道而非邪道!”原来,在八卦中北方五行属水,五色为黑,水圣使掌管圣道北方事务,打黑色旗帜,属下圣士均着黑衣。姬昌道:“你是来截杀伯昌的?”水圣使的腔调恢复了常态,道:“西伯侯且听了,伏羲八卦演绎千古,其中不乏正正邪邪,争争斗斗,分分合合,至今只余我圣道和你等自称的正道。我圣道力主走‘强国之路’,政教合一,万众一心,家财入道,大公无私,并使圣道教义流传千古……”
蒙秋打断他,道:“若想截杀西伯侯,就动手吧,休再多言。”
水圣使斜了蒙秋一眼,继续说道:“我圣主原本以为,姬昌既然能作《周易》,明了天之大道,就该将其除去。后来圣主听闻,《周易》是一部奇书,弥纶天地之学问,蕴蓄宇宙之义理,博大精深,玄妙绝伦。圣主道,若《周易》果真暗合天数,则能流传千古,圣道教义必被《周易》之光环所遮掩,即使杀了姬昌,也不能阻止《周易》流传。”
闳夭道:“你的圣主说得极有道理。”
姬昌恍然大悟,道:“你的圣主原本一直想置伯昌于死地,现在却想索取《周易》,细细研读,寻求应对之法,未雨绸缪,是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