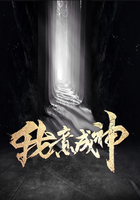这是几年后,我重来古店庄看望何顺仔时发生的事情。
古店庄的面貌依然如故。生着寸草的山和背负着生活压力的古店庄人给了我又一次不小的震颤。何顺仔向我述说的那些过去的故事我已全都写进小说《孽魂》里,算是为古店庄留了一段称不上史料的记载。他本人自然是从来没写过什么作品的,当然那份自诉父母的状词例外。
何顺仔只是笑。那种笑里隐藏的内容太过复杂,我无法用一个准确的词语来概括。我正对他的愁苦面容和他身后背景里的苍凉地貌,想说句话时——何顺仔只是笑。苦涩、艰难、残酷、贫穷、愚昧、偏僻、无奈、烦闷、急躁、懊丧、颓唐、悲哀……在这些很丰富的词汇堆里,我想找寻能包罗古店庄的那个“网兜”,然而,何顺仔疯疯癫癫地跑来打断我的思路说:“正滋生一种可怕的病呢!”
我走来古店庄就必须途经村口的水涝池子,走到那里我特意望了它一眼:干涸、无水,底上有鱼鳞甲样的泥巴层。有两个人蹲在池子沿,一老一小,嘴里无休止地咕哝着,见我来,睁了怪眼看。我不认得他们,也就没有搭理他们。
古店庄里倒是没有见到新奇的图景和惹人惊叹的成就,单就是村里山背后的阴洼多了些黄土堆起的新坟。坟上有茂盛的野草,野草在瘠凉的山地上另树立了一番景色,景色里斜阳低垂,扯出一幕昏黄模糊的暗影,暗影处遍及的是东边天空和西边山隅,余外的天地格调是明朗的,最明朗的当是头顶青天,碧瓦深蓝,亮莹莹的透明若水。
有人走来了,是个女人。胳膊上挎个红柳细条编织的篮子,篮子里装着两只白瓷碗,一只碗里盛着细长的面条,一只碗里是蒸熟凉拌的土豆丝。她迈着小碎步顺着羊肠小路向山后走,两只脚虽交换的勤快却速度缓慢,临到我身边她一闪而过,但我还是认清她的脸上挂满低沉的情绪,缓圭,我暗中心里说,熊家老大熊改的媳妇。我诧异:日暮该归家,她给谁送饭?
月亮上来了。月初的月亮出得早。夜风瑟瑟吹来,脸上和身子都觉得冰凉。“熊家这些年出了不少事。”当我问起古店庄的事,何顺仔收了笑,第一句话就这样告诉我。“熊家的两位老人已经去世,埋在山后,熊家二儿子熊过死了女人,一直再未娶,独自一人闯村子,地不打粮,羊死尽了,连狗也养不住。”“老大熊改呢?”何顺仔不答我,却说:“有个姓赵的阴阳你还记得吗?近些年里他发了迹,富着哩,还有好人缘。”何顺仔望着远山,远山亦如老朽的牛忧郁地卧在天边。何顺子漠然地问我:“你住几天再走?”我说:“一天足了,还有事。”“你是作家,不是要听我讲故事?”他说。这话好像是漫不经心随口而出的,但我清楚,这家伙还是了解我的,知道我的嗜好的。
夜渐渐显露出了黑暗的本质,把夜初朦胧的画面涂抹得模糊起来,呈现出沉重和压抑的感觉。突然,古店庄的后山上响起了一个女人的哭嚎声,使夜颤动了,我有些害怕。何顺仔冷冷地骂:“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装腔作势,死就死了,哭的想见鬼啊!”
“她哭谁呢?不是去送饭吗?”
“送饭!哼!哭儿子!送个屁!”
儿子?我心里掠过一丝惊惧,“怎么了?”
“唉,甭提。娃才六岁,怪可怜的,活着时无人管,熊改和媳妇整天吵骂打架,熊改乱和村里女人行不正经的事,熊改媳妇赌气了和村里几个男人……都那样,没个好熊!只是害了孩子,饥一顿饱一顿,有时,吃不上饭,睡不了热炕;孩子早就生病了,谁管呢?那天,不小心跌下崖,摔死了。”
我有些伤感了。觉着那孩子生命来临得不逢善遇。
何顺仔说:“你伤心什么?熊改媳妇缓圭才不把那当回事儿,你看她哭孩子是吧?才没那爱心呢,像个泼妇,狠心的很!有颗菩萨心肠倒也死不了那孩子,谁能知道她究竟哭哪个?和她有乱七八糟关系的男人也有死的哩。我告诉给你想一想,孩子死了,她不但不反悔,仍然和别的男人钻在一处不说,竟然还跑去请了赵阴阳来,掐来算去说是她兄弟熊过死去的女人来把孩子魂勾去了,又和熊过闹事闹得无法收拾,你说,是个好女人吗?”
熊改媳妇缓圭和熊过曾不止十次闹事儿。我便也想象得出他们那让人悲悯的一场互不相让的斗骂,定是叫骂得山沟震响,使三代祖宗都不安然。还有那个赵阴阳,在旁边添盐加醋火上浇油。我独不能猜测出这件事的结局该是怎样的,因为何顺子说“戏还没演完呢!”
那年,我曾见过缓圭对她公婆玩命,如狼似虎的凶残样子让男人们都哆嗦。现在,她要是和刘家狼们一样的熊过翻脸争胜负,不定会弄出个什么悲惨后果哩。
何顺仔却幸灾乐祸地说:“好戏在后头……”何顺仔变了。正如先前他对我说的:古店庄他妈的邪乎,不是人呆的地方,外人来到古店庄窝上一阵子都会受污染的!何况他这个生在古店庄长在古店庄的人,以后么,他说,不知道自己将会变成什么样的,也许就像人见了就怕就骂的刘家那些“狼”……
我不信。我无话可说。
何顺仔又笑,那笑让我一辈子都忘不掉,他笑的那么认真,开心。可我总能从这笑声里听到哭泣。月亮落了,沉寂在墨黑里的古店庄,荡漾在何顺仔的笑声里,一浪又一浪,声的波纹逐渐扩大了、化开了,飘向更遥远。在他的笑声里还回荡着他的话语:“你吃惊吗?你永远不理解古店庄人的脾性和生活、信仰和追求,是啊,你理解什么呢?你连这个小小的引子都接受不了,还谈什么体验生活?引子——告诉你这只是个引子!”
这一夜,我没有闭过眼。
何顺仔自从状告了他的父母因为对他逼婚后,就出外晃荡了,但终因过于思念古店庄这块地方,不长时间后又回来了,独自一个人过着。他已都三十多岁了,一直没结婚,用他和我喝醉酒时说的话就是“这一生不离开古店庄,也就不结婚。”我无法弄懂他的思想:究竟为什么要过单身?他是古店庄文化程度最高的人,会写诉状,让别的人望尘莫及,感到他高他们一等。大约也正是基于这点原因,古店庄的女人也都从不对他抛媚眼展情怀,见了他,低头匆匆躲走。他也看不起她们,没有对她们用一个男人的眼光审视过,往往视若未睹,不屑置之。对外地女子他间或有顾,然而,对方一听“古店庄”三个字,就认为是魔鬼或虎狼居息的洞穴,便逃之夭夭。
他的个人家庭境况看起来比我想象的还要糟,几乎没有陈设,乱如一团散麻,堆积的杂物遍布这一方小小的古院。令我惊讶的是窑墙上竟挂着一棵少见的塑料草,本来碧绿的颜色被烟火都熏黑了。院子里的陈积物堆在一起。甚至可以从中捡出陈年老帐本来,色黄,纸质低劣,字迹模糊。这本说不上年代的帐本,上面的人名字连何顺仔也没听说过。他对我谈道:“要寻找古店庄的历史是不是?这就是确凿的证物,是那个时期的惟一资料。”我翻开来,某半页上面隐约写着:曹氏古明三年已显考因欠斗米四钱……就这几个字,另一半已无踪迹。我笑说:“古店庄还是文明古地呢!”何顺仔就又用他的那种笑令我张口结舌欲说不能。
早上,何顺仔对我说,你躺着,我去叫荃兴,他还活着。我想想也行,古店庄人我认识的好像没有几个了,又没一块儿会过面,就是见了面是否会毫不拘谨地畅谈也难说。只有荃兴了——一直像是醉着醒不来的一个。
何顺仔走了。走出门时只听到什么东西“咚”的发出一声巨响。
我躺着,懒懒地从疲倦里自拔不出,睁大眼睛瞅布满了乌黑裂缝的窑顶,身体里缓缓流动的是些没有感觉的血液。我仿佛麻木了。古店女老板死了,她的两个儿子、号称刘家三只狼的其中两个相继落入法网。古店女老板的大儿子刘丑银被枪毙,古店庄少了一头恶狼。那坟上竟不生草……老光棍虎山终是未能走出而落入了古店庄的坟墓。万事都通晓的胡老大没有算准自己的年龄和死法,被塌在墙下……古店庄该是面貌全非,有新进展……我进入梦中。曾经活灵活现的人物全都复生,他们倚在村子的脊梁骨上,爬的形状像蚂蚁,啃食着,占有着,脸上是十足自满的大笑,手舞足蹈着。古店女老板满面艳笑,身后出现一只火红的大鸟,抖落满身羽毛,却全是疮疤的干痂,有血在上面耀眼……不知谁扔来半块铁疙瘩,砸得虎山头破血流,他嚎叫着:我不能说啊……狂风卷起来,发出悲壮的吼声,撼得地动山摇,却是胡老大在敲一只破碗……半空里降下一个童子,浑身古装,英俊可爱,举着一面旗子,上写着:救世神童拯救尘世……爬在古店庄背梁上的这些人惊慌失措,逃之不及……
“哪个是云先生?云先生在哪里?”
我被一种粗暴的问话声惊醒,全身大汗淋漓。一骨碌爬起来,失声匆促地回答:“就我一个人在这儿,正睡哩。”我揉了揉睡意朦胧的眼睛,又掐自己的腿方知是梦,可还是惊魂不定,又猛地把头埋在臭烘烘的被窝里,等再从被子里钻出来,身心才恢复了。
地上立着一个人。
似乎很像几年前的何顺仔,二十六、七的年龄,脸上含有小股俊气,就是双眼里射出的光很黯淡,衣服也凌乱。
“你是谁?”我问他。
“村长。”他骄傲地回答。然后问我,“你就是云先生吗?看不出来有啥怪地方,咋能写书的?你来古店庄干啥?”
“只是来看看。”这么直接的问话让我感到回答为难,我笑笑说。
“你来有啥目的?这里没好宣传的。”
“你是说,古店庄不能来?”
“对!不欢迎你!”他毫不掩饰也不顾出口是否伤人,看来他的思考神经非常麻痹,而我大脑里一片迷惘。
“为什么?”
“反正不欢迎你!”
“我会很快就走。请你放心。”
“以后永远也别来!”
我不清楚这其中的缘由,手里死死抓着被角,心里有些烦乱。
他倒像是什么事也没发生,什么话也没有说,表现得一派坦然。他最后看了看我又说:“这是古店庄新定的规,我定的。你走吧!”然后他跨出了门。
我突地笑了一声,自我感觉像是何顺仔那种笑,我叫道:“你站住,你为什么要对我这样?我们之间没有仇怨……”
他回过头,还是那种凝固的表情,说:“对于不是古店庄的人,我都这样。很公平。”
我听到一种脚步声离远了,像幽灵无声地消逝了。又听到脚步声走近了,是何顺仔和荃兴趔趔趄趄地踏进了门,见我有些失态,他说:“我知道了,定是村长牛经来过。他妈的他老想整治人。”
荃兴伸了双手来握我。才四十多岁的人,已苍老的几乎使我不敢相认。身体消瘦且精神极差,宛若一个废人。
我问他们那个村长所定的规矩倒究是出于哪种理由的。荃兴沙哑着声音凑近我耳边,神秘地说:“牛经说外来的东西都邪门,包括人,会伤古店庄的脉气,死人。”
“什么依据?”
“他是赵阴阳的传人。”
下午,苗家老汉在古店庄哭天嚎地,拽着瘸腿到处跑,嘴里哭叫着:“谁来救救我的小孙子啊?我给他当儿子当孙子都行,只要能救活我小孙孙……米斗、猫蛋、亮卡,快些来啊——”
我在这种紧张嚣乱的呼叫声中匆忙奔出何顺仔的家,却看见何顺仔蹴在地畔,睁了冷漠的眼望着对门苗家院子里乱糟糟的人影。
“出了什么事?”
何顺仔头也不回,说:“又死了一个。”
“得病?”
“嗯。”
“为什么不送医院?”
“古店庄没有医院,没有医生,只有阴阳。”
“阴阳又不是医生,我说……”
“古店庄的阴阳能看各种各样的病,古店庄人根子里都知道阴阳能看病。” “怎么看?”
“烧纸画符,念经送律,求神问卦,打五雷碗,摇神铜铃,洒七色水,杀公鸡头。”
“哦——因而就死了不少人,对不对?”
他呆若木头,一句话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