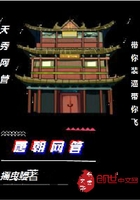嬴淮极想撇清从舟之嫌,但也只能推诿道,“此事蹊跷,多年前的事或许已难查证。”
但王稽一拢袖又道,“此事千真万确。当年微臣曾派暗间潜伏于虞从舟身侧,她亲眼见他梳拢魏臣须贾,密谋将私通齐国的罪名栽赃与范相,以绝隐患。”
江妍当年,真的把他的每字每句,都一一报与秦人的么?虞从舟疏冷的心里又多了一道冰痕。
“好个尽绝后路,原来你自己也知道寡人绝不会饶过你。”秦王见他已是默认,一拍案道,“既然是范相的仇家,寡人绝不会轻易放过。就算是魏国相邦,寡人也要翻开赵魏二国将他挖出来,如今,真凶原来竟是赵国虞卿,寡人亦会为范相做主。”
嬴淮深深一闭眼,不知这死结要如何去解。
“将他押下去,明日,寡人亲自监斩。”
从舟被侍卫拖起。他并无惧意,只是盯着秦王的双眼,又一字一顿地恳求道,“还请秦王放了平原君。”
“秦赵向来交好,寡人只是想替范相复仇,自然会送平原君安然返赵。”
而朝堂百臣中,公子市逆着殿外阳光,看着虞从舟被押下的背影,忽而想起什么,目光愈加沉冷
秦宫地牢,一片冥寒。
一个红衣女子托着茶盘走下地牢。她略带英气的妆容非常美艳醒神,一身宫中近侍的明媚红装令她更显挺拔,与牢中幽寂立成鲜明反差。
她走过几格牢室,空空荡荡并未囚人,她心中略微起疑,不知道公子市差她将茶盘送与何人。
转过一弯,她看见角落的囚室里押着一个白衣囚犯,那人垂首跪立着,似乎早已陷入昏沉,只是双臂被链锁缠绑,拴束在墙上,所以并未倒伏在地。
她遥遥望见,手指已忍不住微微颤抖,那人一头微卷长发泻在肩旁,隐隐仍散着光华,虽一身囚锁,卑微入尘,但身姿铮立,并未输了傲骨。
手中的颤抖愈发难控,茶盏在盘托上臻臻晃响。她顿时一回神,直觉此处相逢,只怕另是一场陷阱。她压下情念,立刻强压身上颤抖,摒着呼吸静静立稳。
但那点茶盏相碰的脆声,已令从舟渐渐有些清醒。他微微睁开眼,却在那一瞬间,闻见幽幽百合花香……
……那错落三生,以为永世难寻的伊人香气。
他蓦然抬首,一记急喘令他全然醒透。不须要寻觅,那一瞬间他已对上她的双眼,不敢置信竟在临别之际还能见此回光一照。
幽牢之中一片肃杀,唯有红衣艳唇的她,犹如霞中桃花,颠倒冗世韶华。
似乎前生后世压抑下的刻心恋想,都在这一刻倾闸泄下,情如潮涌,将他的心悬至飞腾浪尖。
“窈儿……”
破浪而出的,竟然只是这咽声一唤,似乎在心中喊过千遍万遍,这个名字便从此刻进心房,极难唤出声形,强推出喉,一声声已带着心窍残血。
楚姜窈立在从舟面前,强忍心绪,不让面上有一丝表情。公子市既然诓她来此,必非偶然,只怕此时牢中还有他人静观。
虞从舟嗔痴一笑尚未涌上眼梢,但见姜窈冷冷望着他,似有仇隙,他心中遽然一冷,难道,又只是自己的一场梦?
他低下头含咬嘴唇,牙关一使力,唇瓣尽碎,鲜血溢出,疼痛瑟骨,但他却狂喜般抬眸,纯纯漾笑,带着浅浅泣喘喜悦道,
“不是梦,这不是梦!窈儿,真的是你!你还活着……”说到此处,泪水无边漫溢,再说不出别的。
原来天亦有情,命亦有恩,他的窈儿还在人世,不曾消失!
他失控地跪行两步,想向姜窈靠近些许,但枷锁啶咛作响,拴住他双臂令他全无自由。
明知无解,他还是用尽全身力气,想要挣脱几分,但只是令身上留下浅浅深深地瘀痕。
他此时方恨这千般束缚,万般难舍,原以为,早已心死如沉冰,狱中,笼中,链中都是一样,但原来,有窈儿在的地方,他还是渴望哪怕一线生机。
挣扎得失了力气,他静静地死了心,隔着囚栅默默仰望姜窈,自己也不知道心里是不是存了一丝盼想,盼她能向他走近几分,哪怕只是半尺几寸……
但姜窈只是立在原地,一言不发,神色冰冷地睨看着他。
难道窈儿又不记得他了?
若真如此,也好……他原本,也只剩一天的时间了。记得他,也只是徒添离殇。
他便不再说话。趁着最后的时光,他痴痴看着姜窈的脸。从未见过她飒爽红装,束腰戎服,那份夹杂着妩媚的英气,令他刹那间向往起与她纵马坝上,飞驰瀑中。
以前看惯了她素妆淡袄,清新相随,此时此间,她美的这般耀眼直率,不觉让他想起,很多年前她嬉笑的那一句“小媚贻情”。
从舟忽然觉得很幸运,虽然身陷囹圄,但竟然最后一眼,是她。知她一切安好,见她美得比从前更醒目动人,他不知不觉染着情动的笑意,喃喃自语,
“上天待我,真的很厚……原以为要历三世劫难,赎尽债孽,才能求得再见你一面,没想到今生还未了断,就已经许我见到你了……”
楚姜窈不堪这声声入耳,险些就要把持不住,她强抑着心中潮涌,决然转身向牢外走去。这场狱中相逢必有蹊跷,她不可在此久留。
虞从舟眼睁睁看着她远远离去,经年重逢,却又是今生最后一次相见,他隔着囚栅的缝隙,凝着她隐约的背影,分明想看的清楚些,泪却又斑驳了视线。
窈儿真的又已经忘了他了吧?多少次在梦中憧憬与她重逢的那一天,其实他,还有一点贪念,他还想,再抱一抱她,闻一闻她发间的香气……
他立刻甩了甩头,自己又在贪心什么。即使回到从前,他也不想让窈儿再跟着他受这一生两难无解之苦,如今窈儿能安然脱险,他更不可牵绊她什么。
他极目去寻,依稀还能看到那道红色身影,他忽然注意到,窈儿双手托着茶盘,她的左手……竟然……她的左手真的治好了?!一定是哥哥,一定是哥哥救下了她,医好了她的左手。
哥哥果真是神,每次都能救窈儿于危难……他一生最后的歉疚似乎也得了些安慰。灵动如她,终于又寻回了蝴蝶的翅膀!
他喟然一笑,哥哥也狠心,这么多日子来,都不曾传一点点消息给他。是怕他会搅乱他们的生活?他怎么会……他只是想知道她还安好。
直到再也看不见她,从舟默默低了头,原来生死重逢会是这样陌生,再度诀别可以这般平静。
忽然听见数人脚步沉沉,走下地室,姜窈倒着步子,被那群人逼进狱中长廊。虞从舟心中一惊,这才发现是公子市挑着阴阴冷笑,带着王稽与数名死士步入牢中。
“怎么,遇见小情郎,也不多说两句?”
“他只不过是属下从前行事的宿主。是属下最不愿再见到的人。”
被这一句梗在心间,虞从舟钝钝地看着她,原来,窈儿并没有忘记他。
但为何她又听命于公子市与王稽,哥哥怎么可能让她重陷水深火热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哦,是么?我看,你是被他策为反间,欲潜伏于秦宫才是吧?前两****在宫中侍卫营里看到你,就觉得好生面熟,今日在殿上见到虞从舟,才记起,原来是从前在茔城的地牢里见过。”公子市凑近她道,“那时你对这虞小子,可是情深意浓,一鞭也舍不得他捱啊!”
“那时不过是刑场作戏,演给他看罢了。”
一旁立着王稽,他而今已经不大把公子市放在心上,因这一年来秦王凭着范雎的谋划,已废黜了公子市的王储之位。他此时便向着自己营中人,“那茔城之事,小令箭的确是为了把和氏玉的下落透漏给公子您。公子未追上杜宾,倒也不能全怪小令箭吧。”
“哼,告知我了?只怕是诓我离开,好助这虞小子逃走吧?”公子市戳了戳小令箭的肩,“临场作戏?别以为我看不出你早已经是假戏真做!那狭荣道呢?是不是你动了恻隐,掖着赵人的军机没有传?!”
王稽又岔话道,“公子又错怪了。她冒死递了消息,是小盾牌路上被赵人截下,受了腿伤,才延误了军情。这是小盾牌都招认了的。”
小令箭心中痛楚涟涟,小盾牌就是因为这个,被死士营处死于白芜崖下的么?明明她本想要换他一命,他却连最后的救赎,都决然地背在自己身上。
她的生命上背负着他的沉重,更不敢有一丝晃神。她静静答道,
“属下只是受命潜伏,从不曾心生私情。”
公子市打量着她,甩着扇子退后几步道,“也是,他是赵人,你若敢爱上他,按着死士营的规矩,绝对让你死得很惨。”
“属下怎会爱他,恨他犹自不及!他两度处我极刑,令我左手失残。死里逃生后,他又将我囚在身边为奴。及至他身获重罪时,又拖出我替他领罪受死。属下对他,恨有九重,又岂会爱他?!”
“若真如此……他明日就要处斩了,倒也算是替你复仇了。”
小令箭刻意漫着恨意的双眼忽然打了个冷战,公子市饶有兴趣地斜眸看着那一瞬间的变化,
“你这眼神,当真是恨么?好,今日王大人也在,如果你营中这小妮子对赵人生了私情,还敢潜入秦宫,王大人该知道如何处置她吧?”
他又贴近小令箭,俯视着她,“要想证明自己,倒也不难。小令箭,若你真的恨他,我赏你这个复仇的机会,”公子市笑得愈发挑衅,一字一顿道,
“我赏你亲手杀了他,一剑刺死他。”
小令箭强压胸口起伏,只听公子市又一次催问,“嗯?”
虞从舟没有想过自己的存在会成为验试窈儿忠心的威胁,愈发不解为何自己总是带给她危险。
原以为是重逢,但只是另一场死别,不过一刻十分的时间,竟又要换了阴阳,或许他与她,注定只能是相隔两界。
他接着姜窈方才带着恨意的话道,“窈儿,我总是伤害你,对不起,一直想还,却只是越欠越多……我今生已没有剩下什么能拿来还赎给你,若能在你剑下死,反而让我少些歉意。”
一旁王稽等诸人倒是愈发吃惊,方才只有他与小令箭二人时,似乎已听出他对她深情蚀骨,而现在,小令箭的身份明明白白摆在他面前,过去多年,她不过是个受命潜伏在他身边的秦间,他竟然并不吃惊也不愤恨,还是一心一意地想要把命来赔她。
姜窈一动不动地立在囚栅边,看不出是情满溢,还是恨满心。
“我害过你,伤过你……”虞从舟抬起头,眼中闪动着愧疚,但看到她面容时又不禁抿起一抹柔柔的笑容,
“你不必对我心软。”
“我对你从不心软!”姜窈忽然开了口,语音听来生冷怵心。
虞从舟从未见过姜窈狠戾的眼神,第一次看见,他唇角微微战了战,但依然尽力僵着那抹笑,只是一丝丝冰凉的痛意似乎绣进心里。
这是怎么了,这明明是他想要的答案……
他抿住唇,静静低下头,默默的等候。片刻后,听见金属的铖铖划响,是姜窈抽出佩剑的声音。他随着那声音闭上双眼,只盼窈儿不要犹豫,莫叫公子市起了疑心。
他明白,姜窈总是强装坚强,但她心里或许比他更煎熬。要怎样告诉她,死在她剑下,他不痛,也不伤心,因为能见到她仍在人间,已免去他受轮回三生的历劫等待。
他感觉到剑气就逼在他胸前数尺,却迟迟没有痛感。
忽听公子市道,“怎么,太长时间不用剑,忘了剑法了?要不要我,示范给你看?”
话音刚落,公子市缓缓拔出剑来,起势要向虞从舟刺去。姜窈心中一惊,若公子市下手,从舟必死无疑,她一瞬间乱了心寸,蓦然出剑,抢在公子市之前刺向从舟心口。
剑风凌厉,似乎炙烧着空气,散着焦灼的悲意。但她的剑尖顶上从舟胸口的那一瞬间,她才明白自己完全舍不得,下不了手。
利剑刹那在她手中停滞,但下一瞬间,她顿时感觉到从舟猛地将身体一冲顶,迎着锋刃,狠力地将自己的胸膛扎透在她的银剑上。
二人力量速度的起承转接几乎天衣无缝,在旁人看来全然如同姜窈狠下杀手,一气呵成,长剑刺穿他的心扉。
姜窈心中痛意凌迟,原来从舟早就料到她会下不了手,早就想好会为她演完最后一幕,用自己的心力弥补她恍惚的定力。
虞从舟已没有力气再跪立,但身体悬挂在她的剑锋上,又动弹不得。他止不住痉挛,闭着眼死死咬定唇角,不忍心发出半声痛呼。
见他胸口的鲜血在自己剑下漫溢而下,姜窈只觉从未这般失措过,下意识地退缩了几步,横剑整根带出。
锐利的剑刃在他胸腔里第二次挫划而过,从舟痛得再也扣咬不住,一松嘴喷出一口血雾。
他渐渐失了意识,懵然侧倒在冰凉地面。
他很想最后再看一眼窈儿,但他又舍不得,自己的眼神里还是会略有悲意吧?哪怕仅是一点点,只怕也会更伤窈儿的心。
他躺在温热的血泊中,带着仅剩的一点遗憾,眉宇慢慢松了挣扎,痛苦散尽,神态渐渐如安然睡着的孩子。
他……死了?
难道,他最后对她说的话,就只剩那一句“你不必对我心软”?
姜窈被空前的惊恐悲惧压抑全身,面上全无一丝表情,公子市打量着她,倒不知该不该算她过了这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