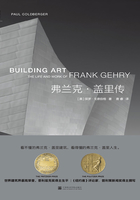“老人终于发现,你们俩时常在凉台上眉目传情。有时,你甚至不去上课。中午也手拿书本坐在凉台的一角。你忽然喜欢独自一人念书了。比普罗达斯找我商量。我对他说:‘大叔,你不是早就想去贝拿勒斯吗?你现在就去圣地进香吧!姑娘留在我这里,我来照看她。’
“比普罗达斯进香去了。我把姑娘安置在斯里波蒂·查特吉的家里。让他冒充姑娘的父亲。以后的情况,你就都知道了。我把事情的始末开诚布公地都对你讲了,我也就如释重负,感到很高兴。这真像一篇有趣的小说。我有时想,把这所有的一切都写出来,印成一本书,该多好啊!但可惜我不是作家。我听说,我侄子颇有创作才能,我打算让他来写。当然,如果你能与他合作,共同来完成,那是再好不过了。因为故事的结局,我还不太清楚。”
赫蒙托没有理会佩里松科尔末尾几句话,问道:“库苏姆丝毫也没有反对过这件婚事吗?”
“嗯,”佩里松科尔说,“她是不是反对,这就很难说了。孩子,你知道,女人的心是很难猜度的。当她们说‘不’的时候,可能要理解为‘是’。搬到新家的头几天,因为见不到你,她几乎要发疯了。我看得出来,你从哪里得到了消息。每次去学校时,你总是手拿书本,像迷了路似的,在斯里波蒂家门前徘徊。显然,你不是在寻找去大学的路,而是紧紧盯着良民百姓家里的窗户--这只是昆虫和害相思病的青年的心所要找的路。当时的所见所闻,使我很苦恼。我知道,这对你的学习极其有害,而且姑娘的处境也很可怜。
“有一天,我把库苏姆叫来,对她说:‘孩子,我是一个老人,在我面前,你不必害羞。我知道,你在思念谁。那年轻人的日子也很不好过呀!我衷心希望你们能生活在一起。’
“库苏姆刚一听完,就放声大哭起来,跑走了。以后,我就常去斯里波蒂家里,把你的一些情况告诉库苏姆,她逐渐地克服了羞怯。后来,我们每天都要谈论这方面的事,而且我告诉她,除了结婚之外,是无路可走了。库苏姆说:‘这怎么行呢?’我说:‘没关系。我们把你当成库林人家的女儿。’经过多次开导规劝之后,她要我探听你对这件事的意见。我说:‘那孩子都快想疯了,有什么必要对他讲这错综复杂的关系呢?如果这件事安稳平静没有波折地过去了,那就大家满意,万事大吉。特别是这些话永远也不会泄漏出去,何必要节外生枝,使那不幸的人终身痛苦呢?’
“我不知道,库苏姆是不是明白了这个计划。她有时哭泣,有时沉默。最后当我说:‘这件事就算了吧!’她又心慌意乱起来。既然到了这个地步,我就打发斯里波蒂来给你提亲。我知道,你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当时,结婚的一切事宜,就这样定了下来。
“结婚前不久,库苏姆变得非常固执,我怎么劝她也不顶事。她握着我的手,或者抱着我的脚说:‘大叔,这件事就算了吧!’我说:‘讲什么傻话。一切都已决定了啊!现在怎么能半途而废呢?’她说:‘那你就放风出去,说我突然死了吧!把我送到别的什么地方去,藏起来。’
“‘这样做,那孩子会怎么样呢?’我说,‘他多日的思想,眼看明天就要实现了。他现在高兴得了不得,仿佛进入天堂。如果我今天突然告诉他说--你死了,那么,第二天我就不得不把他的死讯带给你。这样,当晚又会有人把你的死讯告诉我。我这么大一把年纪的人,难道要落个谋杀妇女和婆罗门的罪名吗?!’
“没多久,选了一个良辰吉日,举行了喜庆的婚礼。我终于摆脱了自己的沉重负担。以后的事情,不用说了,你都知道。”
赫蒙托问:“你对我们,想要做的都已经做了,那为什么又要把这个秘密泄露出来呢?”
“我已经知道,”佩里松科尔说,“你妹妹的婚事安排好了。我心里想,我已经玷污了一个婆罗门的种姓--当然,这是我的职责。但是。现在又有另一个婆罗门面临玷污的危险。这次我有责任来阻止。我已经给他们写了信。我说,我可以证明--赫蒙托娶了一个首陀罗的女儿。”
赫蒙托竭力控制住自己,说道:“我打算休弃这个女孩子,她会怎么样?你能收养她吗?”
“该我做的事情,我已经做了。”佩里松科尔说,“现在养育别人遗弃的妻子,可不是我的责任。外面有人吗?给赫蒙托先生端杯冰镇椰子汁来,再拿点酱叶来。”
赫蒙托没有等这份清凉可口的饮料端出来,就起身告辞了。
4
朔月的第五天,漆黑的夜晚。没有鸟鸣。池塘边的荔枝树,仿佛是深色画布上涂抹的一道墨迹。在这黑夜里,只有南风像梦游者一样,盲目地转悠飘荡。天上的星辰,以机警的目光,竭力想透过黑暗来发现人间的奥秘。
卧室里没有点灯。赫蒙托坐在靠窗子的床上,凝视着前面的夜空。库苏姆躺在地板上,双手抱着他的脚,并把脸偎依在这双脚上。时间像平静的海洋,停滞不动。似乎是“命运”这位画家,在无边无际的夜幕背景上,创作了一幅永恒的画面--四周死一样的寂静,中间坐着一位威严的法官,他的脚下匍伏着一个有罪的女人。
拖鞋声又响了。霍里霍尔·穆库杰走到房门口,说:“我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我不能再等待。快把这姑娘从家里赶出去!”
库苏姆听到这些话后,顷刻间以自己毕生的激情,更加紧紧地抱住了赫蒙托的双脚,不停地吻着,并以额触脚。最后,她松开了丈夫的双脚。
赫蒙托站了起来,对父亲说:“我不能弃绝自己的妻子。”
霍里霍尔咆哮如雷,吼叫道:“你难道要弃绝种姓吗?”
“我不在乎种姓。”
“那你也一起滚出去!”
1892年4月
《祖父》
一
从前,纳因觉尔地区的地主,曾以老爷的声誉而着称于世。那时代,追慕老爷称号的理想,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人们为荣膺老爷称号,不得不进行难以忍受的苦行,正如现在封建王公垂涎拉叶伯哈杜尔头衔,不得不赶时髦,学习跳舞、赛马、寒暄等西洋生活方式。
纳因觉尔的老爷们曾以穷奢极欲而遐迩闻名。他们穿上撕去边沿的达卡产的细布衣服,因为粗硬的毛边,会磨损他们异常娇嫩的老爷气质。他们肯耗费十万贯钱,为小猫举行婚礼。据说有一次,为庆祝一个节日,他们发誓要把黑夜变成白昼,点燃了数以万计的灯火,从空中飘撒下真银制作的缤纷丝带,来模仿阳光。
众所周知,那个时候,老爷们的老爷气质没有世袭下来,他们像一盏有过多灯芯的油灯一样,在短暂的挥霍中,耗尽了自己的油,很快黯淡而逝了。
我们的盖拉什钱德拉·拉易·乔杜利,就是负有盛名的纳因觉尔地区一位家道败落的老爷,也是曾经灿烂一时、如今行将熄灭的这盏长明灯的最后遗民。当他出生于人世,灯油已沉底,所剩无几。他父亲去世时,举行了显赫的丧礼,纳因觉尔的老爷气质闪现了自己最后的光亮,突然黯然无光了。全部财产为支付债务被拍卖掉,剩下的钱财,已不能维持祖先的荣耀。
所以,盖拉什老爷携带自己的儿子,一道离开了纳因觉尔,来到加尔各达定居--他的后嗣很快抛弃了自己唯一的女儿和世道日下的人间,归了西天。
在加尔各达,我们是相邻。我们的历史与他们的历史是截然相反的。我的父亲依靠自己的奋斗,流血流汗地挣钱,他从来不穿低于膝盖的围裤,从不乱花一个铜板,他从来没有想通过挥霍的炫耀、博取老爷头衔的任何念头。我是他唯一的儿子,受到了良好的现代教育,拥有适应于维护自己身心和名誉的足够钱财,对此我是感恩戴德的,也引以为荣的。我觉得,贮藏在铁皮保险箱里的父亲公司钞票,远比家徒壁立的库房里的祖传老爷气质的光辉历史贵重千百倍。
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当盖拉什老爷以自己往昔骄傲的倒闭银行名义,开出又长又多的空头支票,支付别人的债务时,我感到特别不堪忍受。我还仿佛觉得,因我父亲靠自己双手发财致富,盖拉什老爷打从心眼里瞧不起我。我愤怒地思量:谁该是被鄙视的人呢?整个一生,忍受残酷牺牲,抵制种种诱惑,不屑于人们脸孔的鄙夷表情,通过孜孜不倦的、合乎理性的聪明才干,克制所有矛盾和困难,掌握一切有利时机,就这样依靠自己的双手,用一层层金银财宝叠起了高耸入云的宝塔,但是只因为他没有穿齐膝的围裤,被认为是小人物。世道是如此不公正。
那时我年纪轻,血气方刚,唾弃和厌恶这种迂腐的风度。现在随着年龄增大,平心静气地思忖:这里面也并无什么害处。我有万贯家产,不愁吃穿。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如果以清高为乐趣,这又何损于我!相反,那个可怜家伙会由此得到慰藉。
应该说明,除我之外,没有任何人恼恨盖拉什老爷。因为世上还没有遇见过如此无私欲的人。在各类事务和悲喜际遇中,他都竭尽全力地帮助别人。他参加邻居的一切典礼和节会。他不管遇到老和少,都以礼相待,笑容可掬,慈爱地同别人攀谈。他会毫不倦怠、温文尔雅地向人问安,询问家庭琐事。所以他一遇上谁,一串串问话就没有个完:“我的好朋友,近况可佳?身体康健?夏西挺好?大老爷高寿欢乐?听说默杜儿子发高烧,现在复原了吗?我好久没有见到赫利吉勒利老爷,他一定很愉快吧!你的拉河尔有什么消息?你家里人也好吧?”
他是位爱好整齐清洁的人。衣服布料不多,但总是细心地、有规律地把衬衫、围巾、裤子、破旧的床单、枕头套子和小线毯,拿出户,晒太阳,抖开,挂在绳子上,摺起,悬在竹竿上,最后又妥善地保存起来。乍一看,使人觉得一切安排得井然有序,美观大方。屋内仅有的几件家具布置得既惹眼又恰到好处,满屋生辉。给人印象,仿佛他家里还藏有很多东西似的。
他经常在缺乏仆人的情况下,紧闭柴扉,费九牛二虎之力,熨烫宽大的围裤,缝补背心和衬衣的袖口,并做一些仆役的工作。随后,打开房门,接纳朋友。
他的地产和财富早已丧失殆尽。但他费了好大周折,才从贫穷的大嘴里,保存下一个贵重的装花露水的银瓶、一具玫瑰香盒、一个小金盒、一个银色的水烟袋、一条珍贵的披巾以及旧式的礼物。一遇上机会,他就把这些东西统统搬出来,布置得琳琅满目,借此维护纳因觉尔举世闻名的老爷尊严。
现在,盖拉什老爷尽管没有了土地,但在自己的谈吐中,依然流露出一种骄傲的神情,仿佛这种骄傲一直维护着自己对祖先的职责。大家不时怂恿他,挑逗他,从中寻取乐趣。
街区的人们管他叫祖父。在他那里,经常聚集着很多人,但他囿于贫穷,无法增加烟草的开销。所以,邻人总买来一二赛尔的烟草,助兴说:“祖父,尝一尝,品品我们手里的伽耶产的精美烟草!”
祖父吸了一两口后,说:“好极了!老弟,烟草是精美绝伦的!”随即,他吹嘘自己吸过价值六七十卢比一斤的道兰产的名贵烟草,询问:“我不晓得哪位仁兄,想尝一尝它们的味道,我还保存一些。”
大家明白,假如果真有人想尝试,他一定说,钥匙不知放在何处。然后搜寻一番,告诉大家,老仆人的儿子把它弄丢了。“你们兴许不能相信,这个老人懵懵懂懂的,总是遗忘东西的去向。虽则笨拙了些,但我不想辞退他。”
老仆人格兰什毫无怨言地忍受了全部的责难。
这样,大家异口同声地说:“祖父,不必寻找,您这烟丝味太浓,我们消受不了。还是这种烟好吸。”
祖父一听到这话,如释重负,再也不唠叨,脸上绽开了笑容。当大家起身告辞时,他会突然开口说:“哦,想起来了,你们什么时候到我家做客用膳。请说个日子,老弟!”
大家说:“看着办吧,定一个日期吧。”祖父立刻接口说:“这正中吾意。就定在下霏霏细雨,天稍凉快时,不然,在炎热的夏天,丰盛的饭菜要糟蹋掉的,因为大家准闷热得没有胃口。”
当雨季来临,任何人都不去提醒祖父的允诺,一当触及这个话题时,大家提议说:“倒霉的毛毛雨,下个没完,兴头委实提不起。落完了再说吧。”
他住在狭窄的租房里,深感有失体统,寒酸难堪。诸亲好友也在他面前,对他的处境深表同情。但谁都知道,若要在加尔各达租到一所租金合适的寓所,真是难于上青天。很多日子以来,邻居出谋献策,为他寻找租金适合的大房子,但全落空了。最后,祖父仿佛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说:“算了。不过,我与你们住在一起,感到心情愉快。我在纳因觉尔有富丽堂皇的住宅,但我又怎能留在那里呢?”
我相信,他本人定知道,大伙了解他的境况。当他赋予昔日的纳因觉尔以现代的面貌,加以显示,当人们也在其中推波助澜时,他暗自思忖:相互间的欺骗,仅仅是出于互相表示友好情谊的原因。
然而,我十分反感,年轻时就有压抑别人那种洁身自好的邪念。与成千上万的滔天罪恶相比,愚蠢更使人难以忍受。盖拉什老爷并非真的愚昧无知。在很多事务方面,大家都乐意取得他的帮助和建议,但一触及纳因觉尔荣光的话题,他就不注意说话的分寸,缺乏应有的常识。由于他成为大家怜爱和取乐的角色,任何人都不反对他那种天方夜谭式的谈天,他也就漫无边际地胡诌。当旁人寻寻开心,或逗他取乐,用荒谬绝伦的夸大方式,绘声绘色地描摹纳因觉尔的荣光时,他会毫不犹豫而且十分庄严地接受这一切,甚至他在梦境里也未曾怀疑过,别人会不相信这一切的。
我常常想,老年人依赖空中楼阁的幻想生活着,并遐想那种空中楼阁是永存的。而我仅用两发炮弹,就能在大庭广众面前,轰沉他的空中楼阁。猎人见到鸟儿停歇在树枝上,就想用子弹击中它,孩童见到山顶上的奇形怪石,就想把它推翻下山。当摇摇欲坠的什物被一个东西卡住,仿佛那件什物只有被推倒之后,才会显露自己的完美本质,而欣赏者的心也因此而得到满足。盖拉什老爷的画板是那么脆弱,正如他的非真实的话是那么纯洁无瑕,它们在真理枪口面前,如此欣喜若狂地翩翩起舞,以致人们心里立刻产生消灭它们的念头--我仅仅因为十分懒散懈怠,遵循大家的习俗,而没有干预这件事。
二
当我分析盖拉什老爷对往昔的情愫时,发现自己内心存有一个不满他的更深的理由,我有细细叙述的必要。
我尽管是有钱人家的纨子弟,但还是没有虚度年华,按时通过了文学硕士,年轻时也没有交上坏朋友,沉溺于放浪生活。尽管双亲死后,我成为主人,但本性仍没有变坏,品行依旧是白璧无瑕。我的相貌也是绝顶漂亮。如果我用自己的嘴,称赞它的漂亮,别人一定会说我自吹自擂,自鸣得意。但平心而论,这种称赞并不过分。
所以,无可置疑,我是稀罕的乘龙佳婿,在孟加拉婚姻市场上,有着百倍的身价。我发誓,一定要在婚姻市场上,攫取自己的全部价值。我心目中的理想配偶是,一个百万富翁的无与伦比的绝色和富有教养的淑女。
省内外人络绎不绝,前来向我提亲,表示愿出一万、二万卢比的相当可观的陪嫁。我毫不动心地在天平上,衡量这些提议的份量。我觉得,仍没有谁家之女能有配得上我的价值。最后,我的想法犹如帕沃波特诗所描绘的:在这个世界上,
时间是无休止的,
空间是无穷无尽的,
最后或者可能
会诞生出一位与我并驾齐驰的美人。
然而,当今的衰弱时代,褊狭的孟加拉,是否会产生那种尽善尽美的人,颇可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