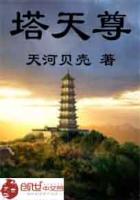在茅盾的早期小说中,写于1929年的《虹》,同它前后的《蚀》三部曲和《子夜》相比,较少受到学者的青睐,这种情况直到最近方有所改变。像三部曲一样,“时代女性”仍是小说的主角,但梅女士与《动摇》里的孙舞阳、《追求》里的章秋柳相比,由于折中、理性成分的增强,个性却显得不那么鲜明。和《子夜》相比,在表现都市生活方面则不够广阔、深刻,“现实主义”的艺术技巧还不够成熟。但在茅盾的创作历程中,它达到了作者的既定目标,即给小说的叙事成功地输入历史展开的内在动力,确定了“革命”主体与历史“必然”之间的主客关系,从这一意义上说,《虹》标志着中国小说形式现代性的基本完成。
《虹》仍属阴性,却明朗、愉悦,受温馨的阳光爱抚,作调情状,在短暂的“幻美”里,尽情展示色相。这与《蚀》不同,“蚀”意象是“阴”气深重,带来黑暗、险恶与幻灭。因此《虹》意味着过渡,像一座桥梁,使作者走出“都市”颓废的“冥国”而回到“世间”。然而大地之春还没来临,作者感到不踏实,觉得《虹》是一座用语言构筑的“幻美”之桥,仅是一种“虚幻”,决非完美,且有可能重新堕入黑夜。
《虹》呈现了“过渡”形态所有的纷纭变幻,捉摸不定。梅女士的肉身指符也如七彩缤纷,受欲望语言的诱惑,“革命”的客观再现仍然险象丛生。作者似乎意识到,用女身作为历史的载体终究是脆弱与虚妄,因此梅女士更受一种“方向”意识的控制;此时“历史”作为时间的载体,更具阳刚之性;它与梅女士这一时间载体分离,又潜入其体内实行颠覆与改造,目的使之成为“历史”的副本,同时也使“历史”变得更迷人可亲。
这部小说在茅盾走向所谓“现实主义”的过渡中,仍富于变量,但处处可以感到那种更强的掌握。由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介入,使“现实主义”的创作过程及其再现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变得复杂化了:“现实主义”——就《虹》的个例而言——并非反映世界的镜子,亦不是认识世界的窗口,而想象的“历史”成为艺术再现的“中介”,与小说人物、叙述者、作者之间构成新的关系,产生新的紧张。紧张的征兆之一是,一方面叙述者变得更全能全知,再现世界的终极目的是确立革命的“历史”这一主体;这是“真理”的化身,具有导师的仁慈、先知的神秘。在如此“客观”再现历史时,叙述者需要一种坚定自信的声音,力图拆除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作者对于自己的“主观”深怀疑惑,甚至恐惧,当他意识到这一“历史”乃是他自己笔下的“虚幻”时。这一“历史”颇像柏拉图所说的代表神性的“理想”,小说家有可能因为拙劣模仿“理想”并误导民众,那就要被逐出“理想国”。
那种处于运动过程中的张力,始终贯穿梅女士的形象创造中:她凭着“战士的精神向前冲”,而“将来”是“不可知的生疏的世间”。在这样紧迫地要求再现“历史”、但尚未得到来自革命权威的“面对面”指令的情况下,作者呼唤“神”的指引。于是因缘凑巧,“北欧神话”在《虹》的创作中起了特殊的作用。梅女士所蕴含的“寓言”性即作者力图抽掉她的“女性”与“母性”之后所体现的“神性”。
《虹》的寓言性在于:“历史的必然”的叙事含有“真理”的自足性,朝向自由目标展开,而梅女士作为一个具普遍意义的现代英雄人物,既接受历史的“教育”和“改造”,又成为推动历史的一分子。这部作品不仅为茅盾的思想与艺术转型印上象征的标记,其历史叙述模式也为后来进一步开展的社会运动提供了艺术形式的先例。这在类型上既呼应西欧18世纪末由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所开创的描写“成长小说”类型,也直接受到世纪初法国“纯粹主义”(Purisme) 的启发,所谓“那种渴求着合理的坚固的社会组织的意愿,不失为现代知识阶级的健全心理的表现。”当然梅女士式的人物也可以在当时茅盾已经接触到的苏维埃“写实主义”文学里找到楷模:“这个写实主义的人物当然不能是个人主义的英雄,而是勇敢的有组织的服从纪律的新英雄。”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呼唤那种体现新民族精神的小说“英雄”,到此时方有了着落。然而其真正的发达则要到1949年之后,大量出现的革命历史小说,尤其是那些带有“小资”情调的长篇小说,如《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三家巷》等,其精神脉络还不得不追溯到《虹》。如果忽视了《虹》而对二三十年代的文学作概括性判断,恐怕要出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