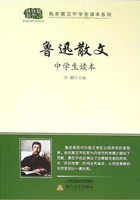小说的开头一段用拟人化手法描写“南窗的小书桌”,为整个故事担任了重要的功能:设定了范围、性质、语调和气氛,并蕴含“暗示”的叙述策略。两朵半开的红玫瑰“宛然是淘气的女郎的笑脸,带了几分 ‘你奈我何’ 的神气,冷笑着对角的一迭正襟危坐的洋装书……”。这一女主角的画像——可爱而具挑战性——首先进入读者的信息接收系统,起一种主宰整个阅读经验的作用。所谓“脱不掉男女关系的小说”,正点明这个故事的内容。诙谐的叙述口气与书桌上杂物的凌乱秩序不相协调,产生某种张力。最后的象牙兔子的一行刻字:“娴娴三八初度纪念。她的亲爱的丈夫君实赠”, 点出了男女主角的名字及两人的夫妻关系,但最后一句“然而 ‘丈夫’ 两字像是用刀刮过的”,虽然没有明指是谁刮的,但埋藏着针脚,呼应了前面这兔子“怨艾”的红眼睛,暗示丈夫方面的某种委曲及这对年轻夫妇之间的危机。
接下来两段继续描写内景,如照相摄镜简洁而清楚地表明,这是一个颇像样的小家庭;一对“大柚木床”,说明这是男女分床而睡的新式家庭。当写到“睡在床上的两个人”及房门“现在严密地关着”时,隐含“床戏”的悬念。顺便提到的“这里有一扇小门,似乎是通到浴室的”。这“似乎”所含的不确定性,却在结构上首尾呼应,显出在“谋篇”上的精致。故事以娴娴从浴室悄然出走为结束,方显示出空间的政治含意:如果这“小书桌”意味着君实在此家中的愈益缩小的精神领地,那么结果显得更为可怜——他的启蒙方案的全盘失败,现今更陷入革命的历史洪流中。
下面一段间接描写女主人,是一个新型少妇,穿着入时讲究,且见她“镂花灰色细羊皮女鞋的发光的尖头”,然而另一只鞋被乱丢在梳妆台边,暗示她并非那种善于料理或安于家室的类型。她的良家少妇身份及其忙碌于户外活动,更从那些随便放着的“少妇手袋里找出来的小对象”得到印证。而最后提到《妇女与政治》的杂志,则使人联想到她的兴趣所在,与户外活动的内容有关。
第二节直接描写床上,君实先给街上急驶怪叫的汽车惊醒。这也是顺便补一笔城市背景,他们住临街房子,暗示经济状况属于一般知识型的市民阶层。女的还没有醒来,但她的身体,“浓郁的发香”,“两颊绯红,像要喷出血来”。这样略嫌夸张的修辞似乎想表明,这是一个充满活力、撩人心怀的女人。
叙述马上进入“危机”主题:他想起昨夜自己早睡,不知夫人几时回家。这一事实所隐含的危机的深度,根本上涉及君实对女人的态度:他关心娴娴的思想,更甚于她的具体存在;或者说他更关心的是他自己的纯洁“理想”,娴娴是他的思想的实验场。接下来数页叙述他的回想,夹杂着痛苦、自省与执拗。两年来的结婚生活,心心相印的融洽与欢乐,仅是短暂的一瞬,与娴娴之间开始从生活趣味到最近思想上的歧异与冲突。尤其是这半年来,自从娴娴认识了“太像滑头的女政客”的李小姐之后,就更牵入政治上的“实际活动”。他并不是不赞成女子关心政治与自我解放,但使他感到难堪的是,她越来越坚持自己的见解,与他之间的思想分歧越来越深。
第三人称的叙述角度与声音基本上从君实的内心展开,在我们和主人公之间建立某种亲昵性,但叙述不断作微妙的转换,变成客观的叙述或评述。如“近来他们俩常有意见上的不合;娴娴对于丈夫的议论常常提出反驳,而君实也更多批评夫人的行动,有许多批评,在娴娴看来,简直是故意立异。娴娴的女友李小姐,以为这是娴娴近来思想进步,而君实反倒退步之故。这个论断,娴娴颇以为然;君实却绝对不承认……”这样的叙述看似客观,给人听到不同的观点,而读者却容易倾向于娴娴。读者不一定马上同意李小姐的“进步”和“退步”之论,但这一笔提示极其重要,点出了君实和娴娴之间的冲突的核心,是有关“革命”的是非问题。而“这个论断,娴娴颇以为然”,则进一步提醒读者的价值选择。
这一段直接引语里,最使娴娴反感的,是他讥讽李小姐那种“不满于现状,要革命”,“只是新式少奶奶的时髦玩意儿”。所谓在电影院跳舞场里的“革命”,或许反映了部分真实或具某种代表性的看法。的确君实的意见仍给读者留下思索和评判的余地,而接下来的叙述:“君实说话时的那种神气——看定了别人是永远没有出息的神气,比他的保守思想和指桑骂槐,更使娴娴难受”,这就使君实显得很不可爱,读者也自然会替娴娴感到难受。这“革命”虽然指明与实际的“政治活动”有关,含义仍有些含糊,到底是有关妇女运动还是别的革命活动,其性质并未言明。但重要的是这里的“革命”作为象征意义的表现,它指向一个吸力更为强烈的外在空间。有的学者认为娴娴“是现代青年妇女对于自由的追求,虽然这是一种个人的解放,不带有集体的性质”。这种看法我觉得是片面强调了“个人”的一面。如果从脚跨“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含糊交界处来看这篇作品,方能得到更全面的理解。
所有的疑惑、痛苦或愤激的反应,都传达了他对娴娴的感情,是真实的,这样一个好丈夫形象的自我呈现,照理会引起读者的同情。但在同情的叙述里,常常有一种模棱两可的音调,使我们感觉到君实身上的一些东西,实在很难使人接受。如“他爱他的夫人,现在还是很爱;然而他最爱的是以他的思想为思想以他的行动为行动的夫人。不幸这样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娴娴非复两年前的娴娴了”。读者也会替他惋惜,但他对娴娴有某种“大男子主义”,也就是说这样的内心叙说却含有叙述者的评判意识,对他的体贴和爱护起到内部消解的作用。
这个短篇的最大创获之一正是这种亲昵语调中所含的喜剧性反讽,最终使读者与君实之间产生距离。更为明显的是,写到昨夜他早睡,做了许多梦;以前他不做梦,因此多梦带来了不安:“他努力要回忆起那些梦来,以便对夫人讲。即使是这样的小事情,他也不肯轻轻放过;他不肯让夫人在心底里疑惑他的话是撒谎;他是要人时时刻刻信仰他看着他听着他,摊出全灵魂来受他的拥抱”。他对夫人固然坦率、忠实,然而要她“摊出全灵魂”而作为回报则显得专权而可憎了。“拥抱”这个比喻含有对于君实的“崇智主义”的戏谑成分。与此相应的,在这一节里写他继续回想时,重复出现了这个“拥抱”的母题,其意蕴更为丰富:
现在君实看见夫人睡中犹作此态,昨日的事便兜上心头;他觉得夫人是精神上一天一天的离开他,觉得自己再不能独占了夫人的全灵魂。这位长久拥抱在他思想内精神内的少妇,现在已经跳了出去,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见解了。这在自负很深的君实,是难受的。
本来君实那种与旧文化藕断丝连的“自负”就显得迂腐,现在用揶揄的语调说明他自己觉得对夫人失去控制,就越使人觉得可笑。原来他自许代表普遍真理,因此他的思想领地无所不在,广大如世界,如宇宙。现在他发觉娴娴从他的“精神内思想内”“跳了出去”,说明他认识到自己的思想和精神的空间是有限的。意识到这一点,无疑是痛苦的。如果将这一对关于“拥抱”的重复修辞和稍后出现的另一对有关室内空间的重复修辞相联系,我们可看到这篇小说的文本的质地之细,而且这些空间的比喻对于男女的角色轻重的错置,起到关键作用。
这一节末尾,失败心理得到进一步证实:“君实本能的开眼向房中一瞥,看见他自己的世界缩小到仅存南窗下的书桌;除了这一片‘干净土’,全房到处是杂乱的痕迹,是娴娴的世界了。”与娴娴争执的细节起初有那种“爱的戏谑的神秘性”,到后来更多的是“主张失败的隐痛”,“况且娴娴对于自己的主张渐渐更坚持,差不多每次非她胜利不可……这便是现在君实在卧室中的势力范围只剩了一个书桌的原因之一。”这里重复叙述的“南窗下的书桌”呼应了小说的起点,在整体结构上也和结尾相呼应:当娴娴走出这个“卧室”,她获得的是整个新世界,同时却隐含着君实的旧思想境界的窘促和孤立,及他的“创造”工程的彻底失败。稍后,作者仍使用君实的感觉的语言,又重复了空间的比喻,在男女主角之间加深新旧、进步和退步、胜利和失败的界线,更强调了娴娴的战斗性:
娴娴的心里已经有一道坚固的堡垒,顽抗他的攻击;并且娴娴心里的新势力又是一天一天扩张,驱逼旧有者出来。在最近一月中,君实几次感到了自己的失败。他承认自己在娴娴心中的统治快要推翻……
尽管第一章的前三节几乎全在写君实,但大段心理的展开已经在读者那里收到效果:女主人公还没有出场,我们已经觉得她无所不在,她不仅是这卧室里的真正主人,也是这篇小说的真正英雄,随着她的“新势力”的“扩张”,给情节的开展带来更多的潜力。读者希望看到、听到这位“神秘的女子”。最后一段回到床上,写两人的动作和对话,戏谑的主调贯穿其中,尤其是娴娴的一颦一笑,一投手一举足,无不横生妩媚天真,性感洋溢:
俄而,竟有暖烘烘的一个身体压上来,另一个心的跳声也清晰地听得;君实再忍不住了,睁开眼来,看见娴娴用两臂支起了上半身,面对面的瞧着他的脸,像一匹猫侦伺一只诈死的老鼠。君实不禁笑了出来。“我知道你是假睡咧。”
这里实写“床戏”,仅止于挑逗而已。所谓“革命加恋爱”的小说,无非在“情场和战场”的两极间摆动,遂生成情节的张力。这一幕夫妇之间的调笑,似乎不无叙述者的自讽,化解了前面种种“斗争”、“堡垒”等带火药味的比喻,但回过来看这个短篇事实上表现的是情场变成战场,就不那么好笑了。
两人的对话内容还是集中在他们之间近来的思想差异上,主问者是君实,但在娴娴方面,显得不那么在乎,结果是君实在她面前承认自己的失败:“你变成了你自己,不是我所按照理想创造成的你了。……娴娴,你是在书本子以外——在我所引导的思想以外,又受了别的影响,可是你破坏了你自己! 也把我的理想破坏了!”于是引出第二章的主题:君实进一步回顾自己如何精心“创造”娴娴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