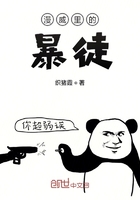不仅是徐枕亚,在上文讲到的几篇周瘦鹃的小说里,歌颂对象是辛亥革命。即使在20年代末鸳蝴派文学那里,如《紫兰女侠》写一批江湖女侠在民国前帮助孙中山广州起义的故事。20年代,虽然民国早已建立,而“革命尚未完成”,所以在民国传奇的重述中也投射出新的叙事欲望。
从1929年7月至1930年6月,在《紫罗兰》月刊上连载了张春帆(1872—1935)的章回长篇《紫兰女侠》,开宗明义曰:
革命这件事,好像男女间的爱情一般,应当有神圣纯洁的性质,不能掺杂一丝一毫杂质在里头的。无所为而为,是吊民伐罪的英雄。有所为而为,就不但变作投机牟利的行为,而且还造出许多的恶例,引起无限的纠纷。譬如男女相爱,彼此同心,既不为财,也不为色,更没有什么作用在里头。这种结合是在爱情基础上建筑出来的,自然可以永久保存。纵然地老天荒,沧桑变换,形骸非我,然而这爱情是万劫不死的。如若男女缔结的时候,并不纯用爱情结合,彼此存着个利用希望的念头,这就是爱情基础没有坚固。一个不得法,内部的建筑就要发生破裂坍塌的危险,如何还禁得起外界的袭击? 自然要溃败决裂,不可收拾了。
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像他的《半月》一样,在消闲文学杂志中是较讲求品位的,自1925年至1930年共出刊96期。每期封面也是时髦女郎,出自月份牌名画师杭稚英手笔,到第三年更为考究,用双页封面,即第一页中间镂空作为镜框,突出下面画页上的女郎。张春帆是鸳蝴派小说名家之一,民国初年即以描写十里洋场妓院生活的长篇《九尾龟》而蜚声文坛。《紫兰女侠》开宗明义以革命与恋爱作标榜,可见这一题材已成时尚,但所谓“革命”的内涵与共产党左翼的南辕北辙,反映了上海各界一般对于国民党的北伐“大革命”乐观其成的态度。但正像作者所声称的,这部小说掇拾一些有关革命的珍闻轶事,写出来“给列位看官作一个酒后茶余的消遣罢了”。游戏性质也见诸书名,“紫兰女侠”是配合《紫罗兰》杂志,一面为杂志打招牌,招徕读者,一面在写作上花样翻新。这个风气从《礼拜六》早就开始,至20年代无论是《红杂志》、《红玫瑰》等,皆乐此不疲。然而有趣的是,这种书写策略源自从前文人之间的唱和形式,却与现代广告术相结合,无不以女性身体作为象征指符,从而反映了以时尚消闲为主的都市印刷传媒中“新女性”与文学商品之间的复杂关系。
令人好奇的是,作者既不讳言这是一部游戏之作,却又标榜革命与爱情的“纯洁”性。这种高调出自一位写《九尾龟》的“嫖经”之类的小说家,听上去不那么合拍,而且跟我们的成见——这类消闲杂志一向被新文学家及革命左翼指斥为“毒害”青年——也有抵触。事实上形成有趣对照的是,此时在新文学的张资平及稍后的叶灵凤、穆时英等“海派”那里,表现女性身体更具生物性、物质化的倾向,即朝形而下的方向发展。
《紫兰女侠》从清末孙中山的“革命之役”写起,一直到北伐时期,描写一群武艺高强的女侠如何出生入死协助革命党攻打清军,最后革命成功,她们也修成正果,功成身退。如作者声称,此即为一部“革命外史”,叙及孙中山历次起义至“二次革命”,以及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颇如一部民国早期简史。叙述爱情的这根线索以何紫兰和柳安石为主,经过一系列周折而终成眷属,还穿插了其他几对恋人的罗曼插曲。主要的悬念是一直夹在何、柳中间的少年仇紫沧,长得跟何紫兰一模一样,最后真相大白,原来是女扮男装,既充作何的男友,又是她的替身。显然作者也在玩三角恋爱的游戏,却挖空心思,刻意求胜。
这部小说固然拥护“三民主义”的“革命”,却另有玄机。主角柳安石是粤中某中学教员,自称“不是革命党人”,而是他们的“同志”。原来他根本上并未认同孙中山。他说:“我的革命主张,本来和急进派不同,是主张联合全国会党蓄养出一种潜势力来,然后用政治革命的手腕解决时局的。这般的办法,既不妨碍老百姓的生命财产,也不阻碍国际的邦交。这武力解决的革命,是我不赞成的。”只是明白革命党“也有一种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苦衷”,方才协助他们。小说里处处突出柳安石见义勇为与人道关怀,有一处写到革命党人要杀一个满人,柳加以制止说:“革命是统一大同主义,不能用狭义的解释,强分内外。”这里显然不同意孙中山的种族主义了。另一处柳说:“要知道革命事业不能专讲破坏的,万不得已只好破坏个人而维持团体。”“少一次破坏,就为国家地方多留一份元气,这是我和革命党宗旨不同的地方。”柳的这些论调,包括他的加入这样武力的“政治革命”是出自形势,他所倾心的是“社会革命”,并非作者杜撰,令人想起清末康有为、梁启超那一派立宪主义的主张。不过在国民党北伐革命节节胜利的语境里,听上去不那么协调。尽管叙述者称赞孙中山的“革命完全是无所为而为的”,亦即为一种“纯洁”的革命,同时却极力描写柳安石以仁义为怀,斤斤于“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破坏”和“和平”之间的区分,当然也是有关小说宗旨即“纯洁”的命意所在,至少对于孙中山的一而再、再而三的“革命”表现出怠倦,似乎清浊之间——说得严重一点——也含有不愿同流合污之意。
所谓“紫兰女侠”是由一班男女自行组织的一个革命同志会,住在离广州几十里外的紫兰村里,一个诗意的世外桃源。会长何紫兰统领一群女侠,每个人的名字中间都有一个“紫”字。她们也是革命的同路人,当何紫兰向柳安石介绍说:“敝会虽然赞助革命,恰不是革命党,和革命党的破坏宗旨略略的有些异同”,于是两人志同道合,走在一起。她们同革命党一起作战,主要在于暗中配合,排难解纷,常在革命党人陷于危机时出现,当然对于小说来说,也是特意制造的关键时刻,表现她们的飒爽英姿,江湖本色,如写到一对革命党夫妇被清兵拖到船上、将被杀害之际,船上突然闪现一道紫光,从空中落下一个紫衣少女,喝道:“不许杀!”只见她:
穿着一身称身可体的紫绡衣裤,恰淡淡的,不十分深,头上裹着一条紫帕,连鞋袜都是一色紫的,空着一双手,只腰间紫绡带上缀着两支银色小手枪,生得削肩细腰,明眸皓齿。
在形象塑造上“两支银色小手枪”是十分现代而别致的,但并不妨碍她们实行“和平革命”的宗旨,何紫兰更使用一种新式武器“电枪”,一种不伤人的无声手枪。不过,在武器方面是现代化,她们在文化上却是国粹派,不光是崇尚功夫武术,连紫兰堡里所有屋里的摆设都是本土产品,没有一件洋货。国粹主义也见诸她们高明的土法医治。一位受重伤的革命党人被送到紫兰堡里,何紫兰以“出汗法”给她治疗,即令她在沙地上打滚,她还是不出汗,于是由四人将她抛到半空中,她受了惊吓出了汗,体内透了气,伤也就治愈了。何还讲了一通身体被电气支配,剑术有红光、白光的玄理。这些描写显然有矛盾处,会令人觉得好玩,作者着意标榜这种文化的民族主义来体现“纯洁”的主旨,其实单是这紫罗兰本身便是舶来品。她们把它用作同志会“证章”似乎也跟拿破仑的“百日复辟”的传奇有关,即拿氏从厄尔巴岛重返巴黎时,凡是拥护者皆佩戴紫罗兰徽章,作为辨认的标志。
在体现爱情的“纯洁”方面,小说宣扬“贞操”论。如在紫兰堡中养伤的李若英“虽是个开通女子,她恰看得贞操极其重要。她说一个女子的贞操是全部分爱情的代表物”,亦诤诤告诫:“世上的女界同胞们,若先受了青年的诱惑,在全部分爱情未有寄托之前,就丧失了贞操……至少在自己的心灵上终是一件不痛快的事。”所谓“全部分爱情”,意谓灵肉一体,丧失贞操,等于丧失爱情,不过也仅关乎“心灵上”的“痛快”与否,听上去还不那么严重。但这和五四以来有关新女性的性欲解放的观点背道而驰,那些时兴的“革命加恋爱”小说普遍涉及灵肉分离的问题,如杯水主义的夏克英、被迫淌白的赵赤珠、欲海无边的王曼英等,即使灵与肉的冲突带来快乐或痛苦,共通的一点是,女性获得了支配自己肉身的自由。至于张资平笔下的苔莉,女性的意识更为生物性冲动所占据,而在茅盾的《虹》里发展到另一个极端,即梅女士干脆要克服“母性”而成为“主义”的化身。
“纯洁”的爱情更意味着肉身的消失。在罗紫云营救柏民强时,两人之间擦出情感的火花,遂引起柏民强的女友汪丽云的猜疑。于是罗紫云堂堂正正地发了一番高论:“我和柏君的联结,是从感情里头磨荡发越出来的爱,不是男女私情中含着欲素的爱。感情里磨荡出来的爱,这个爱是纯的,不是杂的。完全是精神结合,不是形体结合,就连名义上的结合也用不着。”否则像“精神与形体相互的结合”,就会变成“杂”的。像这样歌颂男女间“无形的”、贬抑肉体的“纯洁”的爱,并非张春帆的发明,在鸳蝴派文学中具有普遍性。有趣的是这些“紫兰女侠”也是“新女性”类型,与一般鸳蝴派小说里贤妻良母的类型不同,也受到“革命”的感召,在新天地里大显身手,仿佛是一部儿女英雄传的现代演绎,更带有集体理想的色彩。最后一幕是从众人眼中看去,柳安石与何紫兰两人在花园里:
何紫兰手中拈着一枝紫罗兰,插在柳安石襟上,口中说道:“我别无所爱,平生第一只知爱国,第二只知爱爱国的英雄,你就是爱国英雄中的第一人。”柳安石倏然立起身来,低声说道:“我的爱你,也是由于爱国而兼爱爱国的女英雄。你把我算作第一个爱国的英雄,我惭愧得很,你才算得爱国英雄中的首领呢。”
这里皆大欢喜,不脱团圆剧窠臼,肉麻的卿卿我我是才子佳人式的,却谱出儿女英雄的“爱国”合奏。小说的结局为这个小团体设计了某种理想的蓝图,呼应了在卷首便出现的紫兰堡的乌托邦母题,此时同志会接受了某富翁的巨额捐款,计划在江苏北部的海边建设一个“模范港”,由三个葱茏小岛映带四周的一个冬暖夏凉的天然海港,作为同志会的总部,把广州紫兰堡改作分部,意味着他们小天地的美好将来。
早在1907—1908年一边发表《九尾龟》的同时,张春帆一边在《月月小说》杂志上连载标为“立宪小说”的《未来世界》,或可视作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的姊妹篇。书中鼓吹“立宪救国”、“改良政体,组织国民”,还提倡“满汉团结”、“女子教育”等,确是梁氏的忠实信徒。在20年之后的《紫兰女侠》里,这些主题一一重现,仍不失其现实意义。民国以来“革命”不已,国无宁日,共和政体破残不堪,公共空间愈益萎缩,因此即使在20年后“立宪救国”仍是国人的未圆之梦。尤其在“大革命”之后蒋介石推行“党治”之际,《紫兰女侠》标明与孙中山反清“革命”相区别,取一种与国民党主流意识形态疏离的“另类”姿态。
这一点涉及“鸳蝴派”文学的政治性及其与都市现代性相联系的意识形态,迄今未得到学界关注。其实大多数通俗作家加入“南社”,皆反对帝制、拥护共和,实即以欧美资产阶级政体为楷模,主张有限政府,以发展民族资本、允诺言论自由等为前提。如20年代前半期《申报·自由谈》每天刊登周瘦鹃“三言两语”专栏,追踪时事新闻,揭露北洋政府的丑闻恶行,对于总统、军阀及国会议员指名道姓,尽嬉笑怒骂之能事,其实在继续“自由谈”的批评传统,不无风险地挑战“言论自由”的尺度。 不光是对北洋政府,即使对于当时正进行“护法”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也戏称之为“孙大炮”,尽管是带善意的。 实际上早在1910年代《自由谈》的“游戏文章”便对孙氏的“二次革命”有微词,也出自反对“破坏”,维护宪政的立场。至于20年代末国民党掌权时,《紫兰女侠》表示与孙氏“革命”的距离,当然是更具自由色彩的。总之通俗作家的政治性不在于发表宏文高论,而在于他们的职业与文化实践之中,即大多以报刊为衣食之具,奉读者为上帝,在代表都市日常欲望时,对于现状既有维护的一面,也有疏离的一面。
既为《紫罗兰》作广告宣传,《紫兰女侠》的写作含有商业炒作,是一个文学商品,但它不仅表达一定的政治主张,在文类上别有匠心,将政治、言情与武侠融于一炉,标志着该派在表现策略和审美趣味方面的新拓展,蕴含着有关性别的吊诡的认知及其民族国家建构的典律和代码。有趣的是,这出自一本以消闲为主的流行杂志,对于认识当时的上海文化氛围及资本主义印刷文化的性质,却是一个极佳的例证。
自20年代初“新”、“旧”文学争论之后,“新文学”以白话取得“正统”地位 ,“鸳蝴派”在理论上处于下风,而在创作上却更取开放姿态,如周瘦鹃在论争中提倡自由竞争:“不如新崇其新,旧尚其旧,各阿所好,一听读者之取舍。” 因此他们力求花样翻新,文言、白话并用,形式上多元杂交,为的是能吸引更多的读者。尤其是属世界书局旗下的《红》与《红玫瑰》杂志更重视娱乐性,有意发展侦探与武侠类型,大获成功。1923年向恺然(1890—1957)的《江湖奇侠传》在《红杂志》上连载,描写江湖侠士飞檐走壁,刀光剑影,更能呼风唤雨,降龙伏虎,翻江倒海,飞剑杀人等,种种新招,无奇不有, 使读者大呼过瘾,趋之若鹜,其实融合了公案和神怪的小说传统,遂别开生面。武侠小说的成功,给鸳蝴派文学带来了生机,在这一想象空间里,表现手法上干脆远离写实,专力营造幻象,充分满足读者的感官享受。
1928年《江湖奇侠传》的某些情节被改编成电影《火烧红莲寺》,引起轰动,一连拍了18集。如1933年茅盾看了这部影片后所描绘的:“从头至尾,你是在狂热的包围中,而每逢影片中剑侠放飞剑互相斗争的时候,看客们的狂呼就同作战一般。” 他认为“小市民”观众如此着迷,是因为头脑中“封建意识”作怪,其实影片中如“放飞剑”等运用了现代表现技术,给都市观众带来了新刺激。 此后武侠电影煽起阵阵热浪,不仅《火烧红莲寺》连拍续集,单是1928—1929年间有《荒唐剑客》、《大侠复仇记》、《妖光侠影》、《关东大侠》、《航空大侠》、《荒村怪侠》、《尘海奇侠》等,可见当时各家电影公司竞相争拍武侠片的盛况。 使茅盾愈觉不安的是,“他们对红姑的飞降而喝彩,并不是因为那红姑是女明星胡蝶所扮演,而是因为那红姑是一个女剑客,是《火烧红莲寺》的中心人物……他们是批评昆仑派如何、崆峒派如何的! 在他们,影戏不复是‘戏’,而是真实!”这里涉及艺术再现与认识论问题,其实如何使读者像喝了“迷魂汤”一样认幻为真,达到宣传效果,也何尝不是茅盾的“写实主义”的追求目标?其时他更自觉地执行“无产阶级”党性立场,鼓吹文学“作品一定要成为工农大众的教科书”, “要从形式方面取法于旧小说”。 可见他在痛斥这类武侠作品的同时,却从“通俗”文学那里吸取了不少养分。
小说类型上将武侠与爱情交杂是一种新的探索,给鸳蝴派“言情”小说开辟新途,也与“新女性”公共空间文学表现的时尚似不无关系。如龚鹏程指出,它改写了传统的“侠”的文化代码:“它偏向于个体,描述个体性的英雄或美人,刻画他成长的历程,关心他的内在感情世界,并努力铺垫英雄与美人恋爱的经过。在侠的生命中,爱情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了。”几乎与《紫兰女侠》同时,顾明道(1897—1944)的《荒江女侠》在《新闻报》副刊上连载,一时间“四海传诵,有口皆碑”。这在武侠小说中属软性的,发展了《儿女英雄传》的安公子与十三妹的一路,所谓“以武侠为经,以儿女情事为纬,铁戈金马之中,时有脂香粉腻之致,能使读者时时转换眼光,而不假非僻之途,不赘芜秽之辞,是以受读者驰函交誉”。的确,武侠小说善恶分明,邪不胜正,既能宣扬传统伦理价值,又有“江湖”的另类情趣,而女侠形象可说是一大发明。她们一般性格刚烈,不易受情色诱惑,因此作者也乐得“不赘芜秽之辞”,同时能体现爱情自主,最终以家庭为归宿。她们在公共空间甚至革命的历史洪流里大显身手,不让须眉,当然是“新女性”的投影,分享了新文化的典律,同时并未脱离贤妻良母的价值代码,仍恪守了该派的文化底线。
那些通俗作品能畅销一时,常有些形式上的“新招”引人入胜,如叶洪生指出,《荒江女侠》使用了“限知叙事”方法,“打破传统章回小说的陈腐老套,开武坛未有之先河”。《紫兰女侠》的出新之处在于由“小手枪”装备的现代化女侠形象,意味着武侠小说从刀剑传统战法朝“枪战”类型的转化。这部小说不光结合言情与武侠,还承接了清末“政治小说”的传统,富于“理想”色彩。一种集体意识贯穿在这部“革命外史”中,即柳安石和女侠们加入“政治革命”好像是不得已的,而更钟意于“社会革命”。民国建立后他们满以为可从事社会建设,然而权奸当道,国难不已,等到袁世凯阴谋称帝、宋教仁被刺、孙中山揭橥“二次革命”,他们又继续“政治革命”。于是何紫兰潜入京师,将袁氏的军帽掀去,又飞回他的头上,帽中夹一字条,警告他如在三个月里不取消帝号,其头颅就会像这个帽子一样。这一突出女主角的插曲当然属子虚乌有,只是简单套用了类似“红线盗盒”的情节。
这部小说蕴含着对女性“内”、“外”空间表现的不同代码,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鸳蝴派在“性别政治”方面的困境与局限。所谓“内”的代码反映在“贤妻良母”的“私人空间”的表现方面,主要是在该派的小说里。“外”的方面是把女性作为商品,如“紫兰女侠”为《紫罗兰》杂志做广告,与该杂志的封面女郎分享了集体的商品性格。这一以女性作为现代性标志的印刷文化得追溯到清末《点石斋画报》、《游戏报》等,其间妓女扮演了先锋角色。这方面刚见世的叶凯蒂(Catherine Yeh)《上海之爱》(Shanghai Love)一书作了详尽的探讨。民国以来这一传统在通俗文学期刊中被发扬光大。1911年包天笑主编《妇女时报》,刊登时髦女子的照片。既然难以得之于一般不肯抛头露面的良家女子,即求之于妓女。在南京路上开设一照相馆,免费为她们拍照,由此杂志上照片源源不断,她们的衣着发式成为时尚,反为良家女子所仿效。 这是现代期刊促使女性“可见性”的佳例。所谓“时尚”乃借图文印刷技术构制成都市美梦的幻影,力图表现更好更新的生活方式及品味趣尚吸引读者,其物质层面则与商品市场、尤其跟舶来奢侈品紧密联系。在这方面周瘦鹃更不惜工本,在他主编的《半月》、《紫兰花片》、《紫罗兰》等杂志皆以摩登女郎为封面,彩印精良。20年代末他主编过《良友》和《上海画报》,所刊登的“新女性”照片不以娱乐业的妓女、演员、电影明星为限,也包括各行各业的职业妇女,或作为大家闺秀典范的“交际花”,如唐瑛、陆小曼等,都代表都市风尚,即在商品流通领域里一律平等,却也反映了女性愈趋自由,其公共空间愈迅速扩展。
商业上既如此利用女性的公共性,对于妇女“解放”潮流也亦趋亦进。将女性时尚化也是为都市打造梦想,“新女性”以健美、才能和自主为必要条件。鸳蝴派在这方面也有保守、开放之分,周瘦鹃属于后者。他反对包办婚姻,鼓吹男女社交,大谈欧化的“接吻”与世界“名人风流史”。在《七度蜜月》这篇“杂谈”中对于一位结过七次婚的美国老妇赞美有加。 在《妓女身上的小电灯》一文里,对她们招摇过市、炫人心目的外观既讽刺又欣赏,典型地说明其贯彻文学的娱乐消费宗旨,同时与情色业界纠缠不清。
对于女性身体的“解放”也有积极的响应,如周瘦鹃主编的《家庭周刊》发表了反对女子穿“小马甲”而主张她们胸部松绑的文章。周的《紫罗兰》杂志还刊出“解放束胸运动号”的专辑。其实这些也蕴含着国族想象的成分,就像作者们所强调的,健康的胸部不仅有关健美,也利于哺育子女,优种强国。他们热衷于女性形象的商业消费,将女性客体化,主要在于满足男性窥视,但另一方面也支持了“妇女运动”。就像周瘦鹃的《半月》杂志专设“妇女俱乐部”专栏,刊登女作家吕碧城 (1883—1943) 等人的作品。至于40年代张爱玲在他的《紫罗兰》杂志上刊登小说而一举成名,已是众所周知的文坛佳话了。
与此推进女性公共性的同时,不无吊诡的是另一方面强调爱情的精神性。《紫兰女侠》所表达的“纯洁”爱情,在鸳蝴派文学中并非个别。如周瘦鹃说言情小说,“惟用意宜高洁,力避猥俗。作者必置其心于青天碧海之间,冥想乎人世不可得之情,而叙以一二实事,以冰清玉洁之笔,曲为摹写。无杂念,无亵意,则其所言之情,自尔高洁”。的确他的许多小说都讲心灵的纯真,描写男女恋情不及乎乱。在《真》这一短篇里,汤小鹤对邹如兰的一片痴情,即使在如兰嫁于他人、出了车祸而毁容、遭到乃夫抛弃之后,小鹤不改初衷,将她接过来,让她住在新造的别墅里,但是他自己却从来不想见到她,仅满足在他的幻想里,“每来探望时,只立在园子里,对那小楼帘影凝想了一回,就很满意的去了”。这种女性身体缺席的爱的表现,被发挥到近乎畸情的地步。在周氏那里,对男女之情强调“真”和“高洁”,有其复杂的思想来源,从更深的性别和文化的层面上来看,则混杂着男性对于女性身体的恐惧,伴随着由西方现代物质文化带来的反应。尤其是他在小说里出现那些类型化的女性,即追求物质享受而给家庭社会带来祸害的时髦女子,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
一方面浮沉欲海,热衷商业策略,另一方面标榜“高洁”,视性欲描写为禁忌,对于女性公、私不同空间的文学表现构成鸳蝴派文学的内在矛盾,虽然该派竭力使两者在“高尚、纯洁”的原则下得到统一。即使对于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的“裸体”问题也是如此。他们站在刘海粟一边,在他们的杂志里也不时出现裸体画,但坚持认为这是高尚的“美术”观赏而不容非分之想。这是该派的不成文共识,即遵守“力避猥俗”这一底线,建立在对于清末以来造就“强国”、“强种”的“国民之母”的集体认同之上,也跟他们的一夫一妻“小家庭”主张连在一起。只是到20年代中期之后,女性“解放”与社会“革命”思潮联袂而至,他们的言情小说连同“高尚、纯洁”的原则显然不合时宜,虽然在《紫兰女侠》的类型夹杂中仍有所表现,也属于强弩之末了。§§第三章《蚀》三部曲:时间镜框中的女性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