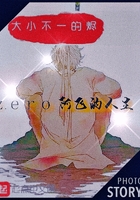铃兰的大字写到一百五十张的时候,地里的庄稼要收割了,二老爷整日忙着查看下面的庄子。白露回说西瓜的事情已经办好了,只是他爹觉得每日里用的冰太费了,总是问这是要做什么。铃兰嘱咐她告知家里不要声张,又给了五两银子让她爹不要吝惜冰的使用,务必保证地窖里的温度不能高。
铃兰大字写到二百张的时候,俞家迎来了大喜事。二房的子语和三房的子评在今年的乡试时都考中了,一个是一百六十九名,一个是一百零三名。他二人都是考了多年才得以中举,因此二太太和三太太都是喜极而泣,老太太也极为欢喜,赏了他二人一人一方端砚,鼓励他们好好努力,为明年的会试做准备。虽然对于他们这样世代读书的大户人家来说,中举也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重要的是明年会试的名次,要知道只有会试考中才能授官。但是一家里二人同时中举,也算是喜事一桩,俞家特意选了个吉日大宴宾客,往来乡绅世交都来祝贺,据说那天叶老爷子也带着叶嘉恒来了,此子相貌风雅,谈吐出众,惹得子谚带着一众堂表姊妹(不包括子谣)躲在屏风后暗暗观看。除此之外当日宴会上还有一件奇事,昌州城七王爷的王府长史唐一笑带了礼物前来祝贺,虽然谁都不知道他为什么来的,但是这人自来熟,长袖善舞,挂着一副迷死人的笑容在宾客中左右逢源,男女通吃,甚至连屏风后面的小姐们都在低声争论他和叶嘉恒两人谁的皮相更佳。唐一笑带来了宫内的御制文房四宝做贺仪,转达了七王爷对俞家人才辈出的称赞,顺便还说七王爷平时也喜爱诗书,请子诺兄弟三人若是有空可以常去王府清谈,这样的邀请顿时给了受邀人等一片遐想。
子诺是宴席一散就急匆匆的去了子谣所住的舒雨阁,把唐一笑的真实身份说了一遍,彼时子谣正在屋里绣一方倦鸟归巢的手帕,听他说完,绣针一偏扎在指腹上,洁白的丝绫上顿时多了两点血迹,葛覃还在一边心急的说呢:“你说那个登徒子是七王爷府上的长史,这可怎么办啊,他不会公然来抢亲吧?呀,小姐,你的手……”
子谣不理这个急躁的丫头,自顾自把指腹含在口里轻吮,想了好久才说:“哥哥,事已至此我们想什么也没有用,关键是他怎么想,我们只能见机应对罢了,他既是王府的长史,想来也不屑于做出强抢民女这等荒唐事情。倒是那****看他身旁的公子气度不凡,难道是七王爷不成?”这话又引得葛覃鬼叫一声。
子诺想了一想:“也不无可能,今日唐长史曾说王爷相邀进府清谈,他日若是真能见到王爷,哥哥定为你留意。”
兄妹二人默然良久,子诺方说:“总之你放心,无论如何哥哥定保你平安顺遂。”
子谣轻轻一笑:“我知道!”看着妹妹坦然自若的神色,子诺也觉得心神安定了很多。
子诺走后,葛覃拿着帕子嘟囔:“小姐为这帕子费了多少心神,连这鸦雀的羽毛都绣的纤毫毕现,如今却被血迹污了,这可怎么是好。”
子谣本歪在榻上忧心皇觉寺的偶遇是福是祸,被这小妮子一打岔,忧虑之情倒也减了不少,勉强起身拿了帕子来看了看:“也还好,要不就在这里绣半轮夕阳吧。”
绮茂居里,二太太一边喜滋滋的给二老爷换上常服,一边迫不及待的把子语得到王爷相邀的事情说了,二老爷也十分欢喜:“好,好,我们的语儿终于有出息了。”
二太太满面红光:“是啊,老天开眼,语儿终于开窍了。不过这次啊,多亏了子诺。自从上次林嬷嬷点醒了我以后,我就督着子语拿着文章常到外书房请教,据语儿说,有时候得他哥哥点评一二,就有茅塞顿开之感。子诺说语儿写的文章过于呆板,说到底是读书不广的缘故,让他在四书五经之外多读些什么哦猪子稗稼方面的书,我还寻思呢,这读书怎么还牵扯到养猪和种庄稼的事了,没想到莫后还真是这些东西有用啊!”
二老爷气的扑哧一笑:“什么猪子稗稼,那是诸子百家,讲的是先秦儒学之外的一些学术思想,怎么到了你这就和庄稼扯上了关系。”二老爷看二太太还是一脸迷糊的样子,不由的叹了一口气:“罢了,和你说也说不清楚。其实书读的不好怪不得子语,你我都是略识的几个字的粗人,怎比得上大哥自幼延请大儒饱读诗书进士及第,就是大嫂也是老太太自昌州诗书世家亲自聘来的,听说自小闺学是极好的,带来的嫁妆里多有先朝孤本,子诺三四岁未开蒙的时候就会背三字经千字文,这些都是子语不能比的啊。”
二太太听得满面通红,她也一直为自己出自商贾人家为耻,所以才发狠逼着子语上学攻书,如今子语已经中了举人,获得了参加明年会试的资格,二老爷仍说赶不上子诺,怎不让她气恼,嘴上不由的就说了:“大哥大嫂我们当然是赶不上,可是就因为我们是乡下粗人,这地龙翻身我们不也没赶上么?子诺再聪明也不能参加明年的会试,若是明年语儿得中,那我们比大房也不差什么了。到时候我们也可以搬到京城居住,就怕子诺弄不来乡下的这些事情哩。”
“你以为中进士那么简单,多少人一辈子考的头发白了也考不上呢,子语这次能中举已是万幸,会试之事应顺其自然,小小孩儿你莫逼他太紧了。说起来,倒是子语的婚事,你可有了眉目没有。”
说起这个可对了二太太的脾胃,她顿时又眉飞色舞起来:“嘿,今天你是没看见杜夫人的脸色,一会儿白一会儿红一会儿绿的,真让人解气。亏她还有脸给我说前些日子是她那庶女病了,怕不好了才没有回我的话,如今病好了,那意思着还想着我们家子语呢,我直接就给她说如今昌州城里多少嫡女争着做这举人太太呢,怎么可能轮到她那庶女。其实哪,我是想着子语年纪也不算大,若是明年能一举得中,就是个京城的官家小姐也能娶得来,你看乐氏平时话里话外的带出来的,京城的小姐不知道比我们这小地方的好多少倍呢,有个得力的岳家对子语的仕途也有个帮助不是。”
“罢了,就大侄媳妇儿那样子,你也看得上?要我说娶妻娶贤,还是要听话懂事,勤俭持家的才好。”
“你就不能说些好话,这乐氏虽然不好,到底人家爹也是都御使呢,子诺守孝之后的起复不也要靠这岳家提携么。要我说如今凡事也不能全怪乐氏,子诺做的越来越过分了,整日里不是在兰晖阁就是在外书房,正经的夫人晾在那里十天半个月的说不上一句话,乐氏的怨气能不大么?”
“唉,隔了房的事情,你瞎操什么心,有空多教导一下子谚才是,你看子谣小时候多么胡闹,这次回来后却贞淑沉静,只守在屋里刺绣,反观子谚,带着一帮姊妹在屏风后面叽叽喳喳,成何体统。”
二太太瘪嘴不言,心里却想着那是子谣知道自己就是看了也没戏,难道让我们子谚也学着守成老姑娘么?
同时清泰院里,三太太也和三老爷在商量这事,不同的是子语是在子诺的点拨指导下取得的好成绩,二太太从此对大房的事情更加尽心,而三太太却觉得自己的子评终于学出结果了,明年的中举势在必得,她甚至在和三老爷商量早点分了家自己一房到京城买房子呢。三老爷听到这个就是一肚子气:“分家分家,你都说了大半年了,这事是我们能决定的么,你看二房都不言语了,你还抓着这个不放。”
“哎呦,你这个榆木脑子,二房怎么能和我们比,他二老爷是老太太陪嫁丫头的儿子,自小就不敢不听老太太的话,如今一家子又掌着管家大权,分不分家的对他们有什么影响,正好可以多捞点。可是我们呢,这么多年被晾在这里,干领着一点月银能做什么用。还有你生母胡姨娘,上次不过去那人屋里说了几句话,就被太夫人叫过去好一顿申斥,到现在都躲在屋里不敢出头。说起来都是姨娘,怎么一个恨不得捧到天上还不够,一个踩到泥里也没有人管。说起来就是泥人也有点土性,你可倒好,自个姨娘都被欺负成那样了,你做为亲生儿子一声都不吭,若是分家了,咱们把姨娘接出去也能想几天清福。”
三老爷心里也不舒服,四个兄弟比起来,只有自己文不成武不就整日里没有正经事情做,所以早就被老婆吃的死死的,二房还有个庶子子谊,他却是这么多年连个通房丫头也没有,可见三太太多么神勇,现在听了这个话,不由得问道:“依你说该什么办?”
“怎么办?分家,我们自己搬到京城去过,你放心,有我的陪嫁在,到哪都少不了你的吃喝,说起来,我的一个娘家堂妹当年嫁了个五品小官,听说现在也升调到京师了,我先去信打听一下,咱们到京城后也好有个照应。”
“可是如今二房也和大房走得很近,我们怎么办,若是真把老太太惹急了,什么都不给就把我们打发走了,你愿意?”
“说什么呢!”三太太抿了抿头发:“再怎么说你也姓俞,怎么可能一点东西都不给你,依我说,我要的也不过分,分家的时候和二房一样也就是了。这么多年她们把持着管家大权,可是别人也不是睁眼瞎子,到时候若是有一丝不公平,我可是要把他们的事情全都抖搂出来,大家谁都别想好过!”
三老爷是不掌权惯了的,也说不出什么。听得妻子话锋一转:“还有一个事情啊,今日的那个唐长史你看着怎么样,还有啊,你说他是为什么来的?”
“唐长史年纪轻轻能做上王府的长史,当然有不凡之处,至于他为什么来,不就是七王爷派他来祝贺我们俞家兄弟二人同时考中举人么?”
“我说你榆木疙瘩吧,你想啊俞家虽然在这村里有头有脸,但是到了昌州城里那就要往后排,这昌州城里高门大户的人家多了,就是子弟中了举的也不在少数,你可听说王爷又给谁家送过贺礼么?”
“这倒未曾听说。”
“所以啊,今日这唐长史来的不寻常!”
“那你说他是为什么来的?”
“这我一时也猜不出来。那人太圆滑,我几次试探都被他把话头带偏了,一点口风都没漏。不过啊,他最后说请子评他们有空去王府一叙,这可是上好的机会,去了不就知道他们所来为何了么?”
“可是我总觉得唐长史是对着子诺说的啊,这事还得以子诺为主。”
“子诺子诺,你看看这一会子时间你说了多少个子诺,以前总是说大老爷如何如何,现下大老爷没了,又是子诺如何如何,我看你是离了大房就不能活,是,子诺自幼就有神童之名,可是我们子评也不差什么啊,哼,过两天就让子评去王府拜见一番,若是得了七王爷的青眼,那升官发财岂不是指日可待?”
“我说你刚才不是还说让子评明年参加会试么,还要举家搬到京里去,怎么一眨眼就又要巴结七王爷了。”
“嗨,说你笨吧你还真就木上了,眼下白放着大好机会哪能不抓住?当然是那条路便利走那条了,总之啊,我们的子评以后的荣华富贵是跑不了的了。”
不提三房人各怀心思,且说这晚铃兰也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今日俞家车马盈门贵客如云,太太们忙着安排宴席,招呼客人;少爷们坐在一起谈经论典,当然顺便谈些风月真经青楼典故;小姐们凑在一起比衣裳比首饰,同时交换些深宅大院里的八卦情报,总之人人都有自己的圈子自己的事情,就是下人也个个得了红包,一个个忙忙碌碌喜气洋洋的往来跑腿伺候,唯独她的兰晖阁里还是一如既往的宁静。这让她彻底明白了自己的身份和在这个大家族中的位置。
这些日子以来她被好吃好喝的伺候着,老太太和子诺都待她很好,因此俞家上上下下也都敬着她,以至于她忘了自己本来就是个姨娘,是个没有名分、没有亲眷、没有地位、没有前途外加不受法律保护的角色,在这个社会姨娘严格来说不能算人,而是被视作玩物,她们没有财产的所有权,连自己的身体姓名都是属于主家的,男主人新鲜的时候可能很宠爱你,一旦厌倦,姨娘们的命运就如水上浮萍,毫不由自己做主了。她们可能一辈子老死在后院,也可能被送人或者卖掉,即使她们生了孩子,这个孩子也是管正房夫人叫娘,是未来的主子,而姨娘仍旧是个下人,即使混的好的姨娘能得到男主人一辈子的宠爱,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死了后仍旧不能进祖坟,宗祠中没有牌位,也不会享受任何后人的祭奠。这样认知让铃兰这个受了三十多年男女平等的教育有着根深蒂固的自由平等思维的现代人情何以堪啊。一整天,她都有股沧海桑田落魄潦倒的空虚感,这些日子以来的安稳富贵就如一场春梦,她可不愿余生都活在对这场梦的追忆中,她深刻意识到俞家不可能是她一生的归宿,来到这个世界后的第一次,她认真的考虑脱离俞家的可行性。
可是脱离俞家谈何容易,且不说她已经是俞家的妾,逃妾在这个年代被抓到可是要被打死的,就算主家不报官,不管她的死活,她出去以后没有身契户籍一样难以生存,再退一步说,就算这些都能解决,她可以恳求俞子诺放了自己出去,可是出去以后靠什么谋生呢?她把前世看过的穿越小说扒拉个遍也没找到什么对自己有用的谋生之法。若是她会厨艺还可以像顾早一样开个属于自己的酒楼,如果她学化学可以像琉璃夫人一样开矿造玻璃,如果她懂水利则可以像林娇一样救下全村人的性命,可是,她上辈子虽然吃过诸多美食但是却不会做饭,虽然中学化学考满分但实际上连黄金和黄铜都分不清,虽然去过三峡葛洲坝小浪底但那都是去旅游啊好不好,这看大坝和造大坝的差别海了去了。这么一想,无论上辈子还是这辈子,她都是一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无法养活自己的废物。这一夜,每个人都揣着自己的心事睡着了,只有铃兰怔怔的望着酸枝木床棱上的鹿衔灵芝的图案直到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