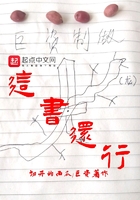最后,还是婉儿首先说,大人这些年来可好?奴婢是婉儿。
显依然低着头。显说我知道是你。你是代表圣上来的。你是要接我去见圣上吗?
是圣上要奴婢通知大人,今晚的觐见取消了。
取消了?为什么?直到此刻依然如惊弓之鸟的李显才抬起头,他惊异于母亲突然取消的会见,他不知道在这取消的背后,又会包藏着怎样的祸心。李显很怕。他是因为怕才抬起头的。他抬起头就看见了婉儿。而婉儿所带给他的惊异比女皇不再见他了还要令他震惊。他久久地盯着婉儿。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不能想象站在他面前的这个女人,就是他曾经那么熟悉那么喜欢的婉儿。
大人不认识我啦?
是显的惊异的目光才使婉儿突然意识到了她脸上的那片晦暗的铭刻着她的罪恶的印迹。婉儿下意识地用手去捂她的脸。很多年来,她甚至已经忘了她脸上的墨迹了。她在后宫里朝廷上出出进进,她与那些熟悉的陌生的人们打头碰脸,似乎已经没有人再在意她脸上的这疤痕了。人们似乎以为婉儿就该是这样的,唯有这样带着那个忤旨标记的女人才是婉儿。但是李显不一样。整整十四年李显从没有见到过她。在显的印象中,婉儿应该依然是十四年前的那个天真明媚的女孩子,婉儿的脸也不该是如此晦暗而丑陋的。只有李显的眼睛才能真正反映出那墨迹使婉儿的变化有多么大,她是怎样的面目全非,让人恐惧,甚至是令人厌恶的。婉JL怕显那真实的目光。她拼命地捂住她被黥的脸颊。她退着。她问着李显,奴婢就那么可怕?
不。不不。婉儿。千万别。真的。不是。李显请求着婉儿。
是婉儿脸颊上所经历的刑罚,使同样遭受了十四年磨难的李显顿时勇敢坚强了起来。他仿佛又骤然找到了那个他当年曾那么深深喜爱的小姑娘,他想保护她,他不想让她再受那么大的苦。
显几乎是跑着追上了那个向外走的婉儿。他拉住了婉儿,那时候他真想把那个无助的备受摧残的女人紧抱在怀中。他拿掉婉儿蒙在脸颊上的手,把那张印着墨迹而且已满是泪水的脸扭向了他。他就那样目不转睛地看着婉儿。他甚至伸出手去轻轻抚摸着婉儿的脸。他在心里说,这墨迹无足轻重,你依然是最美的。他甚至觉得在婉儿这张印满羞辱和苦难的脸上,他的生死都无足轻重了。
显就那样坚定地看着婉儿。婉儿的近在眼前使他觉得他仿佛又回到很多年前,那一天他和他的两个兄弟李贤和李旦,就那样不期地面对了那个美丽清纯的小姑娘。那就是婉儿。那时候婉儿刚刚来到母亲的身边。
婉儿这是为什么?
不,不,这无关紧要。
怎么会无关紧要呢?究竟是为什么?又是她?她到底要怎样?
不,大人你放开我。是奴婢忤逆了圣上,是奴婢罪有应得。
李显放开了婉儿。他扭转头。不知道为什么那热泪便夺眶而出。显不知道他堂堂七尺男儿为什么会落泪。但是有一点是异常重要的,那就是婉儿的苦难让他不再害怕了。显变得坚强了。在婉儿的身上,他仿佛突然就找回了那京城朝野宫内的感觉。漫漫十四年远离宫城,他原以为他对这朝中的一切全都陌生了疏远了,但是,当婉儿一‘出现。仅仅是因为婉儿一出现,婉儿脸上的那墨迹一刺进他的双眼,他就知道他回来了。洛阳不再陌生,这宫中的一切也变得如此熟悉。
婉儿看到了显的眼泪。
但是她不再哭。难道这墨刑就值得哭吗?那婉儿值得哭的事情就太多了。婉儿已变得成熟。成熟而圆融而冷漠而狡猾。婉儿太了解这宫中的一切了,所以她面对李显的眼泪,只能说,圣上是体恤大人旅途劳苦,会见改在明早上朝之前。望大人早早安歇,明早婉儿来接大人。
婉儿说过之后,便转身离去。她心中尽管有很多的苦涩,但是她依然很欣喜。因为她毕竟获知了在她未来走向显的路上已不再有障碍。而仅仅是她脸上的那个墨痕,便使她和显之间的那可能会存在的嫌隙转瞬之间化为乌有。不再有隔膜。仿佛一切都被跳跃了过去。时间被直接切割到了那个最欢乐也是最两小无猜的时代。他们是好朋友。他们彼此相亲相爱。
婉儿,请留步。
大人还有什么事?
我是说母亲。圣上她身体可好?
是的圣上很好。依然很美,精力充沛。
是圣上要我回来的吗?我一家真没有抄斩之忧吗?
大人,您误解圣上了。
就是说,我真的可以高枕无忧了?
圣上是秘密接你回来的。十几年间她一直牵念着你。
圣上是伟大的。
奴婢告辞了。
婉儿……
什么?
婉儿,日后还望你能帮助我。毕竟我离开得太久了。这宫中朝上,怕是满眼都是陌生的面孔了。如此物是人非,我怕没有婉儿的帮助,会寸步难行。
婉儿将尽力而为。
婉儿离开了李显;她又匆匆赶回了女皇的寝殿。婉儿想不到,女皇竟依然站在寝殿门口的石阶上,在很冷的夜风中,在等着婉儿。远远地看到婉儿,她竟然不顾一切地走下石阶去迎婉儿。她抓住婉儿的手。问她,怎样?显看上去怎样?他还那么高大伟岸英姿勃勃吗?他问到我了吗?他都说了些什么……
婉儿这才落下了眼泪。
婉儿是在离开女皇之后,才回了文史馆。她努力在为自己找着理由,她想国史中确实有一些部分在等着她去修改。她想她如果今晚不去做,明天就没有时间了。她已经非常喜欢修撰国史这一项事业,特别是在她整理女皇的那一段段大事记时,简直是一种痛快淋漓的写作。就仿佛她自己就是女皇。就仿佛是她自己在治理着国家。就仿佛是她自己正在一步一步地登上了女皇的王位。
婉儿确乎是回到了文史馆。
婉儿也确乎是决定挑灯夜战,在为圣上修书中体验圣上。
但是,那也许并不是婉儿真正的所思所想。那不过是一个借口。不过是一个婉儿用以欺骗自己的谎言。婉儿还不至于在记录女皇那惊心动魄的经历中去体验女皇的霸业。不,婉儿对权力没有兴趣,她弄权决不是因为她喜欢权,而是她要活着就必得学会弄权。是的,痴迷于整理女皇的历史不过是个幌子,她是要让住在庭院深处的那个可能依然在等她的男人看到她案台上的灯光,知道她来了果然,当婉儿刚刚研好墨,那殿堂的门就被推开了。那种婉儿那么熟悉的门的响声和来人的脚步声。婉儿当然知道那是准。她也许就正期待着他渴望着他切盼着他。婉儿永远也无法解释她为什么不能离开那个男人。
她曾经一千次想离开他,但又—千次回到了他的身边。她就那样等待着期盼着。任那个男人走近她,拉起了她的手,并且吹灭了那盏温暖而明亮的灯。然后一切就陷入了那个被黑暗充满的窒息中。在那里,欲望是主宰…切的真正的帝王。婉儿被那个男人牵着,穿过那个她熟悉的甬道,来到了那张床上。那是她和他的床。没有任何别的男人和女人睡过的床。就在他们的事业的边上,在他们智慧的谋略的同舟共济的愿望的边上。他们做爱。在无言中。直到午夜。当那个男人睡去。当完结。婉儿便起身离去。她必须在早朝之前赶到后宫李显暂居的庭院。她必得将李显带到他阔别十四年的母亲的面前。她必得目睹他们母子之间的那悲欣交集。她必得离去。她这就要穿上她的衣裙,梳好她的头发,离开那个精疲力竭的男人。
她留恋那个给她以温情的男人的身体,她知道那身体对她来说有多么重要,但是她必须离开他。她离开他是为了去亲近另—个男人。取悦他,让他也给予她那满身心的热望和感情。她必得这样,从一个男人走向另一个男人。她要利用他们。她要利用他们对她的那浓浓的爱意和他们对她的那由衷的崇拜。她相信她会从他们那里得到她所需要的一切。她相信他们,不如说她更相信她自己。相信她对他们的那种深刻的诱惑力,相信她才会是他们的那个唯一。她要让他们的彼此需要成为一种生命的状态。她要让他们需要她就像是她需要他们一样。婉儿这样做着,在犹豫间在忧伤间从一个男人走向了另一个男人。她没有对他们说她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她让他们蒙在了鼓里,而唯有她,清醒着。
就这样。婉儿等候在李显的庭院中。李显匆匆走出。他意味深长地看着婉儿。经过了那个短暂而又漫长的孤单的长夜,他知道此时此刻婉儿对他来说有多重要。他觉得婉儿是他重新回到这陌生的而且是险恶的世界中唯一的亲人和朋友了。他视婉儿为亲人朋友。他知道他的选择不会错。他坚信婉儿从此将支撑着他。他觉得他已经从婉儿酌眼睛中看出了她的在所不辞。他这样想着这样坚定着他对婉儿的信念,他便在走向婉儿的时候在那个无人能看到的暗处抓住了婉儿的手,他甚至躲过了那个出门送他的韦王妃犀利的目光。
显抓住婉儿的手并低声对她说,婉儿,帮助我,给我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