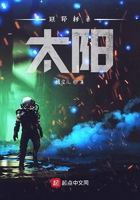那真是干净,关于这个男人,我总是觉得他干净,从头发到脚趾,从笑容到气味,就算跑完十公里满头大汗,我也愿意在他怀抱里被他黏得紧紧的,他住的地方,也永远是如此。
所有东西都在应该在的地方,该折叠的折叠着,该整齐的整齐着,苹果和橙子在果盘里摆成了好看的六角形,唯一凌乱的是阳光里飞舞的浮尘。
我去过两次,一次是正午,找他拿一个u盘拷贝资料,还有一次是深夜。会深夜跑去加蓝那里,绝不是因为我当时就懂得扑倒的可贵——我完全是被逼的。因为暑假,寝室室友都回家了,我第一年读大学,正在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的兴头上,放完假决定先不回家,做一个月兼职再说,说得好听社会实践,其实就是给一个小破学校当家教,整点儿一小时六十块的辛苦钱。
那天跟补习学校的同事上完一个暑假班,大家一时高兴,吆喝着去唱歌了,等半夜回来站在公寓门口一摸,头顶上顿时嗡了一声,我平常挂包包里面的钥匙不见了。
蹲在门口把包包翻了个底朝天,钥匙杳然,更糟糕的是,那天晚上唱歌AA制,我给完自己那份,身上就只剩下七八十块现金了,银行卡和身份证还锁寝室里,且不说有没有不用身份证的旅馆可去,就算有,我敢去吗?我长得再寒碜毕竟也是个女的啊。
那会儿时间去到了凌晨,暑假人去楼空的寝室走廊上一盏黄灯幽幽的,显得相当可怕,我丰富而不合时宜的想像力这时候醒了过来,一路往我脑子里深挖各种恐怖惊悚故事,我一开始还能保持镇定,想着各种方法解决眼下的问题,等楼道尽头的一盏灯突然之间卡擦炸裂,我再也绷不住了,撒腿出了楼门。
我往校外的出租屋一路飞奔,路灯照着我,校园里黑黝黝的,四处无人,唯独远处传来某个酒吧或者歌厅飘渺的音乐声,衬得林荫道上的安静格外浓厚。
傅加蓝带我上了楼,他正在看书,电脑放在一边,屏幕亮着,音响里非常轻微的放着歌剧似的什么音乐,唱的人特别来劲。看到他在这里我就完全放心了,我站起身去洗手间,嘟嘟囔囔上了个厕所洗了个脸,洗完我看了看,印象非常深刻。
地上干净,一点细碎脏东西都没有,洗手池也是,所有东西都整整齐齐,连镜子上也一尘不染,马桶里放了杀菌球,冲出来的水是蓝色的。挂在墙上的大浴巾雪白,我叉着手站在那儿,心想真应该把我寝室里那群女人弄过来上个家居清洁维护课——我们有本事把一礼拜的垃圾藏到开始招老鼠了才去丢啊,我们还是女的啊,人说豆蔻年华十八九的女的啊。
我走出去,看到床上摆了一件他的T恤,两条大浴巾,一条崭新的白色,一条是比较旧的蓝色。加蓝站在一边,说:“你洗个澡吗?”
我愣了一下,他马上说:“我出去买点东西,带了电话的,你慢慢弄,弄好了打电话给我。”
这真是体贴得让我想象不到,我感激地看了他一眼,伸手去拿那条蓝色浴巾和衣服,他抢先一步把两块浴巾都拿起来,直接走进了浴室,白色的挂在了墙壁上,蓝色那块铺到了地上,一边铺说:“这个地板很滑,垫块毛巾比较安全。”
他带上门走出去,嘴里还嘟囔了一句什么,我当时没听清楚。
因为我脑子里突然天打雷劈出现了三个字:处女座!!!!
这要不是处女座我要含血喷天啊。
然后我反应过来他刚说的是什么了:“掉了头发也好收拾。”
为了这句话,我洗澡的时候心不在焉,把洗发水拿来当沐浴露,搓半天才觉得感觉不对,我忙着琢磨去了:傅加蓝怎么会知道长头发的女孩子特别爱掉头发呢。
不管多细心多聪明,这种经验都不是琢磨出来的,都得是经历过,所以他是从妈妈那里学到的吗,还是表姐表妹留下的童年阴影。
或者他有一个女朋友,每处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会为她铺好这块浴巾,防滑,以及收集那些不听话的碎发。
那时候我心灵尚坚硬,可这个念头也困扰着我,困扰了很久。
我洗好出来,他果然没在,只有风扇开着。我收拾好了,打电话给他,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和家人以外的人共同度过一个晚上,我坐在床上,他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我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到终于扛不住睡意的时候,我鼓起勇气,惴惴不安地问了一句:“哎,等一下我睡着了,你不会吃我豆腐吧。”
他看着我笑起来,轻轻拍了拍我的脸,说:“毛毛,我不会欺负你的。”
我伸出了手指:“拉钩啊,不要等我睡着了你变身色魔,我会大叫的。”
他笑得更厉害了,却又非常认真地回应:“我保证不会的。”
我严肃地说:“我妈妈说了,除非是要结婚的人,否则不可以给男孩子占便宜。”
他楞了一下,说:“你妈妈说得对,毛毛,睡觉吧。”
他站起来:“我刚刚去学校招待所开了个房间,明天早上你出门前给我打个电话。”
他对我挥了挥手表示晚安,然后把他的房门钥匙放在了床头柜上,带着自己的手机和钱包就离开了房间。我跪在床上,趴着窗台看着他走过楼下树荫的暗影,默默的,忽然不知道我们两个,这算是正直还是蠢。
“当然是蠢。”
过了这么多年之后,于南桑给了我一个确认无疑的答案,她今天穿着一条大红色的裙子,带点旗袍款,上面有吉祥如意花纹遍布全身,料子带弹性,裹在身上,任何一丝赘肉想必都无所遁形,但她穿得泰然自若。
“十八岁到四十八岁,女人能够享受床第之欢的时间,最多就是三十年。”
她挑挑眉毛,精致圆润的手指点点我:“你,还有三分之二强,”又指指自己:“我呢,只剩三分之一弱了。”
“姐,你的point是啥。”
于南桑叹口气:“我的point就是,但凡你们俩中间的一个当时能对着对方扑上去,估计现在计划生育罚款都交了好几笔了吧。”
。。。。。
姐这是什么人生观。
她对我的震惊无动于衷:“直接动手吧,如果他毫无反应的话,你找错人了,他要么志不在你,要么志不在女人,在你献完青春献子孙之前,当务之急,是确认下半身在下半生的幸福。”
她还有心思荡开一个闲笔:“你看我身和生发音多清楚。”
骄傲个啥!
我对于南桑叹了口气:“我的天,你真是我见过最轻浮粗暴的女人啊。”
她风情万种的一笑,悠然说:“但是你喜欢,不是吗。”
那天我和于南桑喝完茶之后,回到办公司拿了自己的手提电脑,找了一个小办公室坐下,整个下午都没好好工作,而是在网上一气胡找,真是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我不但找到了我心目中的东西,还找到了更多我压根想都想不到的东西,甚至还有想都不敢想的东西,总之,下午六点半傅加蓝打电话给我问我晚上想吃什么的时候,我已经整个人重新接受了一次三观的洗礼,变得比三个小时之前更像一个正常的成熟人类了。
我急吼吼地在电话里叫傅加蓝:“我啥都不想吃了,你几点能回家?”
他有点莫名其妙:“啥都不想吃?你没有什么不舒服吧,你。。”
我赶紧打断他:“我一切都好,不要烦恼,这样,你呢,现在去你们公司对面的咖啡厅打包两个三明治,然后不要回头,不要犹豫,不要停,赶紧地往家赶,等我回来哪儿都不要去,好啦,就这样。”
电话啪地挂断,傅加蓝想必在那头露出了一脸茫然,但我现在顾不上他了,三下两除二收拾好东西,我跟同事打了个招呼就撒腿飞奔出办公室,打了个车直奔某个在网上一早锁定的地址,旋即提着大包小包,又飞奔回家。
八点左右,我回到傅加蓝的公寓,他正在客厅里吃着带回去的三明治,还有一杯奇异果汁,一面看一本刚刚邮寄到公寓的bloomberg英文商业杂志,身体放松,姿态悠闲,对于即将在他身上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
他看到我回来,想起身帮我拿东西,被我一把推开:“坐下,坐下,别管我。”
跟火烧了屁股一样,我匆匆忙忙杀到他卧室去,关了门又打开,还叮嘱他一句:“你不要进来啊,等我出来。”
加蓝举起双手,对我耸耸肩,一副见怪不怪的淡定模样,继续看他的杂志。
我呢,我在他卧室里紧张地忙活着,等一切准备就绪,我估摸着他吃得差不多,甚至也应该消化得差不多,一会儿不至于因为饥饿而昏迷,也不至于因为震惊而呕吐了,就出去了。
他抬头看着我,表情很迷惘:“毛毛,这么热的天,你穿着我冬天的浴袍是什么意思?”
我抹了一把汗抱怨:“我倒是想找你夏天的浴袍,问题是你没有对吧。”
过去牵着他的手就往卧室里拉:“过来,过来。”
他踢踢拖拖地,嘴里说着:“我还没洗手呢,你等等,哎哟,你怎么这么大劲儿我以前不知道啊。”
我一往无前,手下半点没松:“蒙古摔跤我也不是白练的,好了,你站这儿。”
我说的这儿,就是卧室的门口,我把门在他身后关上了,顺手关了吊灯,留下床头一盏阅读灯,虽然还不够旖旎,但好歹在这种光线下我的皮肤会显得比较细腻,因为内分泌失调而出现的痘痘也能被遮起来。
我鼓起勇气,咳嗽了一下,警告傅加蓝;“你一会儿不准笑。”
他很冷静地看看我,又看了看他自己的卧室,然后点点头:“我不笑。”
我又咳嗽了一声,正要说话,他打断我:“你看我们家一直单传,就我一个儿子,如果你现在要把我大卸八块的话,能允许我给我妈打个道别电话吗?”
我大叫起来:“严肃一点,严肃!!”
他赶紧退后一步,摆手摆手:“好好好,严肃,你不要激动,你继续。”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解开了身上那件厚重浴袍的带子。
我穿着一件黑色蕾丝的睡衣,丁字裤,没有穿内衣,所以我妈遗传给我的胸,那是相当的显眼,刚才我在主卧洗手间里穿好之后,自己都忍不住对着镜子看了好一会儿。
我闭着眼睛,插着腰,胡乱转了个圈,本来我准备了台词的,我准备要用平静而魅惑的声音,慢慢地说出:“我好看吗”这四个字,我认为这应该是最简单的台词和最没有难度的腔调,但事到临头,我发现颠倒众生四个字需要的技术含量直接爆表,绝不比徒手抓鳄鱼或者高空走钢丝少半分。
我既做不到平静,也做不到魅惑,我喉咙干涸,胸腔收紧,就跟马上有人会杀掉我似的,根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但我至少转完了那个圈。
是逃出大门,永远不再回来,还是坚持演完自己在脑海里彩排了一下午一晚上的戏,我吞了一口口水,想起于南桑戏谑的眼神,决定不能当逃兵。
于是我笨拙地扑向床上,因为跑太快,还差点被自己的拖鞋绊了一跤,我稳住身体,压根没机会去想姿态是否优雅或美好的问题,而是好像跟谁发脾气一样,一把拉开了傅加蓝的床罩。
床罩下面放着一排东西。
我和傅加蓝一前一后,都愣愣地看着那些东西。
沉默像睡神的羽翼一样降临,将身处其中的人温柔覆盖,
我的肩膀,腰和膝盖,一条线下去,都绷紧了,我听得到身后的傅加蓝轻微而绵长的呼吸声,并没有任何频率的变化,我不敢回头看他到底在看什么,又有什么神色。
到这里,我觉得自己的编排基本上已经都演砸了,刚才偷偷在洗手间灌下的龙舌兰就够支撑我走到这里了,只要傅加蓝凯开口说话,不管他说什么,我觉得我唯一的下场,就是在羞愤与懊悔里反复煎熬要不要自杀了。
世上没有后悔药买不是吗,我这种资质的女生,为什么会蠢到去相信于南桑对男人的判断啊。
她的判断都是基于胜利而来的,一个手指钩钩,男人就愿意为她做狗的女人,我有什么好模仿的,我最应该模仿的是孙二娘,谁敢不听话,我就劈死他那个范儿容易多了。
床罩下放的是羽毛调情套装,跳蛋,趣味前戏筛子和飞盘,还有一条男孩子穿的大象鼻子内裤,黑色的,****得那是相当彻底。
理论上我应该穿着我的暗夜妖姬性感套装,在傅加蓝面前旋转一圈,等他看直了眼睛之后,仪态万方地走上去一掀床罩,说:“轮到你了,选一样开始吧。”
现在,那句台词早就跑到了阑尾的某个缝隙里,绝对不可能轻易寻回,而我所有的勇气已经用尽,我懊恼地想,我真应该准备一个后备计划的,比如说放一把锤子在旁边,现在可以一把打晕自己,或者干脆把整瓶龙舌兰倒出来,喝得人事不知,就不必接受这么浓厚的尴尬和下一步的羞辱。
房间里那么安静,列在床上的东西都那么刺眼,我站了一阵子,如同大梦初醒,一阵阵的苦涩涌上心头,我想我这是在做什么。
这时候傅加蓝的手轻轻从后面抱住了我,抱得很紧,我一惊,身体绷紧了,耳朵边传来傅加蓝炽热的气息,他轻轻地说:“毛毛,你真美。”
他的手插进我的长发,微微用力,将我拉向他,在灯影里他神色温存,那么迷人,他俯向我,声音如同天籁回荡耳边,如同人鱼歌唱,唱出飘泊太久的水手终生渴望的美丽歌词。
第二天早上我迟到了,带着一脸傻笑走进办公室,屁股还没坐热就被于南桑叫进了她的办公室。
多年养成的习惯,不管于南桑叫我干啥,天塌下来我也要先看一眼她今天穿什么,今天是巴宝莉的卡其色贴身丝绸衬衣,黑色长裤,袖子随随便便挽起来,亮出她手腕上一根碧玉镯子,格外动人。
她示意我关上门,劈头就说:“joyce辞职了,下月底lastday。”
我一惊,下意识地说:“这么快?”
于南桑脸上没什么表情:“识时务者为俊杰,负隅顽抗的结果是很难看的。”
我点点头:“那倒是,大家好合好散。”
这个点儿上说我心里不兴奋激动乱哄哄那是假的,我暗自告诫自己世界上没有一次掉两个馅饼的事,一面情不自禁地看着于南桑,期待着她接下去要说什么。
果然,她对我扬扬下巴:“她的职位现在已经正式开放,我交给人力资源部去跟了。”
我不知道是释然好还是失望好,嗯了一声。
于南桑继续说:“猎头那边已经回来了好几个候选人,我下周就会开始面试,我看过简历了,有两个的背景和经验都很符合我们要求,薪酬也和我们的offer匹配。”
听她的口气,这是没我什么事了,毕竟joyce那个职位权责重大,我自己知道自己不够班。
当然是失望的,可也顿时觉得背上一松。
因为心里有一点不切实际的期待,这两个礼拜我活得像是一只蜗牛,想尽量爬得快,可先天条件实在不足,我妈以前常说,有多大的头戴多大的帽,否则不是箍住头就是蒙住眼,真是诚不我欺。
我全身心放松,往后一坐,说:“没我什么事了吧就?”
她看我一眼:“怎么听上去那么高兴?换个人多半都滚到地上开始哭了,你不想要joyce的位子吗。”
我诚心诚意:“我当然想要她的工资,她的待遇,还有那啥,公司还款的行政信用卡,but!”
是时候展现我心宽体胖的一面了:“这些都不是白给的对吧,不管是你还是joyce,看你们都忙成啥样?你就算了,joyce人家都四十了,内分泌失调得一泻千里,男人都没一个。”
于南桑一下就笑了:“你怎么知道人家男人没一个。”
她丢支铅笔过来,砸我胸大无脑:“joyce以前在某著名日化公司,从前台一路做到区域市场总监,所有升迁的节点都是睡通关的,你知道个屁。”
我下巴都掉了:“不会吧。”
Joyce和于南桑是绝对处于世界两级的女人,我觉得但凡认识她的人,都绝对不会认为她会喝“睡男人”这三个字扯上任何关系。
有一次我们在北京开区域经理会议,包括于南桑在内,大家都严格遵守员工着装手册,不是套装就是过膝中袖的连衣裙,结果joyce穿了一件男式的蓝色格子衬衣进来,肥大松宽,下面配条好像去做运动时候会穿的leggings,
素面朝天,眼圈黑得像被谁打过似的。
这都算了,我印象最深的是——她没有穿文胸。
就算那件男式衬衣再宽,在她行动之间,还是能看到她的关键部位,轮廓毕现。
当时主管西南区的同事是男生,晚上我们几个外地的一起喝酒,说到这事儿,他叹口气,说:“太矛盾了,又没法不看,又真他妈不好看。”
现在于南桑说出这么劲爆的话,我真是将信将疑:“不会吧,我以为外企不吃这一套。”
她对我眨眨眼:“太阳底下无新事,哪都有这一套,她以前呆过那个公司是潜规则的重灾区,业内的人都知道。”
摆摆手意思是把这事儿略过不提,我秒懂,站起来准备出去:“人各有志嘿,没我什么事就好,我出去了啊。”
于南桑喝住我:“谁说没你什么事的?”
“昂?”
“joyce走了,claire也呆不了多久,你接受move到上海来吗?”
这才是喜出望外啊,我脑子里噼里啪啦转过无数和傅加蓝双宿双飞形影不离的好日子,一下全身心扑到于南桑台面上:“我okokok
ok的啊,老板真的吗?不是玩我的吗。”
于南桑往后一坐,锐利的眼睛对我上下一扫,马上就了然:“这是搞定你男人了是吧。”
我一甩头:“没有呢。”
她将信将疑:“那你怎么跟昨天判若两人?你是那么容易想通的人吗。”
我嘻嘻笑:“没有没有啦。”
我赶紧打岔:“反正跟这个没关系,上海,这个上海是重要区域嘛,我这不是为我的职业前途着想吗。”
于南桑话里有话:“但愿你真的为职业前途着想。”
我确实没有搞定加蓝,可是我搞定了更关键的部分。
在深深吻我之后,他还是没有进一步的的举动,尽管我能感觉到他的反应,可这样柳下惠级的自制,无论如何都让我觉得忐忑。
直到加蓝说:“下次公众假期,我们一起回去,请两家人一起吃顿饭,好吗。”
他抱着我,抱得很紧,温柔地说:“一定要过你妈妈那一关不是吗。”
那么多年前说过的话,他一直都记得。
我心都甜透了,那些猜测和怀疑,都飞到了九霄云外,我双手环住他的腰,然后为自己刚才的举动觉得好笑,加蓝看到我笑,也实在忍不住开始笑,我们两这么抱着,在房间里笑成一团。
把脑子拉回眼前,好似在北宋年间穆桂英领军出征,帅营前丢牌子诸爱将听令,于南桑叫我:“你明后天就回广州去处理一下那边的工作,下月中旬过来交接。”
我一听这个也太仓促了:“claire那么快就走?我总得找个人顶我那边的工作吧。”
她摇摇头:“你那个位置不招人了,你两边顶着吧,细节我下周再跟你谈,至于claire,该走的时候她会走的。”
她的眼神转向了电脑屏幕,这是惯常逐客的姿态,我起身放好椅子离开,一出门就赶紧给傅加蓝发短信。
“你猜怎么着,我老板叫我来上海管部门。”
他很快就回了:“是吗?那很好啊。”
我觉得他说很好说得太轻率了,于是追问了一句:“真的?你不嫌我要跟你长住下去吗?”
他还是很快就回了:“你知道我的答案。”
我抱着手机贴在怀里就地转了两个圈,脚步轻盈得马上就可以平地起飞,这时乔孟涂从旁经过,叫住了我:“毛毛?”
我脸一红,赶紧停下来站好了,心想我什么时候跟你熟到你可以叫我小名啊大哥。
他神态轻松地看着我:“跟你老板谈过了。”
这二位还真是穿一条裤子的,我老老实实点头:“嗯。”
他看看四周无人,声音轻柔地说:“你管两个大区,以后就完全直接汇报给于南桑了,北京joyce的下一任也就是和你平起平坐。”
这个刚才倒是没说,估计是准备下周跟我详谈的时候再提的,我冲他笑笑,心想要是被于南桑发现你抢在她前面把底透给我,多半你又被她喷得一脸血。
但他看上去像是为我由衷高兴似的,或者也只是爱屋及乌,他伸出手拍了一记我的胳膊,说:“加油。”转身就往于南桑的办公室去了。
我惦记着傅加蓝的短信,一面走一面继续回:“那你不要后悔啦。”
按照他一贯的风格,他再也没有接我这个茬,而是直奔主题:“你的调任什么时候生效。”
“下下个月,我先要把上海这边接下来,再回一趟广州处理那边的交接。”
“以后就要忙起来了,对了,正要跟你说,我今晚要临时赶去杭州。”
我大失所望:“干什么去啊,本来以为一起去吃日本菜的。”
“对不起,lastminute的通知,回来再吃好吗?”
问是这么问,事实上我能对此有什么作为呢,只好蔫蔫地说:“本来想说不好的,但我觉得反正说也白说,不如深明大义算了。”
他轻笑一声:“那就好。”
电话挂了。
我本来包都拿好了,就等着下班冲回家陪男人,结果又变成手机水杯都拿出来摆成一排,继续蔫蔫地在办公室里干活。
做到大概八点多,我伸了个懒腰,肠胃咕噜噜作响,那是正式的饿了,正琢磨着一个人去吃什么好,忽然短信提示音滴滴一响。
我拿出来看,是个不认识的号码,短信正文什么都没说,只是附加了一张照片。
图片上像是一个餐厅的内景,桌椅灯光都很精致,像是时尚杂志上常常会推荐的那种好地方。
我等了很久,那个号码再没有响动,我拨打回去,声音长长的响着,却没人接听。
等我说服自己多半是一次寻常的发错,那个号码却又发来更多餐厅的图片,最后一张,是昏暗烛光下的两副刀叉,一瓶红酒,其他什么都没有说,什么都没有写,仿佛那一瓶酒已经蕴含了千言万语。
身后传来脚步声,我急忙站起来,把手机捏紧了,一看是于南桑。
她脸有倦色,外套脱下来放在了手里,里面是一件一字肩的小黑裙,她对我打招呼:“还没走。”
我楞楞地看了她好一会儿,下意识地点了两下头:“嗯啊。”
很明显于南桑不是很想说话,于是只对我摆摆手就往电梯走了,我目送她的背影差不多快要消失了,忽然想起什么,撒丫子奔上去:“姐,你帮我个忙好吗。”
电梯门在她面前打开又关上,于南桑转过来了:“怎么了。”
我把手机递过去:“这瓶酒怎么样。”
她看了一眼:“波尔多玛歌,年份看不清楚,你问这个干吗。”
别看她一副懒洋洋的样子,逮着机会就要洗刷我一下:“馋酒了?年纪轻轻就酗酒的话,可不大好啊。”
我小幅度地翻了个白眼表示我的无言以对:“估计要多少钱一瓶?”
她接过去放大屏幕又看了一遍,摇摇头:“灯光太暗了,这么看没法估计,如果这是在好餐厅点的,年份又还行,估计一两万吧?”
我倒抽一口凉气,吃顿饭喝瓶一两万的酒,这个世界怎么了?
她觉得无所谓:“各有各的吃法,上次大老板来请这边的运营团队吃饭,开了九六年的玛歌,结果大家不管三七二十一都干杯,我估计他下个月再来就会直接开长城了。”
万物生而平等,不分高低贵贱,直到你知道他们的价钱。
把手机抛回给我,于南桑补充了一句:“酒的问题你要问乔孟涂,他比较懂行。”扬长而去。
我脚步沉重地走回自己的位子,总觉得整件事儿有点什么不对,我拿着手机,在手里翻来覆去地捣鼓,过了一会儿,把那张图截了下来,放到百度上一搜。
搜索的结果,叫我整个人顿时就凉了半截。
有两个关键字在屏幕上亮着,亮得很刺眼。杭州。
这是一家杭州的餐厅,在凯悦酒店里面,各方食客都对之评价甚高。
我坐在位置上呆若木鸡,过了很久才鼓起勇气,发了个短信给加蓝:“你到杭州了吗,在做什么呢?”
然后我屏住呼吸,等着那一声叮叮响起。
保安大爷上来巡楼了,一个又一个区域的灯被关闭,最后只剩下我身边这一片是亮的,保安大爷好心地提醒我:“还不下班啊?快要赶不到地铁末班车了哦。”
我嗯了一声,拿起电话把电池取出来,把保护壳,手机和电池一字排开放在面前,小心翼翼地看着,等待着电脑右下方的时钟跳过一个又一个数字。
五分钟,简直跟做平板支撑一样煎熬,我跳起来四处转了一个圈,扑回去把手机装好电池,开机。
这么晚了,傅加蓝总不会在开会吧,不管他刚在做什么,洗澡也好,上洗手间也好,出去买了点东西也好,超过十分钟了,他总该回到手机旁边了。
可是我等了又等,他还是没有回我的短信。他在杭州做什么呢?我犹豫了好一会儿,拨通了他的电话。
“上海移动提醒您。。”
他关机了。
本来是好好的一天到现在,忽然就难受得无法独自度过接下来的时间。
我趴在桌子上努力调整呼吸,默默地激励自己,我得相信傅加蓝,就算他在杭州,田娜也在杭州,不代表他们就会在一起,杭州那么大,人那么多,也许他只是在接待客户呢,在夜总会花天酒地什么的,白天实在太多事所以手机没电了什么呢。
而那个号码吗?是田娜吗?就算是她,喝那么贵的酒,不应该是跟加蓝在一起吧,加蓝难道看起来很像冤大头吗。
我拼着老命建设自己的心理,一面默默拿了东西,回到傅加蓝的公寓,洗澡,换衣服,坐在公寓的客厅里,望着周围的一切出神,忽然之间,田娜的各种影像次第出现,在我坐的沙发上,在餐桌边,在厨房里,在洗手间,我甚至疑心如果我仔细去找,也许会找到她留下的长发,在各个角落横陈,黑漆漆地证明她曾对这里的一切拥有自然而然的使用权。
他人即地狱。
田娜对我来说是地狱,加蓝呢?谁是他的地狱?
加蓝第二天很晚才从回来,进门累得话都不说,直接倒头就睡了。我有心想问问他在杭州的情况,当时没开口,接下里就再没机会了——败在他针插不穿水泼不进的日程里了。
很显然他们组这次接的项目很很重要,平地一声雷的,就开始忙起来了。
加蓝向来都要出差,往往在一段时间之内不断去一个地方,曾经有过一个月飞十三次北京的光辉战绩,我们当时恋爱,也是因为他在广州做项目才能频繁见面。
现在的项目在上海周边,江浙一带,每个礼拜至少要去两次,一时南京,一时杭州,一时宁波,有一次的周末还呆在了普陀山,我难免纳闷,还想难道普陀山得道高僧们也需要融资方面的咨询么。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不断接到莫名其妙的短信,一个不认识的号码,用图片附加的方式给我发短信,每一张图片,都意味深长。
都是江浙一带的名胜,或享有盛誉的餐厅酒廊,某个五星级酒店看出去的夜景剪影,诸如此类。
我试图回复和拨打电话,无人应答,我把号码拉进黑名单,另一个新的号码又会出现,我找了移动的朋友帮我查查情况,却只能找到号码的归属地是上海,而登记号码的人名,在我人生里和自由女神像一样陌生。
加蓝的行程和那些照片的交集,密切得就像一本第八流侦探小说里破案的线索,又像是交叉在我胸口的两根绳索,一点一点收紧,一点一点收紧,渐渐使我喘不过气来。
当加蓝回到家里,我不再有那么多话跟他说,那通常都是深夜,我沉默地在卧室里,关了灯坐着,听着他开门,去洗澡,然后打开冰箱门,喝一瓶冰牛奶,他不会马上睡,往往还要在客厅呆一会儿,有时候处理邮件,有时候看看电视,声音调得很小。
我虔诚地希望他会注意到我的不同,会为我的故作姿态而有点惊讶,我希望他会走进卧室来,在床边看着装睡的我,轻轻抚摸我的头发,我会装作惊醒,抱住他的手臂,等待他问我:“最近怎么了,特别累吗?”
或者不需要他开始这个话题,只要给我一点点的关心和鼓励,我会勇敢地说:“你最近是不是老和田娜在一起?她老是发短信给我,我不开心。”
但这个对话始终只在我的幻想里反复,现实中却看不到任何发生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