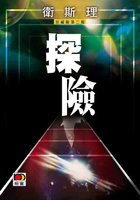1
1996年初夏,我即将从军校毕业的前夕,学校来了一位神秘的领导。
因为临近毕业,几乎每晚我们都会偷偷聊到很晚。我还记得那晚卧谈会的主题是卫生队里新来的几个女护士,我们聊到夜里一点才陆续睡去。
刚睡着没多久,一阵尖厉的哨声骤然响起,我的意识还停在美梦里,身体却像触了电似的从床上弹起来。整个宿舍开锅一样嘈杂,窸窸窣窣穿衣服的声音、手忙脚乱扣武装带的声音、蹲在床上找东西的声音掺杂在一起。有人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嘟囔着:“这都快毕业了,怎么还来这套?”
这些年在军校里,这哨声简直成了我们的噩梦。甭管你是在刷牙还是洗澡,就算上厕所尿到一半,只要哨声响起,就必须在三分钟内武装完毕,打好背包站在楼下。以至于就算是放假回家,窗外有小孩吹哨,浑身都会立刻紧绷起来。
作为还有三个月就毕业的我们,已经很少有紧急集合的情况了,我们也都在夜里慢慢地放松了神经,没想到今天又来了这么一出。拜这些年所赐,我练出一个绝技:从听到哨声开始,起床,套上裤子一直到打背包,再到检查着装,最后飞速跑到楼下,全程不用睁眼一气呵成。
我和其他104名同学飞快地站到操场上,标准间距三步列队站好后,极不情愿地睁开眼,才注意到教官身边站着一位校领导,还有一位从来没见过的首长,凭借微弱的光线只能看到他肩上的大校军衔。
我隐约感觉到,这一天的紧急集合非比寻常。
党委书记和那位面生的首长低声交谈了几句后,首长微低着头背着手走进队列里,像是在小树林里散步似的,偶尔停下来好像在思考什么事,停不了几秒又继续在队列里穿行。
他从我面前一共路过了四次,每次我都加倍绷直背脊抬着下巴。
他中等身材,我斜眼偷偷瞥过去,只能看到他帽檐下露出的鼻梁。
出什么事了?难道有谁闯了祸,上面派人来彻查?那这得多大的过错啊。我心里七七八八地想着,天色一点点亮起来。
升旗的旗手护着国旗正步从我们队前经过,朝升旗台走去,起床的号声这才响了起来。
那首长走出了队列,打开手里的本子唰唰写了一通,撕下来递给校领导,他们相互行了个军礼就低着头离开了。书记看看手里的纸,抬眼看了看我们,大声说道:“我点到的同学出列!一排第一、第四,二排第三、第六……”
我被点到了!
我顿时明白,首长是来挑人的。
站了一个多小时,腿已经有点儿发木,我正步出列走到队伍前面,跟其他19名同学站成一列。我扫了一眼与我一同被挑出来的同学,希望能找出我们的共同点,但很快就死心了。就成绩而言,我们这20人可谓遍布上中下三个级别:既有全能型的优等生,也有年年垫底的老末;既有成绩不高不低的中游“砥柱”,也有成绩毫无逻辑上蹿下跳让教官心脏不适的跳跃生。
大家一定都揣着很多疑问,有人已经忍不住互相交换疑惑的眼色。但条例明确规定,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
我只能静等答案,也有可能,永远都不能得到答案。
接下来,我们被那位首长不知以什么标准又筛了四次。在这个过程中,文没有理论考试,武没有体能测试,只是挨个儿找我们聊天。后来我和其他同学聊起,发现他和每个人每次谈话的主题都各不相同,天南海北,甚至上一个问题跟下一个问题完全不挨着。
聊天过程中,他始终保持着一个表情,就是没有表情。因此根本无从判断什么是正确答案,所以在回答问题时,只能凭着自己的本能迅速地做出回答。以前比武练兵也好,理论考试也好,谁不服谁想较劲儿也有个明确的指标。这次想创先争优,却根本连分数线都不设。
一周后,我再次来到他在学院的临时办公室,屋里多了两个我的同学:一排的宁志和三排的郑勇。
这位神秘莫测的首长坐在办公桌后,手里拿着几个文件夹,言简意赅地对我们说:“我奉命组建特案组,你们三人的各项条件均最符合或最接近我的选拔标准。你们每人有机会问我一个问题,没问题就准备就位。”他说话声音很低,但是很有力。
我心中一阵狂喜,几乎要笑了出来。我终于留到了最后!这几年,我们每个人最担心的就是毕业后会被分配到城市执勤,或是派到边疆派出所去。如今我显然将要提前告别这种担心,心情真是大好。
什么是特案组?有多少人?执行什么任务?……我脑中瞬间涌出无数个问题,可首长说得很明白,每人只能提一个问题。如果想知道这个特案组到底有多重要,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看它属谁管。我组织了一下语言,问道:“特案组向谁负责?”
首长说:“向我负责。”
一时间,我无法判断这个答案的分量。可惜每人只能问一个问题,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宁志和郑勇的问题上了。
宁志的问题是:“什么是特案?”
我用余光瞥了他一眼,我们不同班,没怎么打过交道。他的问题很棒,也是我最想知道的问题之一:我们不担心特案太特别,而是担心特案不够特。四年军校上到如今,每天按时出操以及教程上枯燥的训练模式早已满足不了我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听教官讲稀奇古怪的真实案例。
首长回答说:“公安部门处理不了,军方又不便出面,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安全的案件。”
宁志的表情显然对这个答案也不够满意,继续追问又是不被允许的,他瞄了一眼郑勇,意思是让郑勇接着问。郑勇问的是:“装备是什么级别?”
首长说:“特级。”
郑勇一个立正:“没问题了。”
我和宁志赶紧也跟着立正挺胸说:“没问题了。”
首长递给我们一人一个文件夹,说:“这是你们进入特案组前宣誓的誓言,你们仔细看清楚每一个字。如果做不到现在就放弃,绝对不能有一点儿勉强。”
我默念着纸上的一字一句,心里翻江倒海血脉偾张,我知道他俩跟我一样,恨不得立刻就能得到一个任务来证实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兑现这纸上的誓言——其实从进入这所院校穿上这身军装起,我们就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
我们不约而同地立正敬礼,表示已经准备好了。
就这样,1996年初夏的一个下午,我们站在学校小礼堂的主席台上,在校党委书记的见证下,面对着国旗、党旗宣誓:“我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特案组警员。我宣誓,绝对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服从命令、严守纪律、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忠于职守;坚决完成任务;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背叛祖国,绝不叛离武警部队。”
首长静静地站在一旁,等我们宣誓完成,走过来站在我们面前,足足盯着我们看了有五分钟,看得我们浑身发毛后才缓缓说:“从现在起,你们和我,既是同事,也是战友。我叫徐卫东,是你们的直接上级,你们可以叫我老徐,也可以直接叫我的名字。”
说完,他上前和我们挨个儿握手。我习惯性地想敬军礼,他狠狠地在我抬起的胳膊上打了一下:“从这里出去以后,你们将脱下军装,我不允许你们身上再有明显的军姿出现。”
从礼堂出来后,徐卫东给我们下了第一个命令:不能和任何人打招呼,十五分钟内收拾好行装。
二十分钟后,我们坐上一辆挂着地方牌照很不起眼的轿车,离开了学院。我们三人不约而同地回头朝越来越远的学校大门眺望,直到车子转了一个弯,再也看不到了,我们才扭过头。
2
我们被直接拉到位于密云深山里的一个训练基地,除了吃饭睡觉,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看幻灯片、录像和卷宗。内容大多是境外毒品、枪支走私和制售的情况资料,还有案件多发地,尤其是西北、西南几省的人文和地理。
开始一段时间还觉得新鲜,尤其是那些重大案件的图像资料,看得我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恨不得立刻奔赴第一现场跟犯罪分子真刀真枪地大干一场,然后领功、受奖、鲜花、掌声……可日子一久,慢慢就觉得腻了。面对着四周巍巍的大山,一天天地数着日子,我们甚至开始怀疑领导是否已经忘了我们这档子事了。
郑勇像个泄了气的皮球,得空就对着我和宁志直呼上当。他是南方人,却长了个五大三粗的骨架,酷爱北方的一切吃食,尤其是羊肉和煎饼。午饭时候他又在一旁望着窗外唉声叹气,我只好安慰他说:“这里伙食比学校好多了,有很正点的内蒙羊腿肉吃。哦,这里没煎饼馃子,回头咱去天津,吃最正宗的。”
郑勇把筷子一蹾,冲我翻白眼:“合着我就是为吃干这个的?”
宁志哈哈一笑,正要说什么,突然撂下碗筷笔挺地站了起来。
徐卫东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我们面前,我和郑勇还没来得及站起来,徐卫东照着宁志的腿上就踹了一脚,指着我们说:“来之前我怎么跟你们说的?动不动就立正的毛病怎么还没改?再让我看到一次,就都给我滚回学校去。”他冷冷地瞪了我们一眼说,“跟我走。”
我们赶紧跟在他身后出门,上了他的车。徐卫东把车开得飞快,一路无话狂飙了三个小时,半夜时分到了内蒙古伊克昭盟(鄂尔多斯市的旧称),住进了当地支队的招待所待命。
郑勇兴奋异常,整晚喋喋不休,临睡前在被窝里枕着自己胳膊看着天花板,嘿嘿地乐着说:“看到没?活儿来了!你们猜是什么类型的任务?”
宁志淡淡地说:“我估计是演习。”
尽管我对这次任务也一无所知,但直觉告诉我,我等的这一天终于来了。肯定是很重要的任务等我们去完成。我也兴奋,更多的却是不安。
这是一种对于未知事物的惶恐,徐卫东两个月前从105个学员里选出我们三个来的时候,我就有过这样惶恐的感觉。我太知道自己的分量了,论体能、论谋略我排不到前三十,宁志和郑勇跟我是半斤对八两。我们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让徐卫东把我们挑出来?我总想从徐卫东的一言一行里找出点儿逻辑来,但他除了走路带风、老皱着眉、说话声音特别低之外,本身也没什么特别之处。
郑勇和宁志还在漫无边际且毫无根据地猜测着任务,我不想参与,闭着眼又睡不着,不由得想起了两个月前的那个深夜。
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徐卫东。
也是在凌晨的这个点儿,他用紧急集合哨把我们集合在操场上,我、宁志和郑勇三人从此就走上了一条注定跟其他同学不一样的道路。
徐卫东敲门叫醒我们时,窗外还是黑漆漆的,我看了眼手表,凌晨四点。
三分钟内收拾利索后,徐卫东开车拉着我们出市区往西,奔了五十公里左右后车子下了公路,感觉是进了一片荒无人烟的沙地。
车停在一个三面都有沙坡的隘口上,徐卫东熄了灯,扔给我们一人一副大墨镜和一个防爆头盔,示意我们戴上。周遭本来就雾蒙蒙的,戴上墨镜和头盔后就更是什么都看不清楚了,我们摸索着下了车。徐卫东掀开后备厢,说:“来,一人一支。”
后备厢里有一个枪架,上面赫然挺立着三支八一式自动步枪,在微弱的天光下泛着幽幽的蓝光。徐卫东说:“上车检查枪支弹药,今天的任务是枪毙死刑犯。”
拿了枪正要抬脚上车的我一个趔趄差点儿绊倒。人形的靶子我打过,人形的人是真没打过。尽管我们都清楚这是早晚的事,训练时教官也一再提醒要把靶子当罪犯,每次我也会把准星后的靶子想象成一个有血有肉的大活人。真的听到要荷枪实弹击毙罪犯了,还是大吃一惊——在区区两个月前,我们还只是某指挥学院里的普通学员。现在,因为眼前这个叫徐卫东的人,我们就成了死刑执行人,要用手中的枪去结束别人的生命。
尽管那些都是罪大恶极的死刑犯。
但这毕竟是杀人。
一阵汽车引擎的轰鸣声把我拽回现实。我定了定神,见三辆依维柯囚车在八辆越野车的护送下已经到了现场。一个中尉军官跑步到徐卫东面前立正敬礼,递给他一个文件夹。徐卫东唰唰签完字,军官接过,转身朝囚车跑步过去。
徐卫东对我们说:“必须一枪一个,而且要保证一枪毙命,否则开除。”
我们齐声应道:“是!”
徐卫东一脚踹到我腿上:“是什么是?”我忙改口说:“收到。”徐卫东点点头,“嗯”了一声。
郑勇的肩膀微微地抖了几下,隔着头盔和墨镜,我看不到他的脸,但我知道他是在笑。我压低声音说:“好笑吗!”跟了徐卫东之后,我们都不由得跟着他养成一个说话刻意压低声音的习惯,这样说话老让人有种错觉,总觉得附近有人在偷听你讲话。
郑勇的肩膀抖得更厉害了,还频频点头。
囚车和护卫车的号牌被迷彩布遮挡着,每辆依维柯上押下来三个犯人,一共九人,双手被反绑得结结实实。押运战士将头一批三个按着头快步拖到最大的那个沙坡前,之所以说“拖”,是因为每个犯人的腿都是软的,根本站不住,整个身体不停地朝下出溜,若不是押送的武警左右架着他们,他们一定会瘫在地上。
徐卫东用下巴指了指那个方向:“利索点儿,一人一个,打完跑步回车里待命。”
郑勇第一个冲下车,边跑边拉枪栓,枪口朝下向犯人快步走去。看得出他的步伐有些凌乱,好几次鞋底都蹭到了地面上凸起的石块。我和宁志忙下车跟在郑勇身后跑步前进。
厚重的头盔将我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开来,只听得见自己越来越急促的呼吸和怦怦的心跳声,渐渐地,觉得连气也喘不上来了。
三辆车雪亮的大灯正正地照在每一个死刑犯身上,几个武警战士手持着枪,面朝外呈半圆形处于警戒状态半包围着现场。
这方圆几百米像是被这世界暂时遗忘了似的,天地间只剩下黑白两种颜色。
郑勇第一个就位,在距离犯人一米的地方抬起枪对准犯人的后脑,没有丝毫迟疑就开了枪。“嗒”的一声枪响,犯人应声一头朝前栽去,抽搐了几下彻底没了动静。郑勇凑近一步低头确认犯人已死,转身返回。
我只觉得嗓子发干,想咽口口水,却发觉嘴里更干,硬着头皮走到犯人身后抬起枪对着那犯人的后脑,耳朵里开始轰鸣起来。我长舒一口气,死盯着准星,很快我的眼里除了准星和准星对准的目标外,什么也看不到了。我心一横,牙一咬扣动了扳机,身体在后坐力的作用下快速有力地晃了一下,恍惚中仿佛听到了子弹冲出枪膛、穿过犯人头颅打入沙石里的声音。
听着回荡在晨曦空旷野外的枪声,我勉强低头看了一眼栽倒的死刑犯,转过身咬着牙拼命甩了甩头,想晃醒阵阵发昏的大脑。往回走时两条腿像是踩在棉花堆里一样使不上劲,我大口地喘着气,连拖带挪地朝车的方向移动着双腿。没走出两步又听见“嗒”的一声,那是宁志开了枪。我的双脚在那声枪响之后更加发软,无论怎么用力都不听我使唤,好几次若不是在用枪撑着地,我几乎就要瘫倒在地上。
挣扎中一抬头,只见车门内伸出一只戴着白手套的手,正指着我。我知道那是徐卫东的手,他的身体隐没在车厢内的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我知道他是在示意我,如果我真的瘫倒,那么就会立刻出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