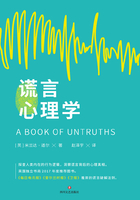经过一天的攀爬我们都已精疲力竭,望着消失在暮色中的依塔洪和阿曼,我深深地被他们的淳朴和善良所打动。队员马玉山感慨地说:“如今即使在山里也很难遇到这样淳朴的人了。”
晚上,我们9个人挤在一顶帐篷里喝茶聊天,有心的吕俊突然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大橙子作为礼物送给了小雨。大家突然想起今天正是2月14日情人节。小雨惊喜万分,她双手捧着这个“情人节礼物”激动地说:“这是我过的最有意义的情人节,8个汉子就我1个青春靓丽的女孩子……”
到达了萨郎开来,维吾尔语意思是“傻子才来的地方”
虽说是租用了3头毛驴,但每个队员负重都在20公斤以上。沿着克里雅河谷陡峭的山崖连续翻越3个达坂后,队伍又下到了布满冰瀑的谷底。纵深的峡谷挡住了阳光,雪花和雾气的笼罩使谷底显得格外的阴森。此时队员们已是饥寒交迫,体力也到了极限,尽管穿着厚厚的羽绒服还是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我们进山前拜访了于田县玉石矿的安矿长,听说我们要去火山口,他认为我们是一群疯子,并反复告诫我们,昆仑山每年的11月到来年的5月大雪封山,气候极其寒冷,进山就等于送死。在人们的印象中,冬季的昆仑山自然是大雪封山,人迹罕至,其实,由于昆仑山是个干旱的极地,年降雨量很少,冬季下雪也很快被升华,留在地表的积雪很少。但山区的寒冷的确让人难以忍受,白天时而阳光普照,时而寒风凛凛,气温一般在-20℃以下,夜里气温超过-30℃。由于普鲁河水大都发源于上游的山泉,狭窄的普鲁河并没有被冰封,河谷中除了巨石和大大小小的冰川瀑布外,河道中始终流淌着一股清澈的泉水。
晚上,顺着山谷而下的风吹得帐篷“哗哗”作响,想想明天的行程大家心里都沉甸甸的。毛驴在冰上是无法行走的,河水也不知有多深,毛驴能否继续前行谁也不知道,才进山两天,如果毛驴不能走了,靠人力背上所有的物资,我们能到达火山口吗?
一夜的降雪给昆仑山披上了银装,气温也降到了-30℃。依塔洪和阿曼冻得一夜没睡好,一大早起来就急忙清理毛驴身上的积雪。早饭后,按照依塔洪的要求,所有队员开始在冰上撒沙子,给毛驴铺路,这是唯一让毛驴继续前进的办法。
连续的铺路、涉水,行军速度慢得像蜗牛似的,队员的体力消耗也很大。经过近10个小时的行进,下午6时队伍到达了萨郎开来(维吾尔语意思是“傻子才来的地方”)峡谷。这里海拔4100米,前方的峡谷变成只有几米宽的“一线天”,两侧垂直峭立的崖壁上满是摇摇欲坠的巨石,跌落的河水在峡谷底部形成了一个个数米高的冰瀑,当年筑路部队沿着山坡铺设的路基早已因山体坍塌而难以辨认。此时,天气突变,风雪交加,依塔洪说,毛驴不能再走了,几天没草吃的毛驴如不及时返回便会死在这里。
毛驴不能走了,小雨也必须下撤
望着从毛驴上卸下的物资,大家心里都在犯怵。按照目前的行军速度到火山口至少还要4天时间,更何况还要带上这些装备。在这最困难的时刻,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到了小雨身上。她是9名队员中唯一的女孩,是从上海专程赶来的,为了能参加这次活动她献了400毫升血,换取了15天的休假。我对着风雪中瑟瑟发抖的小雨说:“你还能走吗”?她回答:“不背东西可能还行。”
“今天走到现在,直线距离才走了3公里,前面的路还远呢,小雨,你不背东西也走不动了……”我话音未落,小雨就哭了,默默地、不停地流泪,似乎是巍巍昆仑需要这样的眼泪,坚毅的汉子需要这份柔情……我脱去手套,用手背擦去她的眼泪。
有些地方一生也许只能去一次,即使失败了那也是一种美。对于小雨而言,虽说有点遗憾,但这种遗憾值得一生回味。
雪更大了,探险仍要继续,我挑选了吕俊、马玉山、甄晨光、邢睿四名队员,依塔洪也许是被我们的勇敢所感动,愿意与我们一同前行,而阿曼牵着3头毛驴带小雨、褚东田、刘湘晨、董在中返回。为了减轻重量,我们在此处埋下返程时用的部分食物及燃料,多余的物品全部让毛驴驮回,其中包括吕俊心爱的佳能70-200毫米的镜头。为了确保活动的成功,5名继续前往火山口的队员不得不分担了两只羊的肉,使得每人的负重达到了35公斤以上。
临分别时,吕俊从怀里取出了橙子再次送到了小雨的面前,那是她的情人节礼物,没舍得吃,让吕俊帮她带着的。
“带回路上吃吧。”吕俊对小雨说。“还是带到山上去吧。”小雨话音未落,便情不自禁扑在吕俊的怀里,再次流下了眼泪。
分手时,大家心里都很难受,紧紧地相互拥抱。
忍受不了寒冷,向导也不愿意向前走了
又飘了一夜的雪花,早晨起来天灰蒙蒙的,由于4名队员的突然离开,大家心里都沉甸甸的,多少感到有点孤单。
每个人的背包都重了很多,队员们一走一晃地很不适应,没走几步就明显感到胸闷气短。虽然气温达到了-20℃,但大家的内衣还是被汗水湿透。出发没多久,就进入了危机四伏的“一线天”峡谷,行进中不时地听到落石砸向地面发出的响声。我们不敢滞留,不敢大声说话,拼命地沿着谷底向上攀爬,只想尽快离开这个鬼门关。
走出一线天峡谷后,河道渐渐宽了起来,在河道东侧的一块平坦处有许多用石头垒起的无名坟堆。在一座黑色大山下有十几堆垒得很规整的铁矿石,少说也有几百吨。听向导依塔洪说,这些坟墓都是修路和开矿的人留下的,当年正是大炼钢铁的时代,开矿人指望着道路修通后能再把矿石运出去。
随着海拔的升高,气温越来越低,穿一双球鞋和一条薄毛裤的依塔洪,哪里能抵御住超过-20℃的严寒!当我们赶上他时,他正躲在一块巨石后避风,他似乎冻得话都说不出来,抬手指了指巨石的下方。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巨石下的一幕令人毛骨悚然——只见巨石下的缝隙里藏着一具死尸,衣服完好,骨肉也没有完全分离,在其周围十几米范围内还有一具被肢解的尸骨。听依塔洪说,一年前,有三个从普鲁村去火山口找宝石的人,翻过达坂到火山口后,一个人得高山病死在高原,剩下两个丢弃了所有东西往回跑,在这里一个给冻死了,另一个被狼吃了。看着死者狰狞的面孔和遍地散落的衣物和尸骨,我们都感到了恐惧。离开时,甄晨光虔诚地在大石头上放了9块糖,深深地鞠了一躬,代表我们9名探险队员向死者致意。
为了远离晦气的死人沟,当天我们一直行进到天黑,晚上在海拔4200米处的石崖下扎营。缺氧和寒冷使我朦朦胧胧地度过了一夜。天还不亮,向导依塔洪就拉开了我们的帐篷,说他腿痛得一夜没睡,要回家去。望着他那双冻肿的双脚我又能说什么呢?我烧了点热水,给他吃了一粒芬必得,甄晨光拿出了一双线袜,马玉山脱下了身上的冲锋衣给他穿上,临分别时甄晨光把仅有的西洋参含片也给了他。
望着依塔洪远去的背影,我们既难受也担心,祈祷他能尽快赶上昨天返回的队伍,安全地回到普鲁村。
路程、海拔、体能、重负行军,使我们在进与退中抉择
离开普鲁村的第四天下午,我们终于到达了苏巴什。卫星导航仪显示从普鲁村到这里直线距离27.8公里,而到火山口直线距离还有31.8公里,这意味着我们4天走了还不到一半路程,而且是马不停蹄地从天亮走到天黑,昆仑山的路真是不能用距离来衡量的!
苏巴什,维吾尔语意为“有水的地方”,海拔4220米。在两个河道交界处,尽管这里气温在-25℃,但仍然有一大股泉水在河道中流淌。当年修筑的路基一直延伸到一处平坦开阔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废弃的院落和几间石头垒砌的房屋,据说是当年筑路大军的前线指挥部。这里的石屋子都没有了屋顶,我们在一个较大的石屋中支起了两顶帐篷。
瓦斯炉在帐篷里不停地烧着,尽管昆仑山的冬季寒风刺骨,但坐在帐篷里还是有点家的温暖。面对严峻的现实,队员邢睿以开玩笑的口气说:“不行我们在这里住几天再回去,就说我们到火山口了。”虽说是句玩笑话,但大家心里都在犯嘀咕。
离开苏巴什沿着干枯的河床南行两个小时后,我们又进入了一个由彩色砂岩构成的峡谷地带,由于常年风雨的侵蚀,两边的砂岩形成了千姿百态的造型。峡谷的坡度很大,海拔急剧升高,前方几公里处便是让人谈虎色变的硫磺达坂。这座达坂的名字也许和火山喷发有着某种关系。据说当年部队到达这里时,硫磺的气味很重,故起名硫磺达坂,而当地维吾尔人把这座达坂叫依斯达坂,意为“有瘴气的地方”。下午五点左右,我、马玉山和甄晨光到达了海拔4700米的达坂脚下,看时间还早,我们轻装攀上达坂侦察。
硫磺达坂位于青藏高原的北部边缘,海拔5114米,翻过达坂就进入了平均海拔5000米的阿什库勒盆地。从山脚下到达坂顶直线距离2公里,海拔上升415米。坡大、雪深加上刺骨的寒风,使得翻越达坂如同攀登雪山一样。天快黑时我和马玉山到达了达坂顶部,我俩没敢停留,迅速下撤,途中劝退了正在向上攀爬的体力严重透支的吕俊。
我们已经离开普鲁村5天了,海拔也升高到了4710米,离村子至少也有70公里的实际行程。晚上我们5个人坐在一顶帐篷里,神情异常严肃。此时大家心里都明白,要想翻过硫磺达坂到达火山口来回至少还需3天时间,在平均海拔5000米的高原上负重行走近百公里,一旦翻过达坂后身体出现问题,后果是非常可怕的——那时谁也帮不了你,你将永远地留在高原。
说心里话我当时都想到了放弃,因为生命不仅仅属于我自己。晚上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们决定让甄晨光和邢睿原路返回,同时达成了一个残酷的约定:翻过硫磺达坂后一旦有人身体出现问题不能自己行走,其余队员不用管他,迅速下撤保全自己。
我们孤零零的三人感到了孤独和恐惧
在严冬季节探访火山口可以说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冒险行动。早在20世纪初,日本探险家橘瑞超在第三次中亚探险时,选择夏天最适宜的季节,试图沿着这条高原秘道进入甘肃。他在普鲁村雇用了30多名驮工,租用了几十头毛驴和马匹,最后也没能如愿以偿。当他历经艰险翻越硫磺达坂到达青藏高原火山口附近的色格孜库勒淡水湖时,驮工都逃跑了,毛驴和马匹几乎都死了,就连他自己也得了高山病差点死在那里。
一夜的寒冷和缺氧使得本已感冒的吕俊开始咳嗽,出现了高山肺水肿的病兆,如不迅速降低高度,病情就可能恶化,一旦发病想下也下不去了。在这危急关头,我不由分说让邢睿护送吕俊立刻返回。甄晨光担心我和马玉山势单力薄难以应付突发事件,决定和我们一起去火山口。
望着队友远去的身影,我的心情顷刻沉重起来。短短6天两批队员下撤了,加上放在帐篷外面的羊肉也被狼叼走,我们孤零零的三人在寒冷贫瘠的昆仑山深处真的感到了孤独和恐惧。当时最怕的是遇到狼群,出发时我把猎刀挂在了包外,默默地祈祷昆仑山能保佑我们安全翻越硫磺达坂到达火山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