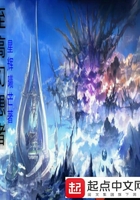走向曲谷达克高山牧场
曲谷达克是桑株达坂以南的高山牧场,它平均海拔4200米,也是古往今来人们翻越达坂前最后的落脚之地。从阿喀孜到曲谷达克高山牧场直线距离少说也有50公里,海拔会迅速地上升到4000多米。我们不仅要通过更险要的栈道,而且还会因为栈道的中断频繁地在河水中穿行。为了能让大家尽快地适应高海拔地区,安全地通过险境,出发前我就叮咛每个队员:照顾好自己就是对团队的最大贡献,只要能走就不要骑毛驴。
出发没多久我们便遇到了一个河汊,一条来自东边山谷的河流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早已做好频繁渡河心理准备的我不由分说地脱掉裤子就跳进了冰冷刺骨的河中。当我登上对岸后,才发现马玉山已经带着其他队员从不远处的一个铁索桥上渡过了河。我的鲁莽引来了大家一阵嬉笑,都说我有暴露癖。我笑着想,也好,我能给大家枯燥无趣的行走添些笑料也是件幸福的事情。
通过前一天艰苦的“演练”,队员们在栈道上行走的速度也快了许多,两个小时后队伍进入了一处狭窄的河谷。两侧高山耸立,湍急的河水紧贴着右侧山体咆哮而下,在我们行进的河岸上堆满了山洪冲下来的卵石。让我们感到费解的是,在河岸上有一堵厚约2米、长约80米的卵石垒砌的墙。它依山势而建,从它那残缺不齐的墙壁可以猜测出,它至少也经受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从工程量和用途上来看,它绝非是当地的游牧民族所为。这墙究竟建于何时,用以何途,令我疑惑。如果是出于军事目的,那为什么详细记录这条古道的探险家特林格勒也没留下任何笔墨呢?这也成了我们此行旅途中的未解之谜。
中午时分,当我们登上一座山梁,视野豁然开阔。一个由绿树簇拥的院落坐落在河谷中央,这便是特林格勒在探险日记中提到过的库尔梁。这是一个古老的牧场,常驻有几户柯尔克孜人家,每到夏季,驮工依明80多岁的岳父就会到这里放羊。前方的道路被河流阻断,峭壁上也看不到栈道,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强行渡河。
中午的河水涨了许多,已经没到了毛驴的肚皮。也许是“回家”心切,当我们赶到河边时,毛驴已经渡过了河直奔库尔梁,不见了踪影。轮到我们时可没那么幸运,湍急的河水把老张的涉水鞋冲走了;田慧虽有驮工的保护,还是被冲倒在河中浑身上下湿透了,随身带的各种电子设备也进了水;郑燕更倒霉,由于河水太急,在水中站立不稳,小腿被激流中的暗石撞伤,皮下血管破裂,小腿上瞬间鼓起了拳头大的包。好在其他的队员都有惊无险,最终大家齐心协力渡过了这段河道。
柯尔克孜人大都分布在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及昆仑山与天山的山结一带,是一个与高山为伍的民族,恶劣的环境造就了他们坚强的体魄。当我们沿着河道向库尔梁行进时,看到了几位从桑株达坂过来的牧羊人,他们身背行囊,穿着露着脚趾的解放鞋,在没有栈道的峭壁上攀爬跳跃,身手之矫健让我们这些户外老驴望尘莫及。
一整天的攀爬和不停地涉水,使队员们体力消耗很大,田慧、瓜子和马玉山的双脚打满了水泡。田慧第一次徒步就来到了昆仑山,行军难度远远超过了她的想象。其他的队员虽然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也被崎岖艰险的道路折磨得够呛。直到傍晚,暴涨的河水阻止了我们前行,探险队到达地图上标有苏干特阿合侧的地方。这里海拔3000米,有一块昆仑山中不多见的绿地,葱绿的草坪中簇拥着茂密的马莲草,清澈的山泉汇成涓涓流淌的小溪在草坪中穿行。累了一天的我们,都四肢展开躺在草坪上,享受着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片刻安宁。扎好营地后,大家集中在一起,对几天的行程进行了客观的总结,并指出未来的几天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提示大家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这一刻,甄晨光打开了摄像机,记录下每一个队员面对雪山之巅内心最深切的盼望与信心。
夜里,由于营地建在了河边,震耳欲聋的水声以及未知的旅程使队员们难以入睡。天一亮我们就出发了。
从苏干特阿合侧南行不久,河谷渐渐开阔。远处巍峨的雪山像一堵巨大的城墙把河谷隔断,河谷尽头跌宕起伏的山丘便是曲谷达克高山牧场。发源于南部雪山的一道道冰川,顺山谷而下,与山丘相接壤。在接近山丘时,河谷开始向东南方向延伸,河水渐渐小了下来。在河谷转弯处有一个向西延伸的山谷,十几个一米多高的天然石柱呈“一”字形排列,静静地耸立在山谷的入口处,每个石柱的上端都放有兽皮和石块。岁月斑驳,一个个耸立的石柱,一块块垒起的石头,似乎在向我们诉说着古道的沧桑。我和马玉山猜测这是千百年来来往于古道的人们的一种祭祀。我俩也走向石柱,虔诚地放上了一个小石块。
曲谷达克牧场四面环山,每到夏季,贫瘠的山丘在雪山融水的滋润下披上了一层绿色,成群的牦牛在山坡上悠闲地游荡。这里几乎不用放牧,因而也看不到牧羊人。千百年来人畜的踩踏,在山坡上留下了深深的沟堑。当我们沿着牧道攀登到海拔4100米的一处高岗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蓝天、白云、雪山、草地交织成的美丽画卷。我们冬季考察时住过的牧屋,依旧孤独地耸立在对面的山坡上。我们都放松下来,队伍此刻也拉开了距离,几个山头上都有探险队的队员。连日来超强的行军使他们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难得的好天气里,随时可待的扎营地让他们放慢脚步,开始留意起周围那曼妙的风景。我也和几个队员躺在山坡上享受着微风和阳光的沐浴,心想今天的营地应该在不远处的牧屋处。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们眼巴巴地朝着牧屋方向眺望,始终没有见到驮队。无奈,我们继续沿着牧道向上走去。和驮工会合后,依明告诉我,如果按原计划在牧屋扎营的话,我们用一天的时间是根本翻不过桑株达坂的。柯尔克孜族驮工憨厚淳朴,从来不说假话,而且只要他答应你的事情就一定努力去做,即使再困难也从不反悔。记得我们上次在冬季到达曲谷达克时,气温降到了零下40摄氏度,桑株达坂下齐腰深的积雪使我们寸步难行,但驮工们从没说过一个“不”字,最后还是我们主动放弃了翻越达坂。这次依明的话,我完全相信,而且后来的行程也证明了他促使我们做出赶路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我跟着驮队继续向上走去,同时招呼已经松懈下来的队员们尽快集中起来,抓紧赶上驮工和驴队的步伐。一路上我不停地问依明什么时间能到宿营地,他只是简单地回答我“阿孜”(维吾尔语“快了”的意思)。没想到,他这个“阿孜”让我们在山坡上一直爬到了天黑……
翻越桑株达坂
海拔上升得很快,没多久原本稀疏的牧草也看不到了。大家艰难地在布满砾石的山坡上攀爬,稀薄的空气让人透不过气来,队伍缓慢地以“之”字形向上行进。当我们转过一个山梁后,一条向西延伸的小道通向高高的山梁,山梁后面一座拔地而起的大山横亘在我们面前。毫无疑问,所谓的桑株达坂就是这座大山之巅。
当我到达海拔4300米的一个山梁下,回头再看时,走在后面的陈建峰和老张已经翻过了山梁,进入到我的视线中,但走在最后的队员田慧还不见踪影。由于只有一条明晰小道,我们虽然看不到她的人影,但也认定她不会迷路。海拔快速提升也使我感到力不从心,身上唯一的负重——相机也交给了驮工托乎提木萨。夕阳已被高山遮住,失去了阳光的山谷显得格外的寂静和寒冷,仿佛失去了生命的躯体,让人不由自主地感觉到一丝绝望。远去的驴队,像一个个小黑点在“之”字形的小道向上蠕动。“在这条喀喇昆仑之路跋涉,红尘中的一切享受都会变成精神负载,微不足道的困难都会被放大到极致。”恐怕只有此时置身于昆仑古道之中的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特林格勒这段描述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