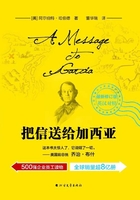一扇门关闭了,另一扇门打开了。但我们常常懊恼万分地看着那扇关闭的门,以至于看不见那扇已经为我们敞开的门。
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恒心,便能做成任何想做之事。
人生如果不是一场勇敢的冒险,便什么都不是。
目能见物却没有见解,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当一个人有高飞的冲动的时候,绝不会同意爬着走。
经历了很大的磨难,生命才能焕发明亮的光芒。因为只有懂得了苦难的意义,才能体会到幸福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展翅高飞的快乐,需要有苦难的衬托。
为我唱首歌吧
作者:[英国]艾德里安
在伦敦儿童医院这间小小的病室里,住着我的儿子艾德里安和其他7个孩子。艾德里安最小,只有4岁,最大的是12岁的弗雷迪,其次是卡罗琳、伊丽莎白、约瑟夫、赫米尔、米丽雅姆和莎丽。
这些小病人,除了10岁的伊丽莎白,全是白血病的牺牲品,他们活不了多久了。伊丽莎白天真可爱,有一双蓝色的大眼睛,一头闪闪发光的金发,孩子们都很喜欢她,同时,又对她满怀真挚的同情,这是我从孩子们的交谈中知道的。唉,不幸之中的同伴,分享着每一件东西,甚至分享每个孩子父母所带来的爱。
伊丽莎白的耳朵后面做了一次复杂的手术,再过大约一个月,听力就会完全消失,再也听不见什么声音。伊丽莎白热爱音乐,热爱歌唱。她的歌声圆润舒缓、婉转动听,透露出作为一个音乐家的超人天赋,这些使她将要变聋的前景显得更加悲惨。不过,在同伴们的面前,她从不唉声叹气,只是偶尔地、当她以为没人看见她时,沉默的泪水会渐渐地、渐渐地充满两眼,扑簌簌流下苍白的脸蛋儿。
伊丽莎白热爱音乐胜过一切。她是那么喜欢听人唱歌,就像喜欢自己演唱一样。每当我给艾德里安铺好床后,她总是示意我去儿童游戏室。经过一天的活动后,房间显得很安静,空荡荡的,她自己坐在一张宽大的椅子上,让我坐在她的旁边,紧紧拉着我的手,声音颤抖地恳求:“给我唱首歌吧!”
我怎么忍心拒绝这样的请求呢?我们面对面坐着,她能够看见我嘴唇的翕动,我尽可能准确地唱上两首歌。她呢,着迷似的听着,脸上透出专注喜悦的神情。我唱完,她就在我的额头上亲吻一下,表示感谢。
我说过,小伙伴们为伊丽莎白的境况感到忐忑不安,他们决定要做一些事情使她快活。在12岁的弗雷迪倡导下,孩子们做出了一个决定,然后带着这个决定去见他们认识的朋友希尔达·柯尔比护士。
最初,柯尔比护士听了他们的打算大吃一惊:“你们想为伊丽莎白的11岁生日举行一次音乐会?”她叫了起来,“而且只有3周时间!你们是发疯了吗?”这时候,她看见了孩子们渴望的神情,她不由自主地被感动了,她想了想,补充道:“你们真是全疯啦!不过,让我来帮助你们吧!”
柯尔比护士抓紧时间履行自己的诺言,她一下班就乘出租汽车去一所音乐学校,拜访老朋友玛丽·约瑟芬修女,她是音乐和唱诗班教师。她们见面简单地寒暄后,玛丽问:“柯尔比,你来这里有什么事情?”
“玛丽,”柯尔比说,“我问你,让一群根本没有音乐知识的孩子组成一个合唱队,并在3周后举行一次音乐会,这可能吗?”
“可能。”玛丽的回答是肯定的,“不是也许,而是可能。”
“上帝保佑您,玛丽!”柯尔比护士高兴得像孩子似的,“我知道你办得到。”
“请等一下,柯尔比,”被弄得糊里糊涂的玛丽打断她的话,“请说清楚一些,也许,我值不上这样的祝福哩。”
20分钟后,两位老朋友在音乐学校的阶梯上分手。“上帝保佑你,玛丽!”柯尔比又重复一遍,“星期三下午3点钟见。”
当伊丽莎白去接受每天的治疗时,柯尔比护士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弗雷迪和孩子们,弗雷迪询问:“她叫什么名字?是叔叔还是阿姨?她怎么会叫玛丽·约瑟芬呢?”
“弗雷迪,她是一个修女,在伦敦最好的音乐学校当教师。她准备来训练你们唱歌——一切免费。”
“太好啦!”赫尔米一声尖叫,“我们一定会唱得挺棒的。”
事情就这么决定下来。在玛丽·约瑟芬修女娴熟的指导下,孩子们每天练习唱歌,当然是在伊丽莎白接受治疗时候。只有一个大难题,怎么把9岁的约瑟夫也吸收入合唱队?显然,不能丢下他不管,可是,他动过手术,再也不能使用声带了呀!
当其他孩子全被安排好在各自唱歌的位置上时,玛丽注意到约瑟夫正神色悲哀地望着她:“约瑟夫,你过来,坐在我的身边,我弹钢琴,你翻乐谱,好吗?”
一阵近乎惊愕的沉默之后,约瑟夫的两眼炯炯发光,随即合上,喜悦的泪水夺眶而出,他迅速在纸上写下一行字:“修女阿姨,我不会识谱。”
玛丽低下头微笑地看着这个失望的小男孩儿,向他保证:“约瑟夫,不要担心,你一定能识谱的。”
真是不可思议,仅仅3周时间,玛丽修女和柯尔比护士就把6个快要死去的孩子组成了一个优秀的合唱队,尽管他们中没有一个具有出色的音乐才能,就连那个既不能唱歌也不能说话的小男孩儿也成了一个自信心十足的翻乐谱者。
同样出色的是,这个秘密保守得也十分成功。在伊丽莎白生日的那天下午,她被领进医院的小教堂里,坐在一个“宝位”上(一辆手摇车里),她的惊奇显而易见,激动使她苍白、漂亮的面庞涨得绯红,她身体前倾,一动不动,聚精会神地听着。
尽管所有的听众——伊丽莎白、10位父母和3位护士——坐在仅离舞台3米远的地方,我们仍然难以清楚地看见每个孩子的面孔,泪水已经遮住了视线,但是,我们能够毫不费力地听见他们的歌唱。在演出开始前,玛丽告诉孩子们:“你们知道,伊丽莎白的听力已是非常非常的微弱,因此,你们必须尽力大声地唱。”
音乐会获得了成功。伊丽莎白欣喜若狂,一阵浓浓的、娇媚的红晕在她苍白的脸上闪闪发光,眼里闪耀出奇异的光彩。她大声说,这是她最最快乐、最最快乐的生日!合唱队队员们十分自豪地欢呼起来,高兴得又蹦又跳;约瑟夫眉飞色舞、喜悦异常。我想,这时候,我们这些大人们流的眼泪更多。
谁都知道,患不治之症快要死去的孩子,他们忍受病痛同死神决斗的信念,他们的势不可当的勇气,使我们这些人的心都快要碎了。
这次最令人难忘、最值得纪念的音乐会,没有打印节目表,然而,我有生以来从没有听见,也不曾希望会听见,比这更动人心弦的音乐。即使到了今天,倘若我闭上眼睛,我仍然能够听见它那每一个震颤人心的音符。
如今,那6副幼稚的歌喉已经静默多年,那7名合唱队的成员正在地下安睡长眠,但是我敢保证,那个已经结婚、成了一个金发碧眼女儿的母亲的伊丽莎白,在她记忆的耳朵里,仍然能够听见那6个幼稚的声音、欢乐的声音、生命的声音、给人力量的声音,它们是她曾经听见的最后的声音。
无论生命是短暂还是漫长,生命的乐章里,总有属于自己的最强音出现。只要出现最强音,短暂的生命一样精彩。
震撼一国的农夫
翻译:胡英
每年,澳大利亚都会举行一场悉尼至墨尔本的耐力长跑,全程875千米,它被认为是世界上赛程最长、最严酷的超级马拉松。这项漫长、严酷的赛跑耗时5天,参赛者通常都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世界级选手。这些选手大多不到30岁,有“耐克”等知名运动品牌做后盾,全副武装着最昂贵的赞助训练装备和跑鞋。
1983年,耐力长跑赛场上,出现了一个名叫克里夫·杨的家伙。起初,谁也没在意他,大家都以为他是去那儿看比赛的。毕竟,克里夫·杨已经61岁了,穿着条工装裤,跑鞋外面套了双橡胶靴。
当克里夫·杨上前领取他的运动员号码时,人们这才明白原来他是来参赛的。他将跻身150名世界级选手的行列参加赛跑!这些选手压根儿没想到,还有一件令人称奇的事,克里夫唯一的教练竟是他81岁高龄的母亲耐威尔·冉。
人人都认为克里夫·杨不过是个头脑发热,想在公众面前出彩的家伙。但媒体却颇感好奇,当克里夫拿到他的“64号”号码布,走进那群身着专业、昂贵长跑行头的运动员中时,照相机镜头对准了他,记者们开始发问:
“你是谁?是做什么的?”
“我是克里夫·杨。来自一个很大的农场,在墨尔本郊外放羊。”
他们又问:“你真的要参赛吗?”
“是的,”克里夫点点头。
“有人赞助你吗?”
“没有。”
“那你不能参赛。”
“不,我可以,”克里夫·杨说,“你知道吗,我出生在一个农场,家里买不起马匹和四轮车。每次暴风雨快来的时候,我都得跑出去聚拢羊群。我们有2000头羊,2000英亩(1英亩=0004047平方千米)地。有时候我得追着羊群跑两三天。虽然费工夫,但我总能追上它们。我相信我能跑这场比赛,不过5天时间,也就多出两天而已。我追着羊群跑过3天。”
马拉松开始了,穿着套鞋的克里夫·杨被专业选手们甩在了后面。观众席上发出阵阵笑声,因为他甚至不懂得正确的跑姿。他好像不是在赛跑,而是优哉游哉,像个业余选手那样拖着碎步小跑。
现在,这位来自碧奇榉林、以种马铃薯为生的没牙农夫开始在这场艰苦卓绝的赛跑中跟世界顶尖选手展开较量。全澳大利亚通过电视直播收看比赛的人们都在心中不住祈祷,赶紧有人把这个疯老头儿从场上劝下来,因为人人都相信:不等跨越半个悉尼,他就会累得气绝身亡。
所有专业选手都很清楚,为了拼完这场耗时5天的比赛,你得跑18小时,休息6小时。可现在,老头儿克里夫·杨竟然对此一无所知!
清晨,当有关赛况的新闻播报出来时,又着实让人们吃了一惊。克里夫·杨仍在比赛,迈着碎步跑了一整夜,来到了一座名为米塔岗的城市。
显然,克里夫·杨从比赛第一天起就没有停过脚步。尽管还被远远甩在世界级选手后面,但他还是不停地跑着。他甚至还有工夫跟公路两旁观看比赛的观众挥手致意。
当他到达一个名为奥尔伯里的小镇时,有人问他剩余的比赛有什么策略。他回答要坚持跑完比赛,他做到了。
他不停地跑着。每天晚上,他只能与领先的第一团队拉近一丁点距离。到最后一晚,他超过了所有顶尖选手。到最后一天,他已经跑在了最前面。他以61岁的高龄跑完了悉尼至墨尔本的整个赛程,不仅没有一命呜呼,还捧走了冠军奖杯,以提前9小时的成绩打破了纪录,成了国家英雄!举国上下的人们立刻爱上了这个种植马铃薯的61岁农夫,因为他以5天15时4分的成绩跑完了这场长达875千米的比赛,成功地击败了世界上最优秀的长跑运动员。而他并不知道比赛当中允许睡觉。他说,自始至终想象自己是在追逐羊群,与一场即将来袭的暴风雨争抢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