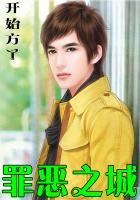二〇〇八年的元宵节,却没想到我会出现在医院里。沈柚穿着病号服右腿打着石膏躺在床上,我说:“你丫是不是疯了?”她说:“谁让他们锁着我不让我出门,网线也拔了,手机也没收。我是犯人么?”我说:“那你就从楼上往下跳么?幸好是三楼,再高点就摔死你了。”沈柚撇撇嘴不做声。我剥了块柚子给她说:“你这又是何苦呢?”
沈柚说:“我怎么了?我是同性恋怎么了?我就变态了?不要脸了?没道德了?他们怎么不说偷看我手机信息还没道德呢?”我说:“你爸也是为你好。”“为我好就可以偷看我手机信息么?为我好就把我骂得要多难堪有多难堪?我不过是跟个女生谈恋爱,难道比杀人放火还罪不可恕么?”
“那你还能怎样,父母到底还是父母,你还能不认他们么?”“不能,我知道我不能把他们怎样,所以我拿自己出气,不行么?”沈柚气鼓鼓地靠在床头,虽然事情过去几天了,但一提起来这姑娘还是登时气得小脸煞白。我说:“你这是跟谁赌气啊?要是真摔个好歹怎么办?这次算你运气好,不过是个骨折,养个把月就好了。可你想没想过,要是万一摔死摔残了呢?你以为自己还是青春叛逆期么?不过是谈个恋爱,你至于么?”
“对了,你住院后,她来看你了么?”
“来了,趁我爸妈不在,偷偷来了两次。”
我看着沈柚一脸义愤的表情竟忍不住笑出来,沈柚白了我一眼说:“你笑什么?”我说:“连来探病都要偷偷摸摸的,你这恋爱谈得也够别致。就为这摔成这样,值么?”沈柚说:“我不是为她,也不是为爱,我还没高尚到那份儿上。”我说:“那你就是存心让你父母难堪呗?”“是他们先让我难堪的。”我说:“沈柚啊,我要是你妈,趁你小就掐死你,免得日后祸害人。”
病房里的暖气很热,我脱了外套坐在床边陪沈柚打牌。说实话,认识沈柚这么久,向来知道这姑娘性格风风火火,可眼下这么一出还是把我吓着了。上午接到沈柚的电话,这姑娘告诉我在骨科医院呢。我急急忙忙赶到这儿,才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难怪进门时,沈柚的爸妈都在门口站着,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最后沈柚的爸爸拍了下我肩膀说:“小绿啊,沈柚跟你关系一直不错,你们是好朋友,就帮叔叔阿姨劝劝这孩子吧。”
可还没等我开口,沈柚就蹦豆子似的先入为主了。怎么劝?没法劝。虽然我苏小绿平时牙尖嘴利的,可此时此景确实派不上用场。摔断了骨头的沈柚明显头脑很清醒,她说她不是为了爱情,也不是为了那个女生,而是为了跟自己父母斗气。我虽极不赞同,却也能理解,倘若禁锢、责骂沈柚的人不是她父母,这姑娘至于为了跟人家赌气跳楼么?说到底,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人,无论好的坏的其实都是我们最在意的,只是眼下这问题在沈柚这里起到了反作用。
我一边抓牌一边问沈柚:“你就不打算原谅他们了么?”“至少目前不打算。”沈柚答得一本正经,而事实是我们两个人都心知肚明,原谅他们是迟早的事情,不过眼下这姑娘还在气头上罢了。
我说:“那你打算以后怎么办?还跟那女生继续交往么?”沈柚说:“当然得继续了,要么我这腿就白摔了!”我说:“我还是那句话,我要是你妈,就早掐死你了。”
许是天下父母都一样,没有哪对父母能讨孩子欢心的。眼下我妈也唠唠叨叨把我逼得无处可躲,她把小账本拿出来开始跟我算账,说这一年又里里外外搭在我身上多少钱。我说:“就当你借我的,日后我还你,还不成么?”我妈说:“我可不敢指望你还,你能让我少搭点我就烧香拜佛了。”
我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上网,我妈怕我听不见似的故意嚷得很大声。我跟良佑说:“我要被逼得离家出走了。”良佑说:“父母都这样,忍忍就好了。”我说:“怎么忍?我这一年在外面好过了么?那些钱到底哪儿去了,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么?现在家里外头都是债主,我哑巴吃黄连跟谁说去?”
良佑说:“要不再回成都来吧?”我说:“才不。你自己都悠悠荡荡入不敷出的,之前在你那儿就给你添了好多麻烦,怎好意思再让你接济我。”良佑说:“你不是说我这哥哥不合格么?我这是在努力向合格发展啊!哥哥照顾妹妹应该的,不是么?”我说:“你还是省省吧,你老人家说不定哪天就结婚了,到时候我又成多余的,我才不讨那个嫌。”
良佑说:“那我就不结婚了。”“真的假的?”“真的。”我说:“拉倒吧,你安安生生过你的日子我也算放心了。”
我在网上搜招聘信息,刚好豆豆告诉我北京有一家公司招人,网站编辑,于我来说也算对口。我便问豆豆要了那边的联系方式发了简历过去,却没想两个小时后就有了答复。那边的负责人在QQ上跟我讨论了下我对“网络编辑”这项工作的认识和见解,谈了十多分钟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彼此看轻,确切点说是网络传媒和平面传媒彼此抵触,因为我之前是做平面传媒的。
那人跟我说时下网络传媒的覆盖面广、信息量大以及方便快捷,而我心底想的却是除此之外,网络传媒的过度娱乐化、炒作、真实性和浅尝辄止。当然,这也不过是我心底驳斥的想法,我还不至于傻到搬到台面上跟人家一决高下,毕竟,在某种可能性下对方有机会成为我日后的衣食父母。
豆豆问我谈得怎么样,我说:“北京人到底是牛气啊,说话那个冲!”豆豆说:“忍着吧,我都在这儿忍一年了。天子脚下寸土寸金,连个卖票的都能对外地人大呼小叫的。”
我嘁了一声,说:“他不稀罕我,我还不稀罕他呢。说真的,我对北京有点抵触了。”豆豆问:“为什么?好多朋友都在这里,之前你在这儿时不也待得好好的么?”我说:“那时候是因为有沈安年在,可是,也是在那座城,我把沈安年丢了。”豆豆说:“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谁离开都一样,自己的日子还得照样过。你看看这半年,你都把自己弄成什么样子了?再深的感情,说散也是散了,你又何苦耿耿于怀念念不忘呢?”
为了躲避我妈的口水阵势,我便每天跑到医院去陪沈柚。其间见到过一次那个女生,足有一米七五的个儿,白衬衫,牛仔裤,扎条装饰的银色皮带,看上去确实干净帅气。我当时心里就想,难怪那个贾宝玉说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这身行头换在男生身上还真未必穿出这个效果来。
两人毫不避讳地在我面前你侬我侬。那女生剥了橘子喂到沈柚嘴里,看得我在一旁直起鸡皮疙瘩。女生走后,沈柚满面桃花地问我:“怎么样?”我说:“什么怎么样?”她说:“这个人啊。”我说:“不怎么样,注定是没结果的事情,纯属浪费表情。”沈柚说:“你非得打击我么?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我也知道没结果,可是想想日后有一天要离开她,我还是会难过,特别特别难过。”我说:“我能理解,但我也得告诉你,这一天在所难免。长痛不如短痛。趁着你们都还年轻,在这条路上陷得也不算太深,赶早回头还有退路。要不到最后就是彼此耽误。”
沈柚叹了口气说:“就我这样的,还嫁得出去么?”我说:“怎么不能嫁?人家二婚的还能嫁呢,我们怎么了?”沈柚说:“那也得嫁得如意吧,不如意还不如不嫁。”我说:“生活的本质就是委曲求全,当初我们对男人的标准就是找个金城武那样的,到最后可能就碰到个吴孟达。”沈柚说:“生活的本质是委曲求全么?我一直以为是曲线救国。”我说:“那是你太天真了。你以为我们是强者还是英雄?其实都不是!”
说话间,沈柚的妈妈捧着保温杯进来,是给沈柚煲的排骨汤,看我在客套了几句便离开了,语气神态里都带着小心翼翼。沈柚问我:“喝不喝?”我说:“我才不喝呢,病人吃的东西一点咸淡都没有。”沈柚说:“那可补啊!”我说:“亏你知道,看你妈现在在你面前都小心翼翼的,你都没给个好脸色。”
沈柚说:“咱俩谁也别说谁,你也没比我强哪儿去,你还让你妈少操心了么?就你这个倔脾气。”我说:“这不一样。我之所以不听她话一直在外面漂着,是我排斥我的家庭氛围。我爸妈在我小的时候就开始打仗,二十来年了也不见太平,我就纳闷他们岁数越来越大,哪来那个力气?我都替他们累!”沈柚说:“这倒是,这点我家比你家好多了。我爸和我妈感情一直很好,就是到这把年纪了人家还情人节互赠礼物呢,看得我这个嫉妒啊。我小时候就想,要是以后我成家了,能像我爸妈这样过一辈子就知足了,谁知道却走到眼下这步。”我叹了口气说:“苦海无涯,回头是岸吧。”沈柚一口呛到,差点把汤喷到我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