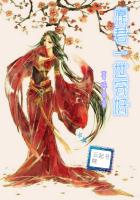22年前,汪金权离开黄冈中学回到故乡蕲春四中,从此离开了华师校友的视线。同学集会,不见老汪的身影。2005年,黄石七中校长叶甲友到黄冈出差,到黄冈中学看望汪金权。到校一问,才知同窗好友17年前就已离开,回蕲春老家了。
这个老汪,在黄冈中学教书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走呢?
叶甲友百思不解。
为了迎接母校华师的百年华诞,校友会编撰校友通讯录,汪金权名后只有“湖北蕲春”四个字,其他信息全无。这么多年了,汪金权到底去了哪儿,又是什么原因离开“黄高”?带着诸多疑问,叶甲友校长开始了后来震撼心灵的寻找。
事情的转机,缘于湖北师范学院田澜教授的一个不太经意的询问。田教授是蕲春人。这天,他到黄石七中讲学。散会后,田教授在叶校长的办公室里喝茶,稍稍休息一会,等着晚上的高三年级复习备考聚餐。田澜突然想起一个人来,便问道:“叶校长,您有没有个叫汪金权的同学啊?”叶甲友眼睛一亮,连忙说:“有啊!不过——”他又说,“我一直没有他的消息。”田澜说:“他在蕲春四中,一点都不像你们的同学,看上去很老啊!”叶甲友心里一沉,关切地问:“他过得还好吧?”“不大清楚,”田澜说,“你们应该去看看他,同学一场,应该有这样的情分吧?”叶甲友有些激动起来,说:“田老师啊,这么多年,我是一直惦记着老汪啊!我到‘黄高’看过他,可他离开了。我很想知道老汪为什么离开‘黄高’,也很想知道他现在的处境。可我没有他的电话,确实找不到啊!我哪能忘记了同学的情分呢?”
田澜笑着摆摆手,说:“叶校长,我也只是说说嘛。同窗的情分我知道,肯定忘不了!”
从田澜教授的话中,叶甲友预感汪金权处境不好,心里不是滋味。也许是为了弥补多年的缺憾,或许是为了内心的安宁,叶甲友说:“田老师,我们吃完饭,去看他吧!”田澜有些意外,但还是爽快答应了,说:“也行,去看看吧!”
因为是高三备考聚餐,叶甲友喝了不少酒。吃完饭,他也没给家里打声招呼,邀上几位同窗好友,与田澜一起出发了。此时已是晚上8点。从“黄黄高速”一路飙车过去,很快就到了蕲春县城。一问四中,才知在蕲春乡下,靠近安徽地界,还有百把里地。叶甲友顿时傻眼了。去,还是不去?从县城去四中的公路破损严重,其中还有一段很窄的乡间公路,加之不少路段正在翻修改造,天黑路远,他们心中忐忑,一点信心和勇气都没有。但渴望见到同学的心情急迫,他们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一路颠簸前行,又天黑风高,感觉路途艰险,真怕有什么不测。也许越是恐惧,越是困难找上门来。行了不足20里,车胎爆了,好在速度不快,车左右摇摆,司机吓出一身冷汗,才将车停住。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四周一片漆黑。找人修理不可能了,自己动手吧。他们摸索着用千斤顶将车子顶住,换下爆裂的轮胎,却不料因为根基不稳,千斤顶歪斜了,车子重重地压在地上。他们只好一齐动手,合力将小车抬离地面,再用千斤顶顶住,又一齐打开手机照明,才将备用胎换上,这才松了一口气,重新上路。
小心翼翼地一路开过去,直到晚上12点多,他们才到达四中所在地——张榜镇。
一路打听,车子绕上张榜去四中的公路,穿过蕲河大桥,又穿过一座座村落,一路尘土,终于来到了蜗居在大山深处的蕲春四中。
好不容易将守门的老师傅叫醒。他打着呵欠,睡眼惺忪,对这几个操着外地口音的陌生人半夜敲门有些恼火:“这么晚了,找谁啊你们?”田澜上前说:“师傅,不好意思,他们几位是您学校汪金权老师的大学校友,是专门从黄石赶过来看他的。”门卫师傅脸上出现了意外的表情:“这么黑的天,你们从黄石赶来看汪老师?”叶甲友也走上前去陪着笑脸说:“师傅,我们真是汪金权的同学,都快20年了,毕业之后就没见上面……”门卫师傅的脸色缓和下来,伸手一指,说:“呶,操场边上,那个亮着一盏灯的小平房,就是的。”
几位探视者莫不讶异。这么晚了,老汪在那儿干什么?门卫老师傅为什么那样肯定,那盏亮着灯的小平房里,一定就是老汪呢?大家进了校门,摸索着走向那排斑驳的小平房,走向那盏亮着的灯。
只见昏黄的灯光从敞开的门里溢出来,落在地上,像是冬天的霜。屋里异常安静。只有一位头发花白的长者坐在农村惯用的长条凳上,趴在双人课桌上,正埋头改着试卷。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丝毫没有察觉远道而来的校友深更半夜的造访。叶甲友走到老者身后,小心翼翼地问:“请问,您是汪金权老师?”
老者这才猛地抬起头来。见到叶甲友,他双眼一亮,脱口喊道:“叶甲友,你怎么来啦?”
叶甲友一下子愣住了。这个头发花白的人,就是汪金权?他在脑海里迅速搜索着十多年前的影子。不对呀,不像啊……他突然嗓子发哽,抖着双手,一把握住对方伸过来的手:“您,您真是汪金权……汪老师?”
汪金权高兴地说:“对啊叶甲友,你不认识我啦,我就是汪金权,就是农夫啊!”
“哎呀,老汪,真是您啊!”叶甲友百感交集,溢出泪来,“老汪,您让我好找啊!”
叶甲友后来提起这一幕,还很激动。他在《我所知道的汪金权》中写道:“老实说,如果不是他叫出我的名字,我真的不敢相认眼前的这位先前被我误认的老者,就是我们的同学汪金权的。那一刻我真的不知是激动还是辛酸,禁不住泪水溢满眼眶。说不上什么滋味,但我真切地感到一丝难受,心里默念道,老汪,你这是何苦呢?这么晚了,这么多年了,除了满头的白发,满脸的皱纹,满身的疲惫,你还收获了什么!”
因为去的人多,校友一行到镇上住宿。汪金权带路,他们从原路返回,一路小心地开着车子来到张榜镇。连找几家私人旅店,不是条件过于简陋,就是床位不够,整个小镇竟没有一家能够住宿的。汪金权说:“去檀林吧,那里的旅店,条件可能好些。”只能这样了。无奈之下,汪金权带着大家驱车前行,向蕲北进发,来到与英山毗邻的檀林镇。几经周折,才找到了一家旅社。待大家安顿下来,已是午夜1点多钟。经过一夜折腾,大家早就醒酒了,都感觉有些饿了。司机到檀林街上买回了几桶方便面,分发给了大家。叶甲友跟汪金权住在一间房里,旅社老板送来开水后,他说:“老汪,快点把面泡了,您先吃吧!”汪金权连连推辞,说:“我不饿!不饿!”叶甲友说:“一人一桶,泡了吧。”汪金权便拿起了面桶。面桶密封着。汪金权端着面桶,左右看看,不知开口的地方在哪里,扯了几下没扯开。这一幕,让叶甲友心灵震撼。自己的校友汪金权,竟然没有吃过三块多钱一桶的方便面!一股辛酸、苦楚的水骤然间涌上心头。他怕自己的泪水伤害校友的自尊,便笑着说:“老汪,还是我先来吃吧,你先去洗洗!待会儿万一电停了,就洗不了啦!”
汪金权不无尴尬地将面递给叶甲友,起身进了卫生间。叶甲友赶忙拆开面桶,倒进开水,把面泡了。待把一切准备停当,他喊道:“老汪,让我先洗,面我帮你泡好了,你先吃!”说完,叶甲友就站起身,翻找自己的洗漱用具,并开始脱去外套。衣服尚未脱完,汪金权已将面吃完,正在喝面汤。叶甲友看了,心里又涌起了辛酸苦楚的水。他心里明白,老汪一定是饿极了。
洗完澡,叶甲友怎么也吃不下他的那桶方便面。毕业后的第一次聚首,让他感慨万端,一夜无眠。
叶甲友回到学校,很长时间心绪难平。这年学校开展“党员先进性教育”,他把不是党员的汪金权接到黄石七中给全体教师作报告。第一次经历这种场合,久居深山的汪金权难免有些紧张。他的“报告”,让心高气傲又爱挑剔的城里老师不太满意。
这场报告,没有预想中的“效果”,但是叶校长却很理解。他认为一个偏远山区的高中教师,初次登上省辖市重点中学的大讲坛,又是给那么多的高中教师作报告,能“讲”就不错了。
英雄相惜,大爱略同。在黄石乃至全省教育界,叶甲友素以德艺双馨的优秀师表享誉荆楚。担任校长的他,每天要处理大量的日常行政事务,还要处置各种突发问题,但他仍然坚守在教学第一线,亲任高三毕业班语文的“把关教师”。这天晚上,他请汪金权给他班上的学生讲讲高三语文复习。
汪金权爽快地答应了。
走上讲台,面对孩子,汪金权精神一振,顿时活跃起来。他思维敏捷,旁征博引,妙语连珠,激情飞扬,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坐在教室后面的叶甲友,第一次见证了校友的精彩。他万万没有想到,在昔日同窗面前不善表达的汪金权,竟有如此演讲天才!直到这时,他才明白:汪金权的生命精彩在三尺讲台,他只属于学生,只属于纯净的心。
2007年秋,桂子山满山的桂花开了,清香四溢,一如往昔。在山乡呆了近20年的汪金权,首次接到83级中文系同窗聚会的邀请。
同学们汇聚在风光秀美的武昌桂子山上,一个个衣冠楚楚,春风满面,谈笑风生。汪金权在叶甲友的引领下走向快乐的人群。
“老汪,同学们都过来了,去见个面吧!”叶甲友说。
汪金权早已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快步走了过去。
不用细看,他一一认出了当年的同窗。
他喊着同学的名字,笑着,伸出了双手……
然而,他梦绕神牵的昔日同学,一个个竟一脸茫然。
这个头发花白,面容清瘦,穿着颜色发暗的旧西服,眼里闪着泪光的人,他是谁啊?
叶甲友紧走几步,给大家作了介绍:“他就是我们班上的农夫——汪金权啊!”
所有在场的人,无不震惊。
华师校友靳红旗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震撼。同学们都是四十多岁的同龄人,但是看到他,感觉就是五六十岁的人。穿的西装有十几年以上的历史了,头发几乎全白。如果在街上碰到,肯定不认识。”
一双双手,细腻的,白嫩的,纷纷伸过来,紧紧握住汪金权的手。
“老汪,真的……是你啊?”
“你是……汪金权?”
“金权?你这是……”
大家热烈拥抱,满是笑容的脸上早已泪水涟涟。
“你过得很苦吗?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不与我们联系?”
20年的分隔,隔不断的同窗友情。然而,友情却不能弥合汪金权与同学之间的巨大落差。
桂子山上,似乎是两代人的相遇。
惊叹和意外,好像是“白领”碰上了“草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