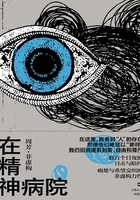王小妮
更高的境界
一个人不写诗照样活得好,那是活着的一个更高境界。
人间不可及达之地
1995年夏秋,我从加格达齐出发向西,只是向鄂伦春的地域走了50公里左右,就原路返回了。暴雨过去的天空上,有不止一道彩虹,白马独自立着,尾巴扫荡,狭长的头低伏在亮晶晶的浅河里,它在喝水。这种地方,人只能路过,谁也不可能踏遍它占有它,它不是人间可以享用的。我知道,我不配。
额尔古纳的早上
我站在额尔古纳小城的街心上。从来没站在过这么早的早上。如果有一个人出现,有推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的,有提一只盛大葱的篮子的,有牵着去上学的孩子的,有推开柴门的探出头的,出现任何一个活动物体都不算惊奇。
没有移动,只有几栋楼房,几块早就褪色的广告牌,宽阔笔直满是微光的大路。这是我经历的最荒诞的早上,除了我,什么都是凝固的。风不大却吹得骨头凉。好像不知道该做什么了,好像需要出现点什么来给人世间定位。
在内蒙古的天空下面
不可能不在云彩下面走,谁也躲不掉当头的那些白色爆炸物,云彩太茂密了太盛大了,大团大团,天空变得比实际的大了几倍,我们被压在一片最小的平面上,哈哈,蚂蚁的感受。
呼伦贝尔告诉我的三句话:
日落是涉及到全地平线的,并不只是西天,整个天空都在改变中。在新巴尔虎左旗的一栋三楼上,能看到日落之时,整个大地的应合变幻。
如果让我留在这草原上,我也许不会再写诗了,写诗变得不是必须的了。这想法出现在从根河到额尔古纳的半路上,车临时停了,同车的人都下去,沿着一片油绿的坡地去一户养蜂人家里买蜂蜜。
我是真满族,虽然在之前我从来没有认真地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一定就是来自于这块地方,巨大的降服感和认同感在潜意识中出现,总是不能消磨掉。
我没有心理准备,这些感觉的出现够奇怪的,离开呼伦贝尔以后,它们反而更鲜明强烈了。
各有各的安身之地
我观察蒙古人,他们坐着的时候安静坦然纹丝不动,站着的时候结实稳当,走路的时候坚定舒缓。过去我认识的那些城市蒙古人中好像没有这些特点了。蒙古人不能离开草原。那么汉人呢,汉人的安身之地在哪?
海岛特有的黄昏
一连十几天,我都放下手里的事情,去注意海岛上的黄昏,它和任何其他地方的黄昏都不同。空气本身就有点粘稠发沉,有点迟滞,有点漫不经心,闲散淡漠。5点半过后,行人和车辆都带有了某种缓慢忧伤的节奏,每个人都好像可走可停,半滞留着。所有物体都微微带点儿金灰色,不是金钱的金。一片向西的高层楼房的玻璃忽然全是耀眼的光,好像那里挂着另一个太阳,形状不定的,紧贴在一大片光洁的平面上,那块不够稳定的金色正在整体下滑,水一样。
这就是海岛和大陆的不同吗?很多年都没注意过落日了。深圳的楼房根本不让人看到那么远,天空被挤迫得很狭小,常常忘记头顶上还有个叫天空的盖子,还有个自升自落的太阳。
要谢谢海岛和这小块土地上的一切。
人是应当住在乡村的
这个道理也许在500年前尽人皆知。是人自己把乡村搞得糟糕透顶,然后,反过来歧视乡村里的一切。
如果有真理,真理和谬误就是这么明白地摆在面前,位置却是颠倒的。因此,除了瞬间的幸福感一带而过,人没有什么幸福生活。
(选自2007年3-4月号《诗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