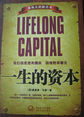以后的多少年里,父亲多次分别给远在兰州的二舅和贵阳的大舅写信,检讨自己,劝说他们兄弟俩能和好如初。一九六八年,在兰州铁路局工作的二舅到武汉,父亲提议他带着永平表哥和二姐明苹,去了贵阳一趟。这是兄弟俩二十多年的第一次交往!
(三)
父亲去世后的日子,母亲坚强地承担着我们的生活和教育的全部责任。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这样有双休日,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要抓革命、促生产,母亲的工厂是三班倒,早班、中班、夜班,每周轮着上。如果是上早班,她总是在四点多就起床,为我们做好过早的(武汉话:早点),还将中午的饭做好。怕我们睡过了,把闹钟给我们上到七点,有时还会留一张纸条:“小玲,过早的油盐炒饭在菜锅里,你起来再热一下,中午的饭包着在(冬天,怕我们放学回来饭冷了,母亲用棉被层层包着装饭的锅子),你放学回来只热菜。记得把门锁好!”
别人都怕上夜班,怕连续一个星期的熬夜,影响身体。可母亲喜欢上夜班,她说这样可以把家里的事都做完,等我们睡了再去上班。中班要到晚上近十一点才回家,记得小时候睡在床上,深夜听得见母亲回来的脚步声。上早班的晚上,我们在灯下做作业,母亲就在灯下做我们的棉衣、棉鞋,她有一双能干的巧手,全家人一年四季的衣服和棉鞋、布鞋都是她做,大孩子的衣服改给小一点的孩子。每个月四十二元的工资,她要仔细地盘算,安排全家人的一日三餐、我们上学的学费等等一切开销,一分钱恨不得当成两分钱花。她还时常一边做着事,一边对我说:“小玲,你帮我记个账。”有时候她自己也记。她没有上过一天的学,在父亲的指导下,她可以写一点简单的东西,可以看报,读两个舅舅写来的信。母亲勤俭、勤劳,能省的钱,她绝不乱花。一发工资,她就会将家里一个月需要的柴米油盐还有煤买回来。
记忆中,每个月去买煤,好像是她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母亲先到鄱阳街排队买煤票,再到洞庭街的煤场去排队拖煤,先交押金借装蜂窝煤的木箱和推车,再从煤场将煤拖回家,一个个把煤从车上放到厨房的灶台下,回头将车子和木箱还回煤场。别人家都是男人做这些事情,可我们只有母亲带着我们一起来做。每次还完运煤的车,回到家,她总是说:“这个月够烧的了!”可是,下个月的日子很快又会来到。想想母亲,是如何用手指在计算着一天天的期盼我们长大的艰难的日子啊!
家里的电灯坏了,她就是电工,椅子上加椅子,她站在椅子上换保险、换灯管。煤炉子不好用了,她到江边的去弄来泥巴,自己在那里打炉子、糊灶台。甚至,家里的小板凳,都是她找来小木板钉成的。
父亲去世后,母亲为了节省房租,也考虑到我们年龄小,爷爷和姑太都是在那个大套的房子里去世,晚上我们害怕。她找到相关的人,要求多次将大套房子换成了对面的一个小套。这间小套房子后面有个院子,她曾经在这院子里种下了扁豆等蔬菜,还种了些花。就是在这个院子里的一个角落里,为了节省煤,她自己做了个烧柴火的小灶,捡柴做饭、烧水。有几次她都高兴地对我们说:“几省(武汉话:真的很)煤哟,有好几天没有生炉子了。”有几次,妹妹不愿意用那个炒菜的锅烧的水洗澡,说有油腻。可能是烧灶的次数多了,灶烟薰得母亲眼泪直流。后来,母亲的眼睛得了白内障,估计就是与这烧灶有关。
忘不了,我和母亲度过的那一个个深夜。为了贴补家用,母亲为黄叔叔楚剧团里加工做一个幕布。这种挣钱的机会是很少有的。又宽又大又厚的幕布,需要母亲加班赶出来。我帮母亲在缝纫机旁扯平那幕布,那台旧缝纫机浑身都响,母亲吃力地、快速地踩着它。快深夜两点了,终于做完了,母亲高兴地说:“我们今晚可以挣六元钱啊!可以买好几天的菜呢!烧水下面宵夜!我们营养一下啊,打鸡蛋里面!”吃着母亲下的面条,我眼里满是泪:我碗里有鸡蛋,母亲没有!那个时候物资紧缺,生活用品许多都要凭票按人头供应。母亲每个月都要算计着用那些肉票、鸡蛋票。
两个姐姐,特别是大姐,一直是母亲的经济和精神支柱。因为有姐姐,也使得那些没有父亲的日子,我们和母亲有了许多的温暖。
还是在一九五八年,大姐明燕,见家里弟妹多,为减轻父母的生活负担,我才一岁时,大姐十四岁未满,便瞒着父母,虚报年龄,改了户口,报名参加了工作。从此,她每月的工资都贴补家用。一九七0年父亲去世后,大姐更是拿出工资的四分之一,帮着母亲养育未成年的弟妹。我计算了一下,大姐从十四岁参加工作,直到四十多岁,整整三十年的时间,娘家就如同一个需要她尽心弥补的无底洞,每月工资一发,她便从武昌过江,送到汉口的娘家。三十年,大姐送钱回家,送得心甘情愿,送得无怨无悔。其实,大姐自己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把对孩子的爱无私地分给了娘家的我们几个弟妹。星期五,是大姐工厂的休息日。几十年,几乎是雷打不动,不论刮风下雨,还是严冬酷暑,大姐都会回来,给失去父亲的我们带来欢乐。大姐在父亲去世后的那么多年里,曾是母亲的精神支柱,是我们兄弟姐妹的依靠!大姐使母亲和我们,对生活有了期盼:对星期五的期盼,对欢乐的期盼,对大姐四分之一工资的期盼!
二姐明苹,从农村招工抽到襄樊铁路分局工作,她一参加工作,像大姐一样,也帮着母亲分担养育我们的责任,从工资里拿钱给母亲,也是每月从不间断。
两个姐姐每次回来,不仅仅是送钱回来,还带回来了外面的精彩世界。两个姐姐,其实是在帮着母亲承担了部分父亲的职责,和母亲一道,关心我们的学习和成长。母亲也总是算计着,把肉票和鸡蛋票在姐姐们回来时再买,常常在天不亮就叫我:“小玲,明天你大姐要回了,快起来去菜场排队!”
(四)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这十年里,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巨大的动荡,我们的家庭也经历了磨难,母亲在这十年里,承受着孤独与艰难。每天晚上,劳累了一天的母亲,总是靠在大床上,抽着劣质的圆球牌香烟,吸着烟吐着雾。那烟雾,仿佛能带走她的一些烦闷,记得那烟是一角九分钱一包。孤独和苦闷她自己承受,却把温暖和安全感、依赖和温暖给了我们。记忆里,母亲总是乐观的、豁达的、助人的。邻居们有时找她帮忙做衣服,她总是二话不说就给人家抽时间做。很少看见母亲在我们面前哭泣流泪,母亲给我们的印象是无所不能,是一个什么都可以依赖的母亲。
记得母亲的一个叫赵逸梅的同事,住得离我家不远,常到我家来玩。后来她患了神经病,她的丈夫到我家来找母亲拿主意,一个男人在我家竟哭泣起来。母亲顾不上给我们做饭,帮着她的丈夫将她送到医院。当时小小年纪的我在场,心里实在瞧不起那个男人。母亲厂里的同事中,有一个女工是日本人,她文静、胆小,在那个年代很受歧视。母亲经常将她带回家来玩,开导她,在我们家吃饭。最后她还来我们家给母亲告别,她回日本了。
母亲乐于助人,记得那些年有好几个人都在我们家住过。二姐的同学董玲,父母下放干校,她从农村回来,有时就住在我家。还有小红姐和她的母亲,也是一回到武汉就住在我家里。小红姐的妈妈邱岳珍是与母亲小时在衡阳一起长大的姐妹,她的丈夫是当年留学德国的武汉一医院的知名眼科医生,岳珍姨妈是一医院的药技师,本来是很幸福的一个家庭。可她丈夫因个人问题,判了十年刑。文革中,岳珍姨妈被单位调到二汽医院工作。母亲曾热心地陪着姨妈,去偏远的汉阳铁铺劳教所看望夏树国姨爹,并给岳珍姨妈做工作,让她原谅她的丈夫。后来,她终于接受了刑满后的他,在二汽医院一同工作了好多年。母亲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做好事,有好事在。”她做好事,从来不求别人的报答。
生活的困难,使得我们经常有些事情很难向母亲开口。高中毕业前的一九七五年三月,我们学校要组织一个农技班,去南湖的农科院农场学习劳动半年,目的是好为下放农村作好准备。在学校是班干部的我,积极报了名,很快被批准了。可是一道难题摆在我的面前:每月要交十三元生活费。我如何向母亲开口。在家里吃饭无非是多一双筷子,要从家里拿走十三元钱,当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晚上睡在那张小床上,想到这个事,我为难的哭泣着,又不敢哭出声来,怕母亲听见。但哽咽的声音还是被母亲听见了,她在黑夜里问我:“小玲,你怎么了?”我骗她说:“我嗓子不舒服。”母亲立刻从床上起来,找出止咳糖浆的药要我喝,说是要赶快挡住,要不然感冒会越来越严重。我只好喝下母亲递到床前的药,眼泪更加无声地流着。第二天,我跑去找住得不远的与我们有点沾亲的春香娘娘,让她给母亲说这个事。春香娘娘带着我回家,母亲竟同意了我的要求。那十三元钱,我拿着心里很不是滋味,有对母亲的感激、还有愧疚。后来与我同去农场的杨小英、王展等好同学,说起这事,她们竟说:“呵,当时我们觉得好便宜好,一个月生活费只要十三元。”她们都是干部子弟,条件好,哪里知道我这十三元从家里拿出来,是多么不容易啊!
一九七五年六月,我高中即将毕业。当年五十岁的母亲,可以从工厂退休,让一个子女顶她的职,去她的工厂上班。记得是在一个晚饭后的傍晚,母亲把我叫到她的跟前,把我当一个大人一样与我谈话、与我商量。她告诉我,她很为难,因为我和哥哥都可以去顶她的职。哥哥头一年下放去了农村,经常写信回家,抱怨在农村的艰难。面对我和哥哥,她不知应该让谁来顶这个职。哥哥回武汉来,我就必须下去。其实当时母亲并没有为难我,她只是很冷静地征求我的意见。有时候外面有的人会说:明家是个独儿子,母亲重男轻女。其实我知道,母亲对我们姊妹五个都是一样的疼爱,只是她总是信任能力强一点的我和大姐。十八岁的我,经历了从父亲去世后与母亲共同度过的艰苦岁月,我很理解母亲此时的心情。我对母亲表了态:“让华华哥回来顶你的职吧!我去农村!”母亲听后,为我的懂事泪如泉涌,他哽咽着对我说:“你快给你哥写封信吧!告诉他这个事情。”然后在一旁一边流泪,一边看着我写信。
父亲去世后,我就是母亲的小“跟班”,我是在她不断的鼓励下变得懂事和有能力的。我很小时就会做饭,现在能做一手好菜也是那时跟母亲学的。母亲还无意中培养了我文字写作的能力,父亲走后,我就成了她的小秘书,常常是她一边做着家务,一边说:“小玲,来帮我记下今天买菜的帐”、“小玲呵,来给你舅舅写封信,你心里是如何想的就如何写,把我们家最近的情况给舅舅说下,让他放心。”我写完后就会念给母亲听,母亲总是会表扬我:嗯不错,写得蛮好!
1975年9月25日我就要出发下到农村去了,头天晚上,想到第二天就要离开家,离开母亲,下放到蒲圻农村去,我心里难受得久久不能入睡。第二天早上七点,从江边母亲单位乘大卡车出发,许多家长来送行,围在即将出发的卡车下面哭,女知青们在车上哭。面对来送我的母亲、二姐和小妹,还有我高中时的喻老师和好同学,我没有哭泣,也不敢哭泣,甚至脸上一直带着笑容。我是怕母亲心里难受,怕她觉得自己的决定是错的。在随同母亲单位下放的那一批知青中,我无疑是最优秀的。在母亲的工厂,我曾经给母亲带来骄傲,给母亲长了脸。下放前,知青办的李主任让我代表全体知青在欢送的大会上发言。下放第二年,我被大队学校选派去当民办教师。因为在农村优秀的表现,母亲厂里还出路费请我特意从农村回到武汉,给在我们后一届的下放的知青作报告。在台上,我远远地看到母亲坐在最后一排,她的脸上带着幸福和骄傲的笑容因为家里生活条件本来就差,到了农村我反而不觉得农村有多苦,不像其他知青觉得日子有多么难过。在农村三年多,我务农了半年,教了三年书,从大队小学教到初中,又因为工作成绩优秀,调到公社的镇上中学教书。三年多的农村生活,对我的人生有很大的帮助。后来我考取技校回武汉,才确实感到母亲的决定是对的,如果不是让哥哥顶职回城,他是很难考上学校提前回城的。
苦难,对一个人来说其实是财富。母亲让我们都十分懂得对生活报以感恩的心情。母亲对我们的爱,使我们姐妹都知道如何自己处理困境,对母亲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的。
现在我们姊妹五人,大姐已是六十三了,妹妹也有四十六了,每当我们聚在一起,就会当到母亲,谈到母亲带领我们走过的那些难忘的岁月。我们怀念母亲,想念父亲,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其实真正的幸福是一种心态,是一种对生活的满足感,是亲人间无微不至的关怀。现在大姐、二姐和我每家一台钢琴,聚在一起时,就会每人表演一曲,她们俩人还经常把好听的曲子复印给我。大姐过年送给我们的是健康保健的书。
母亲没有给我们留下物质上的东西,可她给我们的乐观面对生活的精神是溶入血液的,生生不息!
(2007年08月07日)
7.3想念我的父亲
——写在父亲节
爸爸,今天是父亲节,我的儿子、我儿子的父亲、我们一家三口,在邦可西餐厅,为儿子的父亲过节。
可此刻,我更加想念您、思念您——爸爸,我亲爱的父亲!虽然您伴随我的人生,只走过短短的十二年;然而是您,给了我宝贵的生命,我身体里流淌着您的血液、我的容貌有您的元素、我的灵魂更有您的精神长存!
爸爸,从1970年1月19日那个寒冷的冬夜开始,您已离开我们整整三十九年了!三十九年了,三十九个春夏秋冬,三十九个漫长且匆匆流逝的时光。而您的形象,在我心中永远都没有年老过,永远停留在三十九年前,您四十九岁时、我还是十二岁童年的那个时刻。
三十九年里,无数次的梦中,我分明是见到了您!每一次的梦见您的场景都记忆犹新;您提着那个黑色的工作包回来了,我委屈地扑到您的怀里,娇嗔地责怪您,为什么离开我们那么久?!曾经无数次地在想:如果您不是这般久久地远离我而去,我生命的过程,将全部重新改写!每一程路都有您的呵护、指导,我的人生之路哪有这么多的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