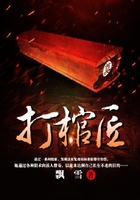对于我来说,这一番理论实在是太重要了,我马上把自己关于战争的思绪抛到了脑后。
“要加多少凝乳酵素?”
“只要一点点,例如,五公升。不要太多了。如果你加得太多的话,奶酪就会变得像橡胶——到处都是洞,味道还会很苦。”
“然后呢?”我问她,害怕她已经说完了。
“然后你拿盖子把羊奶盖上,到第二天早上,它就凝结了。假如是早上挤的羊奶,那么就是到晚餐的时间凝结。接下来就是,拿勺子把凝结的羊奶舀进模型里,等着排出多余的水分,这就是那些小洞的用处。第二天,给奶酪加盐,把它们翻个面,再排一天的水分。这就是整个过程了。”
“这就没了?那陈化呢?难道奶酪不会特别的软吗?”
“当然是软的,因为那是新鲜的奶酪。每天你留着不吃,它就会变老一点。奶酪是一种活的生物,你知道的,就好像葡萄酒。它会变,就像我们一样,越变越老。如果你想要一块陈化奶酪,那么你就保留得久点吧。”
这个和美国农业部小册子上说的并不完全一样。
“但是假如你的奶酪做得好吃的话,就没有陈化这一说了。人们会马上买下所有的奶酪。现在很难找到新鲜的奶酪了,我们都很怀念啊,你说是不是,玛丽.皮埃尔?”她转向了她的女儿,玛丽.皮埃尔赞同地点了点头。
“那么,就这样了。”瑞丽尔夫人把奶酪模型放回了壁橱。
我很感谢她,然后我告诉拉霍斯特夫人如果她还想留下的话,我可以一个人回去。她留了下来,于是我同厨房里的母女俩告别了。
我离开的时候,那条狗醒来了,朝我汪汪地叫着。它挥舞着爪子,使劲扯着链子。我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它的领地,慢慢地走到了房前,又拐上了来时的路。我的眼睛尽可能地扫视着家庭菜园,又要避免令人看上去像好管闲事的。往前走的时候,我的手深深地插在我的口袋里。
我在法国里昂的一家奶酪供应商的仓库里,上了我的第二堂也是最后一堂课。我们在一份有关山羊及其产品(主要是奶酪)的专业杂志《山羊》上读到了那家供应商的广告。
在那里,我们买了一个有着巨型漏斗的五十升盛奶容器,一个被隔成三个部分的过滤器和一些纸质过滤材料,还买了一百五十个塑料奶酪模型和六个用于排干水分的不锈钢架子。
“你还会需要这些的。”在一旁等着我们的年轻人说。他指给我们看一堆看上去十分结实的白色塑料盆和木盆。
“你的奶酪房防尘、防虫吗?”我们还没有奶酪房,我们也很肯定我们很难做到完全防尘。
“不,”我说,“不完全。”
“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建议你买下这些带盖的盆,很方便的。”
我看着他,笑了笑。
“你看,挤完奶以后,你要通过过滤器,把水桶里的羊奶倒到盛奶的容器里,对吧?”
“当然,是这样的。”瑞丽尔夫人没有说明这一部分。
“所以,我建议你把温热的羊奶倒到塑料盆里,再加点凝乳酵素,盖上盖子,把塑料盆放在温暖的地方,十二个小时就会凝结。盖子能防尘和防虫。”
他继续解释说,凝结后的羊奶必须直接拿勺子从盆里舀到模型里,那些模型都是放在一张起皱的塑料纸上——如果我们需要的话,他也能提供。乳胶能够促使多余的水分排到桶里或盆里。接着,他还说起了翻面和朝奶酪里加盐,这些和瑞丽尔夫人告诉我的没有什么不同。
我们买了两个带盖的盆和一升凝乳酵素。即使每公升羊奶里我们有可能只会添加一点点,我们还是想保证,在即将到来的产奶季节里有充足的库存。
我们的农舍并不完全属于我们自己,而是和一个朋友共同买下的。我们经常会去欧洲的各个城市转转,于是我们中的某个便能留下来看家,保证奶酪生意的正常运行,这样我们就能共同分享一份平静的田园生活。然而,从很早开始,我和唐纳德就明显地感觉到,这种共同生活并不适合我们,再加上那个朋友又有了新的爱人。于是我们开始考虑,带上羊群寻找另一个能安家的地方,我们寻找的目标必须带羊舍,还要有可供我们购买的几块土地。在往返里昂的路上,我们商量了这个事,最后打算回去后,告诉我们的同屋人乔安妮和盖尔德这一决定。他们买下了属于我们的那部分房屋产权,而我们则买下了属于他们那部分的羊群所有权。
虽然分开了,但我们仍然是很亲密的朋友,后来我们两家带着自己的孩子,在普罗旺斯共同度过了许许多多个夏天。我和乔安妮的友谊跨越了四十年,经历了两任丈夫,三个孩子、六个继子女和一生中所有的回忆。
在我们穿过山谷到达新家后,离山羊生产的日子只有几周了,于是唐纳德和我把精力都放在了放养羊群上。新家还是租的,我们打算过一段时间,再考虑置办新家的问题。
我们的新家破旧不堪,简直可以称做是废墟,不过房顶还算好,租金也比较便宜。房子是西南朝向的,土黄色的石块几乎整天都沐浴在日光中,我非常喜欢这一点。房子旁边有一口井,屋内有一个壁炉,但是没有通电。我们装上了新的窗户、一个水槽和一个能放两口丙烷炉的厨房台,还装上了一面玻璃门,这样就可以让光线射进楼下唯一的一间房——那里被当做起居室和厨房。
唐纳德从一个已经七零八落的老式葡萄酒榨汁机上,弄下了几块橡木,做了一张床。我们把床放在了楼上的大卧室里,它旁边小一点的房间给了埃塞尔。穿过大卧室的一扇门就可以直接进入它后面的阁楼,这让我们能很方便地在干燥的环境里,储存山羊要吃的牧草。楼下,我们在厨房里,同样也安了扇门通向羊舍,这样我们也就能更方便地管理羊群了。我在楼梯下的空间里,搭起了一个小小的、有纱门的奶酪房,房间的大小刚好足够放下排水槽和养护架,还包括一个接乳清的水桶。
在宽敞的羊舍边上,我们为羊群搭了个羊圈,材料用的是从房子后的森林里砍下的结实的橡木枝和松树枝,这样羊群就能自由地出入羊舍,又不会到处乱跑了,唐纳德还做了个槽装牧草。就这样,在第一批小羊即将诞生的时候,我们已经尽可能地做好了准备。
安顿下来后,我们邀请新的朋友们来共享晚餐。其中有当地的老师丹尼斯.芬和他的妻子乔琪特。他们都是艺术家,在布置新家的过程中,他们帮我们做了一些活儿。还有马克和妮娜.哈格,他们是一对美国夫妇,来这个小村庄过冬,他们也帮了我们不少忙。
我用野玫瑰为壁炉上烤着的猪肋骨肉调味,这之前,我从来没有尝试过在壁炉上烹调美食,现在就算我想到了这个主意,我的烤肉技术还是不行。半边肋骨肉被烤焦了,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在烛光下,我很难辨认出肉烤熟的程度。我还在祖母的荷兰铸铁炉上,烹调填满了食材的美洲南瓜,结果却煮过头了,本来就是过季的南瓜,现在变得更加软绵绵,又没有水分。幸运的是,我从面包房里,买来了坚果馅儿饼作为甜点,再加上有葡萄酒的陪伴,餐桌上谈话的气氛十分愉悦。这之后的好几个月,我们都没有邀请过客人共进晚餐,不是因为不想,而是因为我们实在是太忙了。
白天,我们刚刚好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一些基本需求——食物、取暖、衣服和清洁,这意味着首先要做的是拖运水和烧开水,生起要燃烧一天的火和照顾羊群,挤奶和制作乳酪。然而,直到蕾妮特用了十个多小时分娩时,我才意识到我们的生活和我们厨房后的羊舍里的动物联系得有多么紧密。
埃塞尔拉开了整个事件的序幕。
“快来!我觉得蕾妮特不对劲!快!”
蕾妮特躺在她身边,呻吟着,两只眼睛向后翻着。唐纳德出去了一小会儿,我们把他叫了回来。
他跪在蕾妮特身边,轻轻地压了压它的肚子,抚摸着它的肋腹。
“它越来越虚弱了,如果我们不采取什么措施的话,恐怕我们就要失去它了。我感觉不到胎动。我要把手伸进去试试。也许先出来的是臀部,我现在要试着让小羊翻个身。”
我烧了一壶水,唐纳德洗干净手后,擦了点凡士林。当唐纳德尝试着把手伸进去时,埃塞尔就站在我们身边。
“我能够摸到它——我觉得我一定是碰到了它的背部。它绝不能那样生出来。我要试着让它转个方向。”这时的蕾妮特在虚弱地咩咩叫着,然而它正看着唐纳德,似乎知道他在尝试帮助它。
“我做不到。我的手太大了。你试试。”
“我的上帝啊,我不行!我做不到。”
“乔治安妮,你必须试试。如果我们不帮她把小羊生出来的话,它会死掉的。我想小羊已经死了。我们必须帮它生出来。去,把手洗干净。”
我试了,但是我的手还是太大了。唐纳德转向了埃塞尔。
“埃塞尔,你觉得你能像你妈妈和我一样,把你的手伸进去,帮助蕾妮特把小羊生出来吗?”
“可以的。”埃塞尔回答说,声音很有力。她站在那儿,双臂在身体两侧直直地垂着,看上去神情很坚定。她身上穿着我为她做的红白格子花纹的连裤衫童装,脚上穿着她厌恶的棕色系带鞋,披着的头发贴着她的脸庞。
“等一下,”我说,“让我给你扎好头发。”她不喜欢把头发扎到脑后,但是她让我扎起了马尾辫,用发卡把刘海儿往后夹好了。
“这种时候可不能让头发挡住眼睛。”我说。
唐纳德有点不耐烦了,说:“乔治安妮,给她把手洗了,然后你们两个都回来。”
暴风雨即将到来,天空正一点点变得阴暗,慢慢吞噬了本来就在减弱的日光。远处,第一声雷隆隆地轰鸣着。羊群焦躁不安地想要我们为它们喂食和挤奶。回来的时候,我带来了一盏露营提灯,然后把它挂在了羊舍一根横梁的钩子上。
“你准备好了吗?”唐纳德问埃塞尔。
埃塞尔点了点头。唐纳德给她手上擦了凡士林,然后引导她非常温柔地把手伸进去,看看她能不能碰到某种硬的东西,像一条腿或者羊的头。
“我想我摸到了腿。”她说,她的手和前臂伸进去很深,她的头紧紧地贴着蕾妮特的肋腹,“等一下,是两条腿。我觉得我摸到了蹄子。”
“很好,埃塞尔,现在你要非常温柔地拉拢蹄子,让它们朝着你的方向。如果我们能并拢蹄子的话,我觉得我们就能把小羊拉出来了。”
他一直在摩擦蕾妮特浮肿的腹部,轻轻地安慰着它。我也照做了。它一点也没有反抗,只是躺在那儿。
“我抓住了两个蹄子!”埃塞尔大叫着,突然往后跌到了,手里抓着两根断掉的前腿。
“噢,该死的。孩子已经死了,身体也开始分裂了。”唐纳德说。
埃塞尔和我都哭了,我们坐在羊舍地板上堆积的一堆稻草中,她的双臂紧紧地抱着我的腰,头埋进了我的膝盖中,我们哭泣着,为刚刚受的惊吓,也为蕾妮特失去的孩子。我从她的头发上取下了发卡和橡皮绳,然后我抱紧了她,安慰着她。
我从没有预料到,这种生与死之间的一线之隔,也没有做好准备去面对它。然而唐纳德却不同,他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学习了五年,一心想成为一名兽医。他以前见到过这种事情,也明白这同样也是饲养动物的一部分。我在理智上明白这些,却不能从情感上接受这一事实。
那个晚上我们睡得很晚。唐纳德最后终于把死去的小羊弄了出来,蕾妮特也排出了胎盘。他给了它一些抗生素,并且确保它会感到舒服点,而我和埃塞尔给羊群喂食紫花苜蓿和大麦,还为它们喂了水。
第二天早上,第一个出现在我们脑海里的就是蕾妮特。我们发现它颤抖地站立着,它的乳房因为奶水而变得硬硬的。很幸运的是,它没有染上乳腺炎,因此我们还可以为它挤奶,减轻点它的痛苦。它的身体一直在恢复中,最后,它成了我们羊群中最能产奶的山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