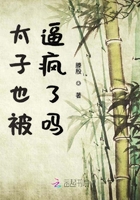午饭刚过,就听见屋外传来“阉鸡呀,阉鸡呀”的喊叫声。我从窗外望去,骄阳下一位年近四十的阉鸡人,肩扛着阉鸡捞子,手拿阉鸡夹子,两三步一吆喝。望着他远去的背景,我便想起十多年前那个暑假学阉鸡的往事来。
那还是入师范的第一年,学生生活十分清苦,父母早逝,又无亲朋接济,经济更显得拮据。暑假我回到了故乡,那小山村里还有一位本家四叔。
故乡虽说山青水秀,大家都忙于抢收抢插,我整天与小孩为伍总觉无味,在四叔家小住几天后准备进城打零工赚点零用钱。
四叔便要我学阉鸡。我则认为阉鸡不是养家手艺,况且与那“偷鸡摸狗”还有些说不清楚的联想。君子固穷,也要不失身份。
“现在‘双抢’,生产队管得紧,周围没人做这种事。学吧,肯定赚钱。”四叔那眉飞色舞,津津乐道的样子,好像有大把的票子可抓一样。
四叔是快语快人,放下碗筷,便要堂弟春宝出去抓鸡。鸡抓来,共四只小公鸡,四叔接过一只说:“我先阉一只,你看好。”开口后便是指指点点:“这是血仓,这是血管,都是动不得的。两个卵子必须先取底下一个。”
看着四叔操作,也觉简单,我深信自己会做,就是不愿学,四叔硬是将我按在矮凳上坐下。我仿着四叔的操作程序,先绑双脚,后卡脖子、翅膀,再拿起生锈的小刀。随着鸡的呼吸,鸡胸一起一伏,我想到这么大的手术,用生锈的刀,没有消毒,没有麻醉,一定很疼痛的,我不忍下手。
“割呀,你割呀。”四叔在一旁催促。
我闭眼一刀,因用力猛,血便从刀口溢出。鸡的双脚在颤抖,眼睛紧闭,张嘴露出一片尖舌,我的心一阵惊慌。松绑后的小鸡一摆一摇蹒跚走出门外,那小生命一定危在旦夕。
四叔说:“换只再来,下手轻点。”
我十分不情愿地将第二只鸡绑上夹子,开口后划破一层薄膜,小鸡的心脏、肠子、睾丸都一目了然。四叔在一旁不停地讲,可我总是缩手缩脚的,小铜瓢和马尾毛特制的专用工具总不听使唤。往往看着容易的事情,自己做就难,人都这样眼高手低。
近两个小时学艺,最终也只能取出一粒睾丸。可四叔还催促我外出:“去吧,要想手艺学得精,跑遍满天星。”
真是拗不过四叔。第三天我起了大早,扛着阉鸡捞子,手拿阉鸡夹子偷偷地溜出了村。天上繁星密布,月影扶疏,夏日晨风清爽。我想趁天亮前尽力赶路,这副行头我怕见人,特别怕见熟人,巴望走得远远的,到一片陌生的地方去。
鱼肚白的夜空,几朵云霞飘过,渐渐露出一点亮光,慢慢上升,一会儿从东边群山之中滚出一个大火轮来,把东半天照得火红。初升的太阳给人带来一种向上的感情。
离村约三十里地,我便抄小路进入村庄。走进村口,脚步轻轻的,又不敢叫喊,像做了很不光彩的事一样,怕人看见,怕人听见。好在成人都下地,只有几家门前的竹床上坐着几个睡眼惺松的小孩。
一种惶惶不安的心理支配我抄近路逃离村庄,路过一个水塘,偏被一位在水塘边洗衣的老太太“抓”住。“喂,阉鸡的师傅哎,不要走了。”她丢下手中的棒锤赶来:“一窝鸡都大了,一天到晚赶骚,连蹲在窝里生蛋的老母鸡也被赶得满天飞,真是奈它不何。多时要阉的,总无师傅来。”她高高兴兴地来到我面前,但又见我面嫩,便投来一股淡淡不信任的目光。
老太太梳洗得很洁净,头发在脑后盘个髻,用根竹发卡固定,耳不聋,眼不花,上衣下裤十分整洁,一看就知道,是位很精明的老太太。
她把我带到她的门前就发号施令:“小师傅,你拿阉鸡捞子网住前门,我从后门唤回鸡从前门赶出,全会扑住的。”她的安排十分周密,令人佩服。
一会儿,后门传来她“咯咯咯”的声音,鸡都被她唤进了堂屋,我见那些公鸡,一只只面红耳赤,大红冠子绿尾巴,油亮的脖子金黄的脚,它们个个都是鸡中的男子汉了,凭我的本事是没办法阉的。老太太又十分精明,蒙混是无法过关的,真是出师不利。怎么办呢?我急中生智,当老太太背过脸赶鸡时,我“网”开一面,鸡们一个个扑腾着翅膀“咯咯”地逍遥法外了。
“网住吗?网住吗?”老太拉开门见我提着个空捞子,气极地用手指着我:“你这小师傅,不是个做生意的,不是个做生意的。”
老太太一语道破天机,我也懒得申辩,为了争回面子,我竟装模作样一声一声吆喝:“阉鸡呀,阉鸡呀!”扬长而去。
阉鸡这手艺最终未学成,就是现在看见阉鸡人,总有一种“不能小看”的感觉。手艺人凭本事,钱不是那么好赚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