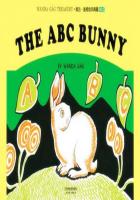“烟子吗?那我问你,我是谁?”皮匠爷装作不认识我的样子。可是,他眼睛在笑,我就放心了。
“你是皮匠爷,也是我二舅爷!”我嚷嚷道。
皮匠爷打了个响指:“对啦!”他从口袋里翻出一截皮绳,一翻一系,往我手上一套,哇,就成了一条皮手链,漂亮极了。
我举起手,绕着外婆打圈圈,要外婆看我的新手链。
外婆正急急忙忙往外舀面粉,打鸡蛋呢,皮匠爷来了,一盘子鸡蛋饼可不够!她用沾满面粉的手指,皱着眉头在我额头上点了点,要我给皮匠爷泡茶。
茶泡好了,鸡蛋饼也煎好了。皮匠爷却坐在火塘边睡着了!我和外婆烤着火,守着皮匠爷。
皮匠爷说过,每次来我们家,坐在火塘边的第一个梦,都是温暖的好梦,那全是因为有我和外婆守着。
外婆往火塘里加了木炭,火更旺了,把厨房烤得暖烘烘的。
皮匠爷在梦里嘀咕了一声,满意地舒展了手脚。
2
皮匠爷一觉睡到黄昏。
厨房里,暮色渐浓。外婆煨在火塘里的红豆粥,早就熬得香喷喷的了。
“好香啊——”皮匠爷说着,睁开了眼睛,“哇,天快亮啦!”
我哈哈大笑:“皮匠爷,是天快黑啦!”皮匠爷真好玩!
皮匠爷拍拍脑袋,嘿嘿笑了两声,坐起来拢拢火,半天,说:“有一忽儿,我以为回到了山里。”
“山里也有红豆粥吗?”我挨着皮匠爷坐下,问。皮匠爷身上有种特别的味道,那不是鼻子闻到的,而是看到的、感受到的。外婆说那是风尘味儿,外公说那叫沧桑,我觉得那就叫外面的味道。
“一罐粥,一塘火。”外婆说,“天擦黑了,我们围着火塘吃饭,在山里就是这样。”
我们像在山里一样,在沉沉暮色里,围着火塘吃了晚饭。饭后,也不掌灯,大家围着火塘坐着“唠嗑”。
“唠嗑”是皮匠爷说的,就是说话儿。皮匠爷说,有个地方,一到冬天就下雪,整整下一个冬天的雪,积雪太厚了,把房子都埋起来了。人们就像鼹鼠一样,在雪下挖出通道,相互串门子“唠嗑”。
那可真是太神奇了!
“有次,一个人喝醉了酒,驾着雪橇从邻村回来。狗拉着雪橇走啊走啊,那人吼着歌呢,突然,哗啦——一个调子卡在喉咙,再一瞧,竟然掉到了火塘边!他走错道,走到人家屋顶上去了。屋顶承受不住重量,就掉下来了。”皮匠爷说。
我听得哈哈大笑。外婆也笑了,眯着眼睛瞧着皮匠爷。
皮匠爷挠挠头,笑着承认了:“嘿嘿,是我驾着雪橇。人们冬天呆着家里正无聊呢,我这一摔,可热闹啦,人们从雪下的甬道里走出来,都来看从屋顶上掉下来的人。主人家温了酒,烤了肉,人们喝酒唱歌,简直成了个节日。”
我想象着皮匠爷掉进屋子的样子,笑得肚子都疼了。一个人走啊走啊,啪——掉到了屋子里,多好笑啊!
皮匠爷拧拧我的鼻子,说:“烟子,小心点别把鼻子笑歪了。”
我才不会呢!皮匠爷吓唬人,哪有鼻子能笑歪的。
外公在火塘上温一壶米酒。米酒的香甜慢慢溢出来。外婆也借着炭火,烤玉米粒。
皮匠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才接着说:“北方那些村子,靠在森林边沿上。森林里住着狐狸,狐狸特别喜欢吃鱼。村里的鱼贩子总是特别讨厌狐狸。有次,这个鱼贩子驾驶着雪橇,运鱼出去卖。雪橇走到路上,他看到路中央躺着一只狐狸。那狐狸可漂亮啦,皮毛像火焰一样。鱼贩子想,今天可走运了,捡了只狐狸。”
“狐狸死了吗?”我忍不住问,“它为什么不跑呢?”
啪——一颗玉米爆开了花,好香!外婆捡出那颗玉米花给我——哇,真好吃!
皮匠爷拍拍我的头,说:“那狐狸躺在雪地里,一动也不动。鱼贩子把手放在狐狸的鼻子上,一丝温暖的呼吸都没有。他就放心地捡起狐狸,丢在雪橇上。雪橇上装了好多鱼。狐狸一闻到鱼腥味就醒了。它只是饿晕过去了。狐狸拼命地吃鱼,啃啊啃啊,吃个不停。风呼呼地吹过,鱼贩子过了好久才注意到身后越来越响的声音。他回头一看,可不得了,狐狸活过来在吃鱼啦!”
“哎哟——”我忍不住叫出来,这只狐狸要被抓住了!
“狐狸看到鱼贩子发现了它,赶紧跳下车。可是它吃得太撑了,根本跑不动。鱼贩子一下车就抓住了它。一只漂亮的狐狸,比车上的鱼还值钱,鱼贩子好高兴,一手提着狐狸,笑啊笑啊——一不小心,踩在绳子里绊倒了,鼻子撞上雪橇,歪啦!”
“那狐狸呢狐狸呢?”我急忙问。
“鱼贩子痛得捂住鼻子。他一松手,狐狸就跑啦!”
哦,我放下心来,嘿嘿笑个不停。听皮匠爷唠嗑真好玩!
玉米粒烤好了,酒香也弥漫了厨房。外公端下米酒壶,倒在碗里。皮匠爷端起瓷碗,喝了一大口,眯着眼睛满意地品了品,说:“香啊!”
我和外婆一颗一颗吃着烤玉米粒。
火塘里,炭火慢慢燃烧着,温暖极了。
喝了酒,皮匠爷的话更多了。他说,他们还把积雪敲打结实,做成雪砖,在林子里垒雪屋住。往雪砖上洒点水,砖块转眼就冻在一起,垒成的雪屋又结实又暖和。晚上,他们在雪屋里烧篝火,说故事。白天,他们就在林子里打猎……我们守着火塘,听皮匠爷唠嗑。夜,宁静悠长。在初冬微冷的空气里,我似乎闻到了雪的气息,似乎听到雪花飘落的声音……3
过了一晚,皮匠爷说,歇息够了。
上午,他和外公一起去了地里。
下午,他和外公一起修整了竹篱笆,把院子清理好,整平整了。
黄昏时,他搬出背来的竹筐,从里面挑挑拣拣,拿出一块黄褐色的牛皮。
“烟子,把脚伸出来!”皮匠爷说。
我乐呵呵地脱了鞋子,伸出脚,踩在外婆拿来的土纸上。皮匠爷用炭笔,绕着我的脚在纸上画了一圈。炭笔凉凉的,好痒。我笑嘻嘻地动个不停。皮匠爷只好画了又画,最后,纸上画满了脚印,一个也看不清了。
天色在一个个脚印里黑下来。外婆说我捣蛋。我说是天黑得太快了。
我们只好挪到火塘边。吃过饭,外婆特意点上了灯。
画坏了外婆三张土纸后,皮匠爷把炭笔放下了。
“咱们得想别的办法。”皮匠爷说。我也帮着他想办法。我用浆糊把纸黏在脚上,这样纸就不会动了,外婆可以依着我的脚剪下鞋印子。
皮匠爷要用土纸剪下我的鞋印子,根据鞋印子的大小给我做鞋。
这一招管是管用了,外婆把多余的纸剪掉。可是,浆糊黏住了我的脚,剪好的鞋印子扯不下来。外公一用力,哧——撕坏了。
外婆瞪着我。皮匠爷使劲哈哈笑,他的笑声震得空气嗡嗡响。我们都笑了。
最后,还是外公想了个办法,他磨了墨汁涂在我脚上。我踩在土纸上,踩出个脚印子来。外婆把脚印剪成鞋印子。皮匠爷按着这个鞋印子量皮子,估摸着给我缝新鞋子。
我搓呀搓呀搓,用力把脚丫里的黑墨汁搓掉。哎,墨汁真黑!
皮匠爷是个皮匠。每年,他都会给我缝双新鞋子。皮匠爷缝的短皮靴可好穿了,又软又贴脚又暖和。
皮匠爷给我做新靴子。我们都围在火塘边。
皮匠爷在腿上铺上围裙,拿着剪刀咔嚓咔嚓剪着牛皮。这时候是不能打搅的,要是剪错了,缝出来的靴子就不好看,也不好穿。
外婆要多点一盏灯。皮匠爷说不用,他说:“我的手长了眼睛,知道在哪里下剪子。把满屋子点上灯,那是新手干的活。”
手上长眼睛!我凑过去看皮匠爷的手。他的手上有很多皱纹,也有很多茧,没见着长眼睛呀!
皮匠爷哈哈大笑,说我幽默。外婆拉过我,轻轻对我说:“皮匠爷开玩笑呢,他做了很多年的皮匠,手干活熟练了,就像长了眼睛一样。”
原来是这样,皮匠爷才幽默呢。
剪好了牛皮,皮匠爷拿出针和线缝起来。这针线可和外婆的针线不一样,针要粗些,很亮,线也只有棉线那么粗,但是透明的,扯也扯不断。
皮匠爷个头很大,缝起来很灵活。
哧——哧——,针领着线穿过牛皮,发出好听的声音。这声音把黑夜和白天紧紧地缝在了一起。
4
夜晚降过霜,田野和房舍上像下了一层薄薄的细雪,村庄外的林子也是一片银白。
皮匠爷坐在门槛上抽着烟斗,看着面前的原野。
我端着热腾腾的粥,挨着皮匠爷坐下。
早晨,空气清冷,清澈透亮。原野瞧上去,有一种空旷的美。太阳出来了,白霜皎洁晶莹,透映着紫色的暗影。
“真漂亮!”皮匠爷说,“也很安静。”
我点点头。我喜欢村庄的早晨,安安静静地守着太阳升起来。
“烟子,我到过一个地方,那里的冬天又美又热闹,”皮匠爷说,“在东边,有一大片黄土地,地是黄土的地,山是黄土的山。那里的人依着山坡,挖出一个个窑洞当房子。”皮匠爷抽了一口烟。烟斗里冒出淡淡烟雾,在晨光和晨霜的映照下,似乎也带上了淡淡的紫色。
“有树吗?”我问。原野里,树木在晨霜中矗立,很安静的样子。
“树很少。”皮匠爷说,“地也很少,一眼望去,都是黄土地。”
“哦——”我说,“那恐怕不怎么好看。”
“那地方,河流也少,偶尔有条小河一到冬天就干涸了。”皮匠爷在地上敲敲烟斗,地被冻结实了,敲起来嘣嘣响。
我们有一会儿没说话。趁着外婆不在,我把粥喝得唏里哗啦响。外婆不许我很响亮地喝粥,说那样不“雅气”。可是,哗哗响地喝粥,可痛快啦!
“那地方真的美着呢!”突然,皮匠爷说,他皱了皱眉头,“真奇怪,那地方很少有河,树也很少,村子藏在黄土堆中,但就是漂亮!”
那是什么样的漂亮哟?我想象不出来,嗯了一声,舔舔碗沿,说:“皮匠爷,外婆今天煮的红豆粥里,添了枣子,好甜啊。”
皮匠爷嗯了一声,在地上把烟斗敲得嘣嘣响:“那里也种枣子。枣子个头大得很,也甜得很。枣子树种在屋角、墙头、灶房边。秋天打枣子,一棍子下去,噼里啪啦下雨一样。那枣子,有外婆做的糯米团子那么大,晒干了也是鼓鼓囊囊的,咬一口,甜得牙疼。”
这个皮匠爷,净馋我!
“听说,枣核里住着小人。”
什么?小人!住在枣核里!
“我给人做个皮背篓,剩了点零碎皮子,就丢在筐子里。没几天,有人找我补皮篓子。我到筐子里翻碎皮子,嘿——没啊!”皮匠爷一拍手,说,“这可奇怪了,我翻了老半天,把筐子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那些零碎皮子。”
“被枣核小人拿走啦!”我瞪大眼睛。“我收集了不少漂亮的小扣子,老是丢,莫不是也被小人拿走了!”
“或许吧。人家告诉我,天冷了,枣核小人拿回去做皮袄去了。小人既然要缝皮袄,也得要扣子吧。不过,我守了几夜,都是半夜一过,就困得不行,一直都没看到枣核小人……”皮匠爷在门槛上磕磕烟斗,门槛砰砰响,“其实,在那里枣子还算不了什么。那里的人打鼓才叫气派呢。这种天气,没啥农活,大家就聚在一起——咚咚咚、咚咚咚——敲得震天响。”
“就像端午节那样打鼓吗?”我问。端午节,划龙舟。新做好的龙船下水前,人们要抬着,在村子里游一圈。敲鼓的人就走在龙船前头,一面大鼓,两个人抬着,一个人敲,咚咚咚、咚咚咚,可威武啦。
皮匠爷撇撇嘴,说:“人家那才叫敲鼓!敲大鼓的,鼓比桌子还大,敲鼓的人又是跳舞又是敲鼓,好听又好看。不过,最漂亮的是敲小鼓,挂在腰上,那儿叫腰鼓。一边跳舞一边打,前两下,后两下,跳起来再敲两下。鼓槌上还绑着红绸带,敲起鼓来,绸带飞舞,哎哟哟——”哎哟哟——那可真热闹!
皮匠爷拿着烟斗在门槛上轻轻敲着,砰砰砰——似乎在回味那跳跃的鼓声。我也不说话。外婆喂的芦花母鸡跳出来,咯咯叫个不停。
我想着要不要去捡鸡蛋,这只芦花鸡,偏喜欢早上下蛋!
皮匠爷不敲门槛了,问我:“你见过母鸡飞到窗户上吗?”
母鸡飞到窗户上?外婆可不允许。我摇摇头:“没见过。”
“那母鸡比这只母鸡漂亮。”
我不服气,我们家这只芦花母鸡可漂亮啦,羽毛油亮整洁,外婆说它长得“端正”。
皮匠爷嘿嘿笑了:“那母鸡翅膀上的花纹就像菊花一样,不单是菊花,想开什么花,剪刀咔嚓咔嚓几下,就成了什么花!”
开花的母鸡?还用剪刀?
皮匠爷瞧着我迷糊的样子,可得意了,哈哈大笑了半天,才说:“剪纸呢,烟子!”
“哦——”这我明白了,外婆冬天也往窗户上贴剪纸,蝴蝶呀,喜鹊呀,梅花呀什么的,阳光照在窗户上,火红的颜色,又吉祥又热闹。
“黄土地里,人们剪母鸡,剪枣核小人,剪的最多的,是花。窑洞只有一面墙上有窗户,老大的窗户,有半面墙那么大。人们在窗纸上贴满了花,还在门口挂花门帘布。”皮匠爷一扬手,“走在黄土地上,满眼都是土地的黄褐色。突然,眼睛一亮,门上、窗上,到处都开满了艳丽的花,就知道村庄到了……”
我端着粥碗,望着满脸红晕的朝阳,想象着冬日阳光下,那个遥远的、“开”满花的村庄。
原野上,传来牛的哞哞声。村子里的狗也叫了。炊烟升起来,村庄在朝阳的温暖里打着哈欠,伸着懒腰,醒来了。
“不知怎么的,瞧着眼前这个水灵灵的村庄,就想起那里来……”皮匠爷低声说,他眯着眼睛,抽了一口烟,“生活在肥沃的土地上,真是一种幸福!”
我问皮匠爷,幸福是不是就是快乐的意思。皮匠爷点点头。
“黄土地上的人们打鼓,剪花,有糯米团子那么大的枣子吃,还有枣核小人,真幸福啊!”我说。
皮匠爷哈哈笑开了。真好,我不喜欢皮匠爷皱眉头,我喜欢他笑。皮匠爷的笑容,就像阳光一样,很明朗。
5
皮匠爷喜欢坐在晨光里抽一袋烟,慢悠悠地,守着太阳升起来。白天,他和外公一起收拾些农活,黄昏,有时领着我去田野里散步,有时坐在外婆的土灶下,给外婆生火。
晚上,我们围坐在火塘边。外公敲敲打打,修理些小东西。外婆在缝新花袄,我呢,专心看着皮匠爷给我缝新靴子。
他一针一线拉得很紧,缝过的地方很难看到针脚。
一晚又一晚,新靴子渐渐成形了。皮匠爷说,快缝好了。
我喜欢新靴子缝起来,又希望新靴子没缝起来。
(选自《少年文艺》[江苏]2011年第1·2期合刊)
飘扬的红领巾
翌平
一
阳光为他黝黑健壮的轮廓镶了一层金边,他坐在船头,斜叼着一根用报纸卷成的纸烟,不经意地望着远处的海。
他,是我的哥哥,我很羡慕他那一身匀称健美的肌肉。海面上炽热的阳光,为它镀上一层古铜色,不动的时候,他真像是一个雕塑。可他会时不时地转过头,对我恶声恶气地嘟囔一声:“用力划。”
我们的小船名叫海盗号,船头的旗杆上挂着哥哥缝制的海盗旗。
它正驶向牡蛎礁,我们去打海捞儿,在嶙峋交错的岩石下,藏着许多海货,哥哥是有名的潜水高手,在孩子群中,大家公认的有两大高人,第一个是“海蜇”,第二个就是外号“灯塔”的哥哥。
我不知道哥哥为什么让我用双桨划船,家里的小木船已经装了马达。听妈妈说,爸爸因公殉职的补偿金三年后才发到我们手里,哥哥用其中的一小部分买了这部老掉牙的引擎,尽管如此,每次出海他依旧让我划桨,当我将手上的水泡挑破,缠上破布时,我会向他投去乞求怜悯的目光,这时候,他就会拿掉嘴上的那根土烟,恶狠狠地说:“看什么,划!”我也会狠狠地咽一口唾沫,用力接着舞动双桨。
牡蛎礁离岸边不远,夏天到这里旅游的人,站在沙滩上就能看到它,可要是划到对面需要一个小时。每次出海,他就像个船长,而我只是海员,一个必须对他唯命是从的仆人。在这段单调的航程中,我闭上眼睛就会看到身穿海盗服的我,脊背上留着八爪鱼的文身,我的肌肉比哥哥更强壮。驾驶的小船是一艘有十张大帆的快艇,每次我都可以爬到桅杆的顶部,向下面的人通告闯入视线的猎物。有时候我会忽然闪现这样的幻觉,我领导船上的人暴动,制服了那只独眼儿的船长——也就是哥哥,将他塞进狭小的鱼货舱,他挣扎着苦求着,我们都无动于衷,最后我会狠狠地踩下那扇舱门,任凭他在低闷的鱼舱里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