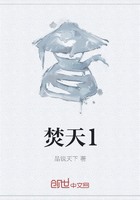玫瑰色花终于到了凋零的时刻,他们紧紧抓住彼此的双手,要么平静得喘不过气来,要么幸福得喘不过气。两个人靠近,彼此喃喃低语,直到中午时分太阳照在脖颈上,然后他们试图赢得一种短暂的延缓:那就是在爱情中挣扎,在爱情中回忆。
Δ敞开了心灵之窗
圣—琼·拜斯说:男人也奇怪,没有岸,却泊靠在岸边的女人身旁,而大海我本身仍走向你的东方,如同走向你那混杂的金沙,并在你的岸上,在你的粘土圈——与孕育她的波浪同生同散的女人——缓缓的展开之中流连忘返……最后一片玫瑰花瓣终于凋零了:她现在决心向他敞开心灵之窗,她决心去打开那只抽屉,告诉他。因为40多年来,那只被永远锁住的抽屉对他来说是一个谜。很多次,他都想解开那只抽屉之谜,但很多次当她的体温从他皮肤上升时,他又犹豫了,因为爱她,他可以容纳那只被锁住的抽屉之谜。40年过去了,现在,她打开了那只抽屉,这是40多年来她头一次打开抽屉,这只散发着檀香木味的抽屉,锁住的是几封信,用粉色绸带捆住的几封信对她来说是一次回忆,是一个只有开头,没有结尾的故事。
有一年冬季,他带她去旅行,在中途,他把她留在了旅馆,因为公务缠身,他不得不提前离开,那是他们的第一次旅行,是新婚之前的一次旅行。她孤零零地住在小旅馆里,独自一人在那座小镇散步,就这样她碰见了那个后来给她写过几封情书的青年男子。他陪她在小镇外的小径上散步,走到很远的湖边,然后回来,这个青年也是旅行者,他就住在她同一层楼上。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三天,她突然意识到不该在此多停留,她在那个青年男子的眼里看到了一种热情的光芒,她害怕与他目光对视,她害怕和他继续去散步,在一个早晨,她搭上了一辆过路的客车,离开了那座小旅馆,回家以后,她就收到了那个青年男子给她写来的情书。
圣—琼·拜斯说:一如盐存在于麦子,你身上的海存在于其本原,你身上属于海的东西,给你养成了易于接近的幸福女人的趣味……他在情书中告诉她,他使用了许多技巧,才在小旅馆的客房登记册上寻找到了她的地址,这对他来说是一次幸福的收获。从此以后,他就给她写情书,他告诉她,虽然时间很短,但他无疑已经陷入了一种相思病之中去。他用写情书的方式把他的相思病传染给她。
她起初还饶有兴趣地拆开那些情书,因为在她生命中,她还是头一次读到这样的情书。慢慢地,当婚期逼近时,当另一个男人拥抱她时,她惊悸地告诉自己:不能再让他给自己写情书了,不能再让他的相思病传染给自己,因为自己就要结婚了。所以她必须给他写一封信,尽管这封信会伤害那个患相思病的青年男子,她还是给他写了一封信,并在信中告诉他自己已经是别人的新娘了,请他不要再给她写信。他果然中断了将相思病传染给她的欲望,他的情书犹如雾一样散去,留存在手中的那几封情书就成为了她的秘密。
结婚以后,她继续带着几封情书跟随他迁徙,她把那年冬天的意象全部锁进了那只抽屉里去,从而锁定了那个只有开头而没有故事结尾的故事。每当她看见那只抽屉时,一种记忆就会上升:在那年冬天,在他们新婚之前,当他因公务缠身把她独自留在小镇旅馆时,她碰到了一位青年男人,他有着非常普通的面庞,在某种程度上,她已经忘记了那张脸,只记得他带她到小镇上散步的情景,他陪着她,度过了那段寂寞的日子。
她将抽屉敞开,那些情书裸露着,他不想伸手接触那些情书,然而,她给他讲述的故事终于使他心灵中的谜露出了真相:他伸出手去轻轻地接触着信封上的邮戳和邮票,40多年过去了。这个谜使他想起那个小镇上的冬天,那个只有靠信笺上的指纹才能捕捉的青年男子的衷肠,以及他的相思病已被他看见。当她向他敞开窗以后,那只抽屉中的谜——充满在他们晚年的沉静生活中,成为了往事。
Δ爱情的永久享受者
圣—琼·拜斯说:……爱情啊,爱情你把我诞生的啼叫保持这么高,使它从大海走向情女!所有沙地上遭受践踏的葡萄藤,浪花在每个肉体中的善行,沙滩上水泡的歌声……致敬,向神圣的勃勃生机致敬。他和她始终享受着爱情。他们的爱情可分为三阶段:其一,谈情说爱最甜蜜的时期无疑是婚前,那时候他们之间没有可以守候的城堡和物质生活,惟有相互守候的爱情才是他们之间的世界。一个星期的约会总是在周末,这是他们让脚尖在地面上旋转的时刻,飞快地沿着水泥地面旋转到约会地点,无论明月和小桥流水,还是蟋蟀声都是那么美好。在约会中,他们可以把说过的情书说了又说,尽管如此,那些情话对他们来说仍然是那么新鲜,这个阶段是恋爱者不为他人只为爱情而活着的时期。其二,婚姻产生以后,开始两人守候着城堡和两个影子,接下来,一个孩子的啼哭声划破了天际,他们将爱的视线转移在孩子身上,盼望孩子长大的梦想使他们开始为孩子而活着,这当中,两个人肩并肩地和那个孩子在一起,在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同样他们已经同他们爱情的果实在一起。其三,孩子拎着箱子离家出走的那一天,意味着他和她已经尽了爱情的职责,他们很清楚,孩子离开他们的时刻,就是他们彼此重新守候的日子。为婚姻,为孩子而建造的城堡空空荡荡,现在,是他们两个尽情享受爱情的时间:屋子里炉火正旺,而外面的冰雪覆盖住了大地。两个人开始用手指勾勒住已经完成的诺言,无论是爱情也好,孩子的出生到抚养也好,都是他们天长地久爱情中的一种诺言。现在,面对炉火,他发现她已经在等候他的到来。
圣—琼·拜斯说:出生于海的男人躺在我躯体的沙滩上。愿他把脸贴在沙下的泉水里汲取清凉,愿他如身上刺着雄蕨图案的神,在我的平地上得到欢乐……尽管他们每天面对面的生活,为现实而面对面,为了孩子而面对面,为了物质而面对面,现在,她坐在椅子上,他的到来——将使他们面对面地沉浸在爱情,他们已经携带青年时期的那萨克斯中忧郁的、狂热的爱的音符进入了暮年。现在,他们可以面对爱情了。
面对爱情,也就是面对他们各自已经被岁月所改变的那张脸,她的脸再也不可能是一只正在成熟的苹果,她的脸上的皱纹像一只苹果经过霜染之后,从春到冬的、经历了梦寐以求的每一种理想之光的燃烧之后,那只苹果意味着和平与宁静,尽管苹果已经开始干枯,但从那只苹果上显露出来的颜色就知道,它香气依然……而面对他的那张脸,首先,在过去,他是河边的那些笔直的柱子,和他约会时,她总是感到他像一根根伫立在河岸的柱子,可以撑起一切。后来,他果然就是她生命之中的一根根柱子,撑起了碧草连天,也撑起了黄沙漫漫,现在,伸手去抚摸他的影子,那根柱子虽然已经失去了过去的力度,但它仍然撑起了面前的这座城堡,于是,他们才有可能平静地坐下来,享受爱情。
从用手触摸到彼此的影子那天开始,他们就开始学会了去享受黄昏约会之中的柳叶的影子,倒映在水中的影子——在他们享受爱情时,记录了他们灵魂远去,随同流水远去的时光,当他们体味着婚姻中肉体的快感时,爱情所唤起的一种性的?茨维塔耶娃说:凡是别人不要的,都请你们给?一切都应当在我的火里烧尽!我既招来生命,我又招来死亡,作为一份微薄的礼物献给我的火。有一种爱情存在着,它对于她来说永远是模糊的,事情发生在她梳着羊角辫子的年代,她19岁了,在一条胡同里穿行时被他看见。不久之后,他就给她送礼物,从送一朵花开始,那座小镇没有玫瑰花,他就给她送一朵野花,有时候送一朵石榴花,后来,他就离开了,当她知道再也没有人送给她花时,她觉得世界是那样无聊和空虚——她哭了,伏在那只枕头上,第一次为一个男孩的离去而哭。
但她决心把这件事忘记,尽快地把那个男孩送花给她的快乐忘记,就像那个男孩突然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一样。然而,第二年春天,她又在那条胡同里看见那个男孩,男孩举着一束玫瑰花,下了车,直奔她而来,那是她生命中第一次看见玫瑰花,她被这种既有荆棘又有香气的花朵震惊了,她忘记了那个男孩的不辞而别,忘记了自己想把那个男孩忘记的念头,她捧着那束红玫瑰,开始被那个男人的出现以及红玫瑰的香气和荆棘所包围着。有意思的是,这个男孩再一次从她视线中消失了,而且这一消失就是永远,从此以后,她在那条胡同以及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看见过那个男孩。
她曾经无数次地想念那个男孩,在睡梦中,在她爱上另外一个男孩之后,如果那个男孩在任何时候能够出现在她面前,她认为自己都会去爱上他。但问题是这个消失了的男孩再也没有出现过,甚至他献给她的那些花朵和那束红玫瑰花显得就像梦境一样不真实。事实上,从此以后,对那个男孩的回忆就是对一段梦境的追记忆。
茨维塔耶娃说:我是凤凰,只在火里歌唱!请你们维护我的崇高的生命!我高高地燃烧,烧个干净,而你们会得到一个光明的夜。在这个像梦境一样虚幻的故事里,一切都那样模糊:一条胡同是模糊的,它两侧的民房也是模糊的;最初送给她的小花是模糊的,一朵石榴花也是模糊的,对她来说,那束红玫瑰花是真实的,但在现实中却也是模糊的。
而那个男孩的出现,意味着他只是在她梦境中出现过的一道影子,他的年龄刚脱下学生装,他在那条小镇胡同出现,他看见了那位梳着羊角小辫的女孩,他为她而采摘野花送给她,他是不是陷入了当时的梦境,把那个女孩当作了他的仙女?
玫瑰花从,从他怀抱到她怀抱的那一瞬间,她根本没有想到这个瞬间只会留存在记忆中,成为永远,所以,当她看见那束红玫瑰时,她第一次感到一个男孩送给她的玫瑰花可以插在花瓶里,可以被她嗅着,可以是一种感情,正当她探出头去在窗外去寻找他时,他便消失了。
她至今仍然不明白,那个男孩为什么会在她生活中永远消失?当她牵住另一个男孩的手,她想念着胡同中的男孩,她想把对那个已消失了的男孩的感情给予正在牵手的男孩,她觉得一个男孩是模糊的,是中断的镜头,另一个男人却正在与她牵手,她被这个牵手的男孩携带着,一方面是婚姻,一方面是爱情,另一方面是对一个变得模糊男孩的回忆……她用插玫瑰花的方式纪念那个男孩给予她的梦境,她坐在花瓶前:用一切尽可能的方式在回忆那次模糊的冲动,时间使她的头发开始变白,使她的身体开始变萎缩。她垂下头,一边打盹,一边回忆,那个男孩却似乎不会变老,他永远从那条小镇胡同闪出,挡住她,站在她对面,将一束鲜花送给她。这个情景永远是模糊的,那个男孩是模糊的,往事如烟是模糊的,凋零的玫瑰花才是现实的。在转瞬之间显示她灵魂在燃烧的梦境突然置入了现实,所以回忆是美好的。 Δ美丽的蓝色
米兰·昆德拉说:实际上,谁才是强者呢?当他们置身于爱情地带,或许他真的是强者。但当爱情从他们脚边溜走时,她却成了强者,而他成了弱者。蓝色环绕着她的意志,因而她是蓝色的。清晨,她正在与自己的60多岁作斗争,现在,她的蓝色被她带到了操场上,晨跑是她让自己的蓝色意志转移的空间——她在岁月流逝之中表现出与衰竭作斗争的勇气,这来源于她的丈夫。那个男人总是迷恋她身体上的蓝色,当她是一个小女孩时,她的蓝色决定着她的呼吸、着装、声音,有一次,他与她在月光下散步,她披着长发站在他面前,那时候的她有一种蓝色——可以让她去生活,在她的头发的光泽和嘴唇里,他发现了她正是他要的那个女人,他被她迷惑着,这就是爱吗?接下来,为了这种爱,他送给了她各种各样的与蓝色有关的礼物,比如,一块手表,指针是蓝色的,当她看到那只表上的蓝色指针时,她让他感受她的心跳:一条蓝裙子,对她来说穿在身上可以参加舞会,穿在身上可以出现在人群、街角,她在那条蓝裙子中寻找到了身体的快感。
60多岁,对她来说是一个困难的时期,她不可能再穿那些蓝裙子了,只有那块手表始终陪同她,蓝色指针给予她一种自信,即使60多岁了,她仍然可以点燃一场无比炽烈的蓝色火焰,她仍然可以让他站在身后欣赏她,并给予他力量。
他给予一个蓝调女人变换姿势的自由度:当她靠着那片蓝色来支撑她的60多岁时,他送给她一辆蓝色跑车。一个男人应该如何对待一个到了60岁仍然野心勃勃的,用蓝色来显示自我的女人呢?
米兰·昆德拉说:他感到了一种无可救药的伤痛,而且,那种伤痛还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它就像在炫耀一种人人都看得见的不公平一样炫耀着自己。但他已经没有耐心等待尚塔尔回来向她解释这一切了。他看着60岁的女人将那辆蓝色跑车开出去后,她不断想出新的计划,他看见跑车在她手的旋转中已经奔驰出了郊外,这是他给予一个女人爱的自由,因为爱她,他便爱那个女人所爱的一切,所以他满足她的愿望,他给予她一辆跑车,颜色由她操纵在手中,她可以驱车到她想去的任何地方,让她体会到蓝色的孤独,在中途,她停下车,进入一家小餐馆,要了几道小菜和一瓶啤酒,美丽的蓝色在她四周弥漫着:她在与自己的年龄作斗争时散发出一丝如梦如烟的微笑,这就是她的蓝调使她区别于所有60多岁的女人。她喝着啤酒,60多年来,她热爱着这个世界,当她从她母亲的子宫中掉在襁褓中去时,她就已经被那块蓝色襁褓紧紧裹住,她驱车出游的最为重要的目的就是把灵魂,那颗被蓝色荡漾的灵魂交给世界。
在小号吹奏的节拍中已经将车开到了她的故乡。故乡是一个人报之以微笑的地方,对这个女人来说,故乡是把她轻轻从子宫中托出,交给蓝色襁褓的地方,她开着车在那座丘陵似的小镇——看望了长寿的母亲,她送给母亲的蓝色手镯,仍然戴在母亲手上,她从她母亲那里学会了在对世界的热爱中产生出灵感:她要坚持不懈地驱着那辆蓝色跑车,为了一种小小的,人类的最值得环绕下去的幸福的理由而活下去。
这正是他欣赏她,爱她的理由:她的蓝色始终在感染着他,并给予他另一种灵感,为了这个世界上最有魅力的蓝调女人,他愿意把所有的爱都给她,这正是他真正的生活。
她在驱车回家的路上,他已经嗅到了她身上好闻的气息,那些花草和溪水以及繁星的味道——始终让她能够用蓝调子铺满回家的路,一条可以暗示一个梦想的路才是她真正的路。
Δ重新塑造他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