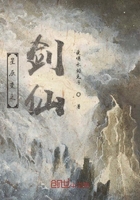实践证明,今天太需要依法办事、按章办事的原则了。因为只有符合现代政治精神的法规和规章,才能从根本上保障最大多数人民的安全和利益。过分宣扬“照顾”,麻痹了人们对法治的追求,压抑了公民意识的成长。在“反右”时,有几个大人物利用自己的威望照顾了几个人免戴“右派”帽子,但我们还是反出50万“右派分子”;“文革”时也有好心的大人物照顾了几个人免遭迫害,但冤假错案依然遍及域内。“照顾”只在微小的局部完成了某些人的道德义务,却挡住了人们观察全局的眼睛。巨大的代价告诉我们,“照顾”一词应从现代政治生活中驱除,代之以依法办事、按章办事的原则。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大量的帝王影视。戏中对“明君”的赞美和臣民的贱视,大大地恶化了现实的政治空气,就是一些反映现代生活的影视,也不自觉地套用着臣民和奴才的语言,污染着当代的民主和平等。
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它需要观念的现代化,也需要政治用语的现代化。用语的守旧恰是观念守旧的反映,只有观念更新、用语更新,方能造就大写的“人”——现代公民。
原载《北京日报》2008年7月14日
新闻事实的真假比记者身份的真假更重要
魏剑美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新闻主管部门最着力的一件事情就是打击假记者。于是我们有幸看到各媒体在显要位置刊布“敬请核查本媒体记者真假”的声明,也陆续从报端看到逮着假冒记者的“看点新闻”:湖南一假记者站站长敲诈到真记者站站长头上;广东县委书记抓住三个企图敲诈他的假中央电视台记者;山西运城一个县级收费站3小时内查出19名假记者;而最著名的是山西大同煤矿主打死假记者兰成长的事件……我留心到,这些揪出“假记者”的新闻中,那写报道的真记者在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都是欢欣鼓舞的情绪,而没有一个人试图去冷静地追问一下:这些“假记者”们所做的是不是真新闻?
假记者最为人指斥的是假借新闻采访之名行吃喝玩乐、敲诈勒索之实,其手段无外乎是抓住当事人的某一把柄,以“曝光”相要挟。但常识告诉我们,被要挟的人多半是强势群体,没有确凿的证据在人家手里他们哪里肯乖乖就范!这些假记者除了将采访做深入,将材料整扎实之外,事实上并没有别的什么可以依仗。如果其调查本身不能过硬,别说敲诈不成,人家首先就可以治你一个诬陷和诽谤的罪名。
那么,一个没有真实记者证的人到底有没有调查、了解新闻真相的权利呢?对此,法学专家们早就指出,新闻报道源于公民的言论自由。除非被剥夺了政治权利,言论自由对每一个公民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可以报道新闻,发表评论。联合国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上明确主张人人有“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也就是说,即使这些人是“假记者”,也丝毫不影响他们采访行为的正当与合理,其非法之处仅仅在于他们将正当的行为用于非正当的目的。
假记者泛滥最起码揭示了当前传媒界的两大真相:一是大量的社会负面新闻被真记者们所漠视。媒体没有尽到“监测环境”的天职,其留出的大量空间被“假记者”们所利用。我们要问:既然在采访便利上受种种限制的假记者都可以掌握扎实的材料,为什么货真价实的“无冕之王”们却屡屡缺位呢?说到底还是“报喜不报忧”的新闻传统与体制在制约着。面对假记者们发掘出的真正的新闻,媒体不去反思自身的不作为,却沾沾自喜于“揪出了假记者”,这是一种悲哀!
当前传媒界的另外一个潜规则就是,只要是真记者,其非法获利被揭发的危险系数就会大大降低。事实上一些真记者利用吹捧或者要挟来牟利早就是业内尽人皆知的秘密,但其不仅没有被揭发,反而步步高升,甚至还成了“模范记者”和“十佳记者”。这样的真记者,笔者能有名有姓数出来的就不止一个两个。从某种角度来说,那些以敲诈为目的的假记者还只是零散的、偶尔的,而靠掌握话语权牟利的真记者才是体制性的、日常性的。
所以,我厌恶假记者,同时也同情他们,因为他们并不比某些“真记者”更卑劣。
原载《中国青年报》2008年1月3日
一篇不及格的高考满分作文
王晓渔
底层问题至关重要,如果关注底层成为集体表演,那就会适得其反,只能导致对底层问题的冷漠。
2008年,在近10万份上海高考考卷中出现一篇满分作文,这也是2006年以来上海高考惟一一篇满分作文。据说这篇文章在阅卷中心组里被从头到尾朗读一遍,有些专家当场被感动,经过激烈讨论,最终决定给这篇文章满分(《东方早报》6月19日)。
我最初对这篇满分作文充满期待,作者首先表达了自己的困惑:“让我怎样称呼他们?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农民子弟?亦或是农民工二代?”这种疑问同时也是一种思考,遗憾的是,接着读下去,没有惊喜,反而非常失望。文章除了文字通顺,并无太多新意,只能说是一篇不及格的高考满分作文。
这两年,文坛盛行“底层写作”,即以弱势群体为对象的写作。这篇作文也可以称为“底层作文”,可惜它几乎集中了“底层写作”的所有弱点。文章中的“底层”是想象的、“同情”是抽象的。作者对“他们”并不了解,只能在城乡二元对立的格局里描述“他们”。城乡二元对立的问题确实存在于当下中国,可是,作者把乡村田园化,称“他们从小生长在故乡的青山绿水中,纯洁的灵魂在田野里抽穗拔节”,又把城市地狱化,称“繁华的现代文明不曾给他们带来任何快乐”。这与其说是“他们”的感受,不如说是“我们”的感受,是患上“怀乡病”的城市人的感受。作者忽视了这么一悖论,为什么城市拒绝“他们”,“他们”却涌向城市?文章提到“为了生计,为了未来,他们跟从父母来到了城市”,这与乡村田园化、城市地狱化的描述恰恰是冲突的。
阿伦特曾经说过,同情只有在针对具体个体时才可能,针对大众时它就变成了抽象的,甚至产生灾难性影响的东西,当对同情的克制能力被破坏,便产生了意欲以极端手段铲除不幸的倾向。除了“以极端手段铲除不幸的倾向”,还会出现另一种现象,即对同情对象以及同情本身的无限赞美。这种赞美给同情对象允诺一个远景,然后让他们忍耐现状。这篇满分作文不仅充满对抽象的“他们”的同情,即使面对具体个体,作者的同情依然是抽象的。文章讲到:“记得一位记者问一个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学成后是否会回到家乡时,小姑娘毫不犹豫地说:当然,一定回去!那一刻,我差点落下泪来,为他们的成长。”对小姑娘的同情,升华成对“他们的成长”的感动。在记者面前,这个小姑娘有没有表达自己的内心想法?她是不是按照预设的标准答案回答?在回到家乡和留在城市之间,小姑娘能否自由选择?作者没有考虑这些问题,而是差点落下泪水,这种泪水是善良的,也是天真的,更是无力的。事实上,小姑娘根本没有决定留在城市的权利,她对乡村的选择是被动的,甚至称不上选择,只是不得不接受这个结果。如果可以自由选择,至少一半以上的“他们”会选择留在备受歧视的城市,而不是牧歌式的乡村。
重要的不是歌颂田园,也不是歌颂背井离乡的“他们”,而是思考为什么“他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愿意生活的地方,并且拥有尊严、不被歧视地生活。作者也提到户口和暂住证的区别,这些都被“虽然……但是……”一略而过,“虽然,他们还在为不多的学费而苦恼;虽然,学校还是交不上水电费;虽然,还有好多体制还不够完善……虽然有好多个‘虽然’,但是,只有一个‘但是’就足够了,已经有好多视线转向他们,他们正在茁壮地成长”。这种“虽然……但是……”逻辑恰恰是对底层问题的回避,以望梅止渴的方式抹去种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篇末“他们,终将会成为我们”只是一句美丽的口号,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更有可能的是“他们,永远成为不了我们”。
“底层写作”并非一无是处,可是这篇获得满分的“底层作文”仅仅表达了想象的底层和抽象的同情,以“虽然……但是……”的逻辑抹去实质性的问题,以抒情代替思考,堪称“底层写作”的失败范例。在这里,我不想苛求这位作者,对于一位18岁上下的学生,不能要求太多。让人困惑的是,为何久经考验的阅卷专家会被这篇只是道德表态的文章感动?为什么他们对这种“底层作文”不加反思地全盘接受?高考满分作文具有强烈的示范性,将会直接影响中学生的写作模式,据报道,参加中考的初中毕业生已经把这篇文章视为范文。底层问题至关重要,如果关注底层成为集体表演,那就会适得其反,只能导致对底层问题的冷漠。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8年6月22日
“进课堂”二题
房向东
京剧还是科幻进课堂?
最近被热议的一个话题是京剧进课堂。
我不喜欢京剧。为了对这一艺术有所了解,曾经硬着头皮看过十场以上的京剧,如果没有打字幕,不要说唱的听不懂,就是说的也听不懂。我对京剧的印象是:有话不好好说,有歌不好好唱。尽管不喜欢,但我热诚地期望京剧走向中兴,道理很简单,我不喜欢,有人喜欢,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从现在的事实看,京剧是小众化的艺术。为什么小众化的东西要硬性推广,让大多数人接受呢?这不符合常理。说京剧是国宝,那国宝还多得是,比如象棋、围棋、武术、相声等等,难道都要进课堂?京剧比民歌难唱,比通俗歌曲难唱,学校的音乐老师甚至都唱不好京剧,让所有学生乱哼哼,那是糟蹋了京剧。
不论是传统京剧还是样板戏,都与孩子甚至大众的日常生活有一定的距离。因为这种距离,决定了京剧只能走向式微,靠强力挽救,也无济于事。“文革”期间,一台样板戏反复看三五遍,甚至十来遍,也不见得推广了京剧这一艺术。我爱听的通俗歌曲,我的孩子就不爱听。就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一样,一代人有一代人喜欢的音乐。我不相信现在的小孩会喜欢京剧,如果对这一判断有疑义,可以在学校做一下调查,看看到底有几个孩子喜欢京剧。小孩不喜欢的东西,靠强力推行,往往事与愿违,只会让孩子产生逆反。
一切都应该顺其自然。中国这么大,这么多人,总会有一些人喜欢京剧的。京剧作为艺术品种大家族中的一种,我相信不会断子绝孙,它会在少部分发烧友中流行,发烧。
国家在扶持动漫产业,因为动漫有广阔的市场。动漫更容易走进孩子的心灵。与其提倡京剧进课堂,不如提倡动漫进课堂。如果把一些可以动漫化的课本动漫化,提高孩子的学习兴趣,那真是善莫大焉。
京剧进课堂,肯定会受到学生的抵制,我相信过些日子就会不了了之;我说让动漫进课堂,虽然与国家扶持的产业政策相吻合,估计会受到家长的抵制。我们也来一个折中,我应该呼吁让科幻进课堂。
孩子是最有想象力的,想象力是创造的基础。在西方国家,课本中有不少科幻,这不仅是培养想象力的需要,也与孩子的身心发展想吻合。青少年而不会想象,在那里哼哼哈哈地唱京剧、读武侠,这样的民族有多大的希望?
什么时候,我们的课本中才会有科幻作品?我的中学时代,课本中是绝对没有选入科幻作品的,最近的初、高中课本也没有科幻作品。
有这样一种说法:中国有多少武侠,美国就有多少科幻。美国中学课本有很多科幻作品入选,有四百多所大学开设科幻课。有人指出,目前在我国的电视节目中,充斥着大量武侠片、皇宫秘史剧,相比较,科幻和科普节目却微乎其微。当美国的孩子们在《星球大战》之类的科幻片中长大时,我们的孩子们是在《笑傲江湖》一类的武侠片中成长。当发达国家的媒体为孩子们打开面向未来的想象大门时,我们的媒体却将孩子们封闭在几个世纪以前的紫禁城中。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熏陶出来的下一代,知识储备和兴趣倾向难免是偏向于过去而不是朝向未来。毫无疑问,中国孩子存在的缺乏想象力与创造力的现象,同整个文化背景缺乏科幻与科普的文化氛围不无关联。
在西方,当少男少女跨进中学、大学校门时,老师向新学生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往往是:一个没有幻想的民族,会有热情、希望和生机吗?老师对学生们说,愿我们的空气中弥漫着两种因子,一种是民主和自由,另一种就是幻想与创造。
早在上个世纪初,梁启超和鲁迅都鼓吹过科幻,他们或是创作,或是翻译,为中国科幻做了拓荒性的工作。科幻兴而科学兴。我们早已进入了科学时代。神舟飞船上载满了中国人的飞天梦,载满了中国人的科幻梦。我们最需要的不是种种崇古,而是科学的理性,是幻想、创新和创造。所以,我呼吁——应该让科幻作品走进学生的课本。
关于繁体字进课堂
我只知道宋祖英、郁钧剑们歌唱得凑合,没有想到他们对文字也这么热衷,或者说他们对所谓传统文化是这样偏爱!他们煞有介事地建议,小学要增设繁体字的教育。小学生课业负担重,本来就够烦的了,如果采纳了他们的建议,那真是烦上加繁!
学习文字是为了接受知识,传播知识,文字具有工具性。一般说来,工具越简单,越容易被接受。电脑也是一种文化,电脑是一年一年地进步着,电脑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操作越来越简单,正是越来越简单,所以越来越普及。我们不能说,为了弘扬电脑文化,我们在用奔五的同时,还要进行奔二的教育。过去的东西很多也就过去了,只要一些专业人士懂得的东西,不一定大家都要懂,更不必孩子都要懂。如果让现在所有的学生都去接受繁体字的教育,推到极致,学校应该进行甲骨文的教育了。
前些年,我在《参考消息》上不时看到这样的报道,香港人、台湾人如何地喜欢简体字。台湾和新加坡都有简体字的报纸。我接触过若干台湾人,也与他们通过信,他们也是简体字和繁体字夹用。说起理由,无非是写字快,方便。粉碎“四人帮”不久,大约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吧,国务院公布了第二批简化字,后来被废除了。作为编辑,我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很多人的书信还在使用第二批简化字,为什么呢?也无非是写字快,方便。
写一千个简体字,估计比写一千个繁体字要节省三分之一的时间,如果每一个写字的人累计起来,全国该节省多少时间啊!具体的个人学字,学一千个简体字,也要比学一千个繁体字快了许多。简体字在扫盲工作中,可谓立下汗马功劳,便是说头功也不为过。
字从复杂到简单,并不是在公布了简体字以后,文字是伴随着历史的进步越来越简单,内含越来越丰富的,最早的象形字有的简直就是一幅图画,先人们费尽了脑筋,才有今天这么简约、干净的文字。我们某些时代的歌者,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大旗,要把先人的智慧,要把无数文字工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果给抹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