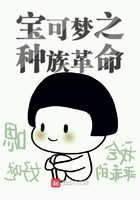皇帝要问仆人
场坊里移魂造梦酿酒也可以自杀
有时颓丧,如泥土坐地上
有时邈远,似林中藏丹房
我妈妈的手工艺术,荷花做得最好
我包裹自己,时而是赤子,可睡女人床
时而是鹤
老虎饿,人写作。
1、“昨天,我抚摸镜子,湖水起皱了/天去蓝而阴沉/我不敢,我敬畏稀饭”,开篇的这一段,我喜爱的无以复加。抚摸镜子,湖水却起皱了,一片心水。“去蓝”中,“去”的使用,是汉语的开阔与妖娆,用得极准确。“稀饭”对家常俗世的代入感极强,顿时抓住我的心。
2、寥寥语言,不间断的断裂,赋予这首诗巫言般的自由度与意蕴。《境》的主旨,是当下,是生命中的闷棍与灰烬。罗亮并非告你真理,他喋喋不休的向读者展示自身的脆弱,他不再是个战斗者或战败者,只是个受惊的人,如同你身边的任何一个委屈的街坊。
3、“老虎饿,人写作。”这种写作中的饥饿感,或生命的空泛,选择诗人用笔托出。老虎是个脆弱的纸老虎,我相信,罗亮并不抱什么光明的希望。无非,写作而已,达尔文已死,老虎也有饿死的一天。
《这几天老是想到孙武》
这几天老是想到孙武,奇正合依
及我楼下有一株歪脖子树
不用现世的语言,是因为我有羽翼
和立身之所
如何个死法?
如何解除昨日之烦忧?
人们一开始思考,楼下的歪脖子树
就会直立起来
孙武啊
虚无是一顶被风吹落在地的帽子
我坚持到老,到八十九岁
但树枝早断了
但马鞭,我已改成餐桌上一双上褐漆的筷箸
(2010.10.2)
1、我曾经写过一篇《一个虚无主义者的歪脖树》,所以读这篇,觉得极亲切。原来,是有血缘的。当然,罗亮对飞行和羽翼的偏爱,也和我一样。我把这首诗当做自己的私情。
2、《这几天老是想到孙武》,是关于难堪的重复,罗亮在个人化的臆想中,不惜抬出孙武救命,但救不了,兵法是大规模杀人的集成体,在如今是典籍,可以在文化讲坛宣讲,教育人民窝里斗,这分明与罗亮的理想相差十万八千里。所以,这首诗是荒谬的的,是怪诞美学,但罗亮发挥到极致,因为在结尾,一概归结为饭碗筷子间的拉扯,还是庸常事。
3、罗亮在这首诗中,始终是冷静的,他暴露的失败具有不可置疑的真实性,所以我阅读时才感觉荒谬。他的悲悯,具有一种伟大的自嘲意味,只要你懂他,就不会轻易落泪。
罗亮,是我在汤养宗之后,最为感到震撼的诗人。汤诗的气息运转和对汉语口语的突破性进化,足以击中读者的灵魂。而罗亮,则在暗黑中不断展览一个分裂者的心灵世界,他对军事和暴力的杂糅,只是汉语突围中的云梯,是工具。而作为一个具有惊人语言天赋的诗人,他沉得住气,内力深厚而绵长。
罗亮短诗中,结构的复杂多变,用极少的语言呈现广阔的心灵气场,叙述方式的多样化,死硬的汉语病句,构成他的诗歌世界。我愿意不断的进入他的诗歌体内,观赏一具尸首的咏叹调。
(2010-11-05)
2.痴孬傻呆
《瞬间III》
在春天,西红柿和一二两红酒。
但我又想到鲲鹏,东海,一小团乱麻
阴部,隐私,阴影;同父异母的三姐妹;一根快要断的钢丝
和失去作用的屠龙之术
人们逼我说出来的话,我说了
人们逼我做出来的活,我做了
(他们又是一对同父异母的鲁莽兄弟)
我不以为蠢
蠢是现在的特征
正如春,柿红,酒被斤两约束,梦见鲲鹏和东海
“在春天,西红柿和一二两红酒。”。春天春心荡,那就啃噬新鲜的西红柿,配以少许红酒。这样混中国的日子,也不错。
“但我又想到鲲鹏,东海,一小团乱麻”。这个罗亮,却去想鲲鹏,想念浩大的东海,与当下多么不搭调,所以出现一小团乱麻,并不奇怪。
“阴部,隐私,阴影;同父异母的三姐妹;一根快要断的钢丝/和失去作用的屠龙之术”。阴部隐私阴影的三词连用,加深了秘密的符咒。阴部是生殖与性的根源,隐私是内心翻腾,阴影是背对众人的臆想。这三姐妹血缘的复杂性,赋予诗歌多种样本的解读维度,一种交混的语言乱相。快要断的钢丝,实在是不起作用的,在这个堕落时代,其巨大腐蚀性何惧一根钢丝的硬度?至于屠龙之术,已失传,传人不见。
“人们逼我说出来的话,我说了/人们逼我做出来的活,我做了/(他们又是一对同父异母的鲁莽兄弟)”。诗人是软弱的,或者说人是软弱,在逼迫面前,硬汉不硬,选择屈从。“同父异母”再次得到强调,只是兄弟们更加鲁莽盲目,见不得天日。
“我不以为蠢/蠢是现在的特征”。作者不以为蠢,那是因为对智慧的认识,每个人都不同。“蠢”是当下,看来,亲爱的罗亮先生以后还想着翻本呢——也许是秋后算账,不要太乐观。
“正如春,柿红,酒被斤两约束,梦见鲲鹏和东海”。春的短暂与世俗的迷惑,西红柿的红只是蔬菜的生长,与被吃者无关,酒遭到粗暴的束缚。而这些鸡零狗碎,只为了诗人梦见鲲鹏与东海。
《瞬间III》的语言充溢着诗人的智性,对意象的把握具备高级的诗意和准确度,语言的交织凸显整体的概念,气场自由,语感保持着罕见的自信,几乎是自顾自的胡言乱语。这是我对语言和写作技术的看法,比如叙述的古怪——可是,这不是我最想说的话。阅读这首诗,还不是写作技术吸引我,而是罗亮反复提出的东海与鲲鹏,那种大志气、那种精神的交游、那种对宽阔与幅度的热爱,让汉家感动。不论同父异母、不论同母异父、不论春心荡漾,仅仅那份对东海不舍的情怀,就足以形成诗歌精神的穿刺,爆发恒久的力量。
罗先生,我等着你翻本的那一天。
《瞬间I》
有些人,从不这样做
有些人太多这样做,以至痴孬傻呆
繁星闪烁之夜,我推动小树
一株,三点,院外,城内,心中
我希望什么东西落下来,什么东西被晃动
非君,非士,非将,非色危者
非冠,非屣
非桃子,李子,瓜果;非妖,非妇人
我这样推动,由之,不自知
不自知,更由之
那些不现实的东西
那些不长久的东西
那些并不被正确命名的东西
那是一次独立的
机械运动,不撒娇,无色彩,像晃动
也不与你交流
“有些人,从不这样做/有些人太多这样做,以至痴孬傻呆”。做与不做,是分人了。人是有种类的,所以,我们难堪的发现,有太多的人痴孬傻呆,似乎没有解决的好法子。
“繁星闪烁之夜,我推动小树/一株,三点,院外,城内,心中”。繁星的夜晚是诗意的,诗人推动小树,院外城内心中,还在发育的这株小东西!
“我希望什么东西落下来,什么东西被晃动/非君,非士,非将,非色危者/非冠,非屣/非桃子,李子,瓜果;非妖,非妇人”。作者是有希望的,或者推动一个结果,这个结果不是等等等等事物,甚至不是美妇人。那么是什么?
“我这样推动,由之,不自知/不自知,更由之”。这样的推动,是“由之”的力量使然,诗人被内心的惯性驱使,被诗意的繁殖驱使,长驱直入。
“那些不现实的东西/那些不长久的东西/那些并不被正确命名的东西/那是一次独立的/机械运动,不撒娇,无色彩,像晃动/也不与你交流”。那些不现实的,是飞行的。那些不长久的,是脆弱的。那些不被正确命名的,是屈辱的。那是一次独立的机械远动,没有与时代撒娇,无斑斓的喜庆色彩,像晃动——如果你眼神不好的话,会觉得不真实。而不与你交流,是内心的抵抗,或自成一体的自治。
《瞬间I》的语言歧义性更甚,解读这样的作品,还不是智慧的问题,而是能否进入那条专属罗亮的诗性通道。总的来看,这首诗是关于抵抗和寻找的,但不止如此简单,对于被拒绝的和留下的,并未附加道德和价值判断,诗人也在诗行中流露出自我的不自觉。从语言进入,《瞬间I》的语义层层递进,直到最后形成一个关口,释放压抑的内在。我读这首诗,最直接感受是罗亮所袒露的真实,一种迷惑般的真实打动了我。他不屑于答案,我相信他通晓了其中的一部分,但还有相当多的另一部分,他仍是困惑的,并不自觉——就是这种语言的迷惑性和对自我怀疑的袒露,形成《瞬间I》强大的精神力。
罗先生,痴孬傻呆是常见的,我们都沾染过此类病菌,这也是美学的一部分。
(2010-10-27)
3.他不是语言黑社会的头子
《扎头巾的乌鸦》
那些乌鸦,扎着头巾
驴们清闲,吃着切细的青草
小云雀,穿过雨
一个人在房间里挥汗如雨
追赶一只兔子
摇着赌注、零钱和左腮
孤独的球被从窗口扔出
抑或一只鸟?
它们是什么?飞机,钢琴,铅笔
——有什么不同?我一声断喝
操场空旷,港口上
物资堆积
女人FOLLOW,顺从,默认,暗许
放弃思想,情感,尊严和手袋
这些易导致歇斯底里的光亮物
穿着豹皮,阳光直晒皮肤
看到这---乌鸦,驴,云雀,兔子和孤独的
一只球
飞机,钢琴,铅笔
操场,港口,人类的美德
没有污染的字母P,曲线L或S和发音a
“那些乌鸦,扎着头巾/驴们清闲,吃着切细的青草/小云雀,穿过雨/一个人在房间里挥汗如雨/追赶一只兔子”。乌鸦扎起头巾,是伪装,这个不祥的乌鸦居然伪装自己的身份,用意歹毒啊。还是驴子清闲,一副清高的样子,不问世事,也不劳动,吃着人类送上的青草,那份清幽羡慕死人了。小云雀是倒霉的,刚发育好,就要穿过雨,淋湿羽毛。一个人在房间流着汗,追赶一只兔子,这是怪诞的画面,莫名其妙的词语寂寞。
“摇着赌注、零钱和左腮/孤独的球被从窗口扔出/抑或一只鸟?/它们是什么?飞机,钢琴,铅笔/——有什么不同?我一声断喝/操场空旷,港口上/物资堆积”。赌注是生命的常态,零钱是怡情,左腮需要思考。孤独的球被扔弃,还是一只鸟呢?球与鸟都是美丽的事物,却结局不妙。而它们是什么?飞机与铅笔与钢笔有什么不同?这是洛特雷阿蒙的雨伞和缝纫机般的相遇吗?还是笔可以画出蓝天,与飞机所处的境况相一致?诗人一声断喝,操场全然空旷,孤独的,无人在场。港口上,物资却堆积,形成强烈的对比。
“女人FOLLOW,顺从,默认,暗许/放弃思想,情感,尊严和手袋/这些易导致歇斯底里的光亮物/穿着豹皮,阳光直晒皮肤”。女人FOLLOW,缠着不放。顺从、默许和暗许,关乎情感的纠结。放弃——又是放弃,放弃的思想、情感、尊严和手袋,这些容易导致歇斯底里的光亮物。罗亮在这里俨然是清醒的,思想的深入、情感的执着、尊严的放大和手袋内的秘密,将导致危险的分裂与伤害。而身披的豹皮,是裸露的,阳光不讲理的晒着,哪管你的凉热。
“看到这——乌鸦,驴,云雀,兔子和孤独的/一只球/飞机,钢琴,铅笔/操场,港口,人类的美德/没有污染的字母P,曲线L或S和发音a”。乌鸦,驴,云雀,兔子,这几只小动物再次回到诗歌中。孤独的球和飞机、钢琴、铅笔、操场、港口,貌似热闹的词语重新集合,这种景象却更加令读者感到孤独。“人类的美德”如同硬插进来的理性,显得突兀而生硬,但有力量,使读者的大脑不得一刻休息。没有污染的字母P、曲线L或S和发音a,作为最后的强音予以定格,这是幻想中语言道德的一次胜利。
《扎头巾的乌鸦》完全是一首有预谋的作品,是一个精心设置的语言陷阱。开篇就是词语的迷宫,和不着调的意象组合。罗亮在这里进行的不是词语混搭的问题,而是乱搭,由着自己的性子乱来一气。读者在阅读这首诗的时候,是痛苦的,你不知道诗人的葫芦里到底买着什么药。小动物间模糊的指向,女人的介入,平白无故插入的英文,显得生硬而直接。诗歌结尾处的重复与强调,如同病人的唠叨,分外可厌。只是人类的美德,在于没有被污染的字母,那P、L、S和a,通过曲线与发音,印证了词语最初的纯洁,如处子一般。我非常喜欢这首诗歌,如此怪诞的词语组织,不惜毁灭常规文本的内在架构,和突出的对语言本源的赞美,都高调到无以复加。
难道词语的源头,一个个纯洁的字母还完好如初吗?我认定被强奸的占绝大多数,但被珍藏的那些依然存在,罗亮保护着她们,还好,他不是语言黑社会的头子。
(2010-10-27)
4.并置的奇观
《夜晚》
夜晚,一切都熟睡了
只有针睁着一只眼,插在它如麻的往事里
而红木家具,贯耳瓷瓶熟睡了
有着富裕的安逸
有人来回走动
拖着忧悒的狐狸的尾巴和阴影
有人在窗口吞食蓝色药片,有人了望大海
这是个分裂的季节
可以好,这么好;也可以
坏,且
很坏
“夜晚,一切都熟睡了/只有针睁着一只眼,插在它如麻的往事里/而红木家具,贯耳瓷瓶熟睡了/有着富裕的安逸”。夜,睡着了,人就没了心肝。只有针睁着一只眼,插在麻团似的往事里。“针”的使用,具有尖刺的快感,已是惊艳。而“睁着一只眼”,对针眼的词语置换,则大胆得令读者心头颤抖。麻团与针刺,往事不提也罢。而红木家具,贯耳瓷瓶也照例熟睡,如富人的睡眠,安逸,年头方长。
“有人来回走动/拖着忧悒的狐狸的尾巴和阴影/有人在窗口吞食蓝色药片,有人了望大海”。有人来回走动,拖着忧悒的狐狸尾巴和阴影,这是软性的人类黑暗。有人在窗口吞食蓝色药片,应该是伟哥,他的背后也许是一个年青的女性肉体,叉开大腿。有人了望大海,这个人在深夜望海,宽阔与翻腾笼罩了他。
“这是个分裂的季节/可以好,这么好;也可以/坏,且/很坏”。这是个分裂的季节,可以好,好到“这么好”,也可以坏,坏到“坏,且很坏”。
《夜晚》在罗亮的诗歌序列中,是一首易读的作品,与他大量晦涩,具有颠覆色彩的诗作相比,《夜晚》直白得可爱。诗人都是高智商的人,罗亮写出的这首诗,摆脱了语言的精深与乱来,是因为他想给读者一个清晰的口信。这个口信越清晰越好,它能准确传达出诗人对核心问题的思考,类似“分裂”这样的主题,是罗亮诗歌中常见的思考与折磨,这是诗人对人性世事的根本判断。
这首诗中,一些细节的处理,体现出诗人超常的语言功力,如“一只眼”、“这么好”等,汉语关键部件的运用准确无误,可以瞬间抠住读者的眼球。坏的,是够坏的,且很坏,烂掉就烂掉。而好的,如罗亮诗中所言,是这么好,好到难以自持。
《复议》
在董事会室,水神留了下来
他递给我一张涂鸦,他三岁女儿的,说:“这个您看看,她三岁了。”
“很好。”我说,“请鼓风三级。”
关于公司蓝图
多年来令我忧思,殚精竭虑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
我们向何处去
感谢水神,感谢水神三岁的幼女
她用一只胖胖的熊指点了迷津
她是群英会的一员,扎上辫子,可以坐上我们这帮峨冠高戴的人群之主席
“在董事会室,水神留了下来/他递给我一张涂鸦,他三岁女儿的,说:”这个您看看,她三岁了。“/”很好。“我说,”请鼓风三级。一间企业董事会室?这和诗歌有什么关系?水神留了下来。由“董事会室”到“水神”之间的过渡,语言自然,如同叙述一件正常的生活场景。“水神”对应的“办公室”,犹如从现实主义强行拉到神秘主义的山林。他递给我一张涂鸦,是三岁的女儿,他说这个您看看,她三岁了。“我”说:很好,请鼓风三级。这首的开篇,是类似小说的叙述,“水神”的进入,带给读者魔幻般的阅读感受。“我”的话:“请鼓风三级。”如同玉皇大帝般的口气,天下随之震动,“鼓风”被赋予神奇的情绪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