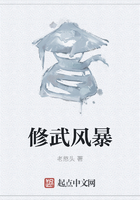——[法国]福楼拜
它是一只鹦鹉,名叫鹭鹭。它有一个绿色的身体,还有一对玫瑰色的翅膀尖,再加上碧蓝的前额,配着一个金色的颈脖,真是标志极了。
可是,它有一种令人讨厌的怪癖。它不停地咬木架,拨羽毛,满地撒粪,将小杯子的水弄得到处都是。欧班夫人讨厌它了,把它给了费莉西泰。
费莉西泰开始教它说话。不久,它学会说:“乖孩子!——先生,为您效劳!——玛丽,敬礼!”它被关在笼子里,挂在大门边,经过的人,叫它雅各,它不理不睬,因为它叫鹭鹭,它不喜用雅各这个名字。有人说它像只火鸡,又有人把它比作一根木头,这些比喻令它的主人费莉西泰伤透了心!但鹭鹭却很冷静,只要有人盯着它看,它就不说一句话了。
它喜欢热闹。每逢星期天,“那几位”洛许弗叶小姐和德·乌普维尔先生等老朋友,以及药剂师翁弗阿·瓦兰先生、马提安上尉等几位新客来家里打牌的时候,它就兴奋地乱飞乱跳,用翅膀扑打玻璃窗,弄得屋子里闹哄哄的,以至于听不清客人们的谈话。
有一天,费莉西泰把鹭鹭的笼子放到草地上呼吸新鲜空气。她因为有事离开了一会儿,但等她回来的时候,鹭鹭已经不见了!她先到灌木丛里寻,又到河边和屋顶上找。女主人朝着她喊:“你瞧自己都干了什么呀!你这个蠢货!”她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她查遍了主教桥所有的花园,拦住过往的行人打听:“您看见我的鹦鹉了吗?”有的人从来没有见过它,她就绘声绘色地描述一番。忽然,她恍惚看到磨坊后面的小山坡下,有一团绿色的东西在那里飞舞。她急急的赶了过去,却什么也没有看到!一个小贩对她说,刚才他在圣梅兰的西蒙大妈的杂货铺里看到过它。她跑去一问,人家说根本没那回事。她没有办法,精疲力尽地走了回来。她伤心欲绝,鞋底也磨破了。她在夫人身边的一条凳子上坐下,向她诉说寻找的经过。忽然,她觉得有件东西轻轻地落到她的肩上:鹭鹭!怎么是你?它干什么去啦?是到附近散步了吗?
然而,她没能从这次事件中恢复过来,或者换句话说,从此她就一蹶不振了。
接着,她着了凉,患了喉炎;不久她的耳朵也出了毛病。又过了三年,她聋了;她开始大声地说话,甚至在教堂里也是如此。即使她忏悔的罪过即便传到教区的每个角落,也不会有损于她的名誉,对旁人也没有什么妨碍。可是教学牧师还是认为,到圣器室里听她的忏悔更加合适。
她整天心神不定,为此,女主人经常责备她:“上帝呀!你真是个笨蛋!”她回答说:“对极了,夫人。”同时,还在身旁不知找些什么。
她的思想范围本来就很狭窄,现在就愈来愈窄了。那悦耳的钟声和牛的叫声也听不见了。所有大自然的、美妙的、难听的声音,她都听不到了。谢天谢地,她还能够听到一种声音,那就是鹭鹭的叫声。
也许是为她解闷吧,它常常学着闹钟转动的滴答声、卖鱼人的尖叫声、对门木匠的拉锯声;一听见门铃响,它就学着欧班夫人的腔调说:“费莉西泰,快去开门!开门!”
她和鹭鹭倒是有话可谈的。鹭鹭不厌其烦地卖弄它那三句陈词滥调,而她总是回答一些无头无尾的、但感情丰富的句子。鹭鹭在她孤苦伶仃的生活中,几乎成了她的儿子,她的情人。它攀着她的手指头爬,它轻轻地咬她的嘴唇,它在她的披肩上荡秋千;有时候,她额头朝前,摇着头,像奶妈逗婴儿一样逗它。这时,她的大帽檐和鸟的翅膀就一齐扇动起来。
每当乌云密布,雷声隆隆时,鹭鹭就尖声高叫,也许是想起了故乡的雷阵雨吧。雨水流淌,也能激发起它的狂热,于是它像个疯子似地飞向天花板,撞翻屋子里的东西,又从窗户飞出去,到花园里去淋雨;不过它很快就飞回来,停到壁炉的柴架上。它停在那里,一会儿展展尾巴,一会儿伸伸脖子,扑腾扑腾地抖掉身上的雨水。
由于天冷,她把鹭鹭放在壁炉前面。一天早晨,她发现鹭鹭耷拉着脑袋,爪子攀在铁丝上,已经死在笼子里了。它也许是死于充血。可是她认为,它是中了香芹菜的毒。她虽然拿不出任何证据,但还是觉得自己把它给害了。
她哭得一塌糊涂,女主人安慰她说:“好啦!别哭,要不为它举行个葬礼仪式吧!”
当地面的白雪像美丽的钻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或者当挂在树梢的冰凌组成神奇的连拱和无法描绘的水晶的花彩时,还有什么东西能与白雪相媲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