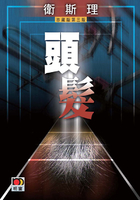——[美国]爱伦·坡
靠近年终,天越发黑暗起来,乌云压顶。我就在这样的一天,骑着马在乡村公路上前行着。夜幕降临时,厄舍庄园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我在庄园旁边的寂静昏暗的湖边下马。湖水映出庄园及其四周树木的倒影,黑乎乎一片。倒影中有些东西使我感到害怕,尽管我说不清那是什么。
我仰起脸,看了看这座老房子,房子是由石头砌成的。房子的正面好像有一道裂缝,从墙顶向下一直延伸到水边,消失在黑色的湖水中。
我这次来,主要是冲着我儿时的伙伴罗德里·厄舍来的,我们已经有好些年没有见面了,他的情况我也所知不多。但是,他最近给我写了封信,要我到这里来。我的朋友会见我的那个房间黑漆漆的,但是我还是感觉到了他的巨大变化。他病恹恹的,而且目光中透露出一种狂乱的神情。他神色慌张,常常忙活一阵,随后便突然安静下来。他对我说,他患了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
依我看,最为严重的是,他充满了恐惧,甚至对房子也表现出一种不可抑制的恐惧。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座房子主宰了他的思想。恐惧已经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在所有的事情中,他最怕的就是死。他说,他的妹妹梅德琳快要死了,他将成为他家里最后一个人了。他害怕在她离世后孤独地死去。
梅德琳也住在这座房子里,但在她死之前,我与她仅仅见过一面,话也未曾说过,那时我看到她慢慢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去了。
在厄舍告诉我他妹妹死亡的有关情况之前,我们一直在研究一本很怪异的书,这本书是在某个被遗忘的教堂发现的。书上讲述了一种叫做“守望死者”的习俗。
在梅德琳死后的一天,厄舍突然告诉我,他不准备即刻埋葬他妹妹。也许由于神经错乱,他打算亲自守望死者!不过,他对自己作出的决定给我说了两条充足的理由:首先她被埋葬的地方距离很远;其次,她的病非同寻常,大夫可能会在她下葬之前寻问有关问题。于是,我和厄舍将她的遗体抬到了楼下的一个小房间里。她穿着雪白的长礼服静静地躺在冰冷的石板上。锁上门后,我和厄舍转身离去了。
从此,我的朋友越发变得古怪了。他的一举一动、一呼一吸都带着恐惧。我也变得恐惧起来。甚至整座房子都使我心惊肉跳。
一周的时间转眼过去了,有一天夜里,突然狂风大作,令人毛骨悚然。但风停时,我却仍能听到那声音。我也弄不清那声音是哪里发出来的,但我心里很害怕。
在这个狂风肆虐的夜里,厄舍敲开了我的房门。“你没看到它吧?”他问我。他打开窗户,风呼地卷了进来。他野人似地仰望着夜空。他似乎看到了我无法看到的东西。
“快把窗户关上吧!”我说,“天气太冷。这有一本书,我读给你听,让我们一块儿来度过这个恐怖之夜。”
这本书一点儿意思也没有,但是除此之外,我没有第二本书。我开始给厄舍读了起来。“有人拉倒了门,发出木头破裂的声音。”我猛地停止朗读。我仿佛听到房里什么地方响起了同样的声音。我对自己说这是风在吼。书中的故事已经使我注意到了这一点。
我又接着给厄舍读下去,故事中,那人闯进房里,发现房里有一只大动物。他击打那只动物,它大声叫唤起来。我又一次停了下来,因为我又听到了和故事中相同的声音。我看了看我的朋友,他似乎快要睡着了。“那些声音真的存在吗?”我问自己,停了一会儿,我又读了起来。故事中,一大块铁掉在了地板上。我一读到这句话,就听到我们下边什么地方发出如同铁掉在地板上的声音。
我一下子跳了起来。厄舍仍然坐在椅子上,他向两边慢慢地动了动。他没有看我。突然,他开始说话了,不过,他不是对我说话,而是在自言自语。
“听,那声音,我听见了,真的,很久很久以前,我就已经听见了。但是,我不能说。我们是把她活着锁起来的!很久了,我就听到了她的动静,我好害怕!就像书中的故事一样。那些声音就是她发出的。啊!我该去哪儿呀?她会问我为什么要那么快就把她放在那儿。她现在就要来了。我听见她上楼的脚步声了。我听到她咚咚的心跳声了!”
突然,他从椅子上跳起来,大声喊道:“我告诉你,她现在就站在那边!”
厄舍说着将手指向我的房门口。这时,门慢慢地打开了。初时,我以为门是被风吹开的,哪知,我看到有个人站在门口。是梅德琳·厄舍。她的雪白的礼服上血迹斑斑。她一定是从楼下锁着的房里出来时把自己弄伤了。
她在门口站了片刻,随后开始向门里走来。最后,她气息奄奄地倒在她哥哥的身上。他们兄妹是一起倒地的,厄舍因惊吓而死。
我冲出房间,冲进暴风与黑暗中。而后,我看到我脚下的地上有一道奇异的光在闪烁着。我转过身想看一下那道光来自什么地方,因为房里昏黑一片。一轮血红的满月破云欲出,悬在空中。我看清楚这道光是透过房子墙壁裂缝射过来的,我第一次看到房子时那道裂缝很小,但现在显然加宽了。在我看它的时候,它还在变宽。转眼之间,狂风骤起,一轮满月和盘托出。房子的四壁正在倾倒。随之而来的是巨浪怒涛的声音——我脚边的黑色的深湖静静地、不可阻挡地将厄舍庄园揽在了自己的怀抱里。
一对美国夫妇住在一个海边小旅馆里。一个雨天,妻子发现窗外一只在躲雨的小猫,出去却没有找到。正当妻子大失所望之际,猫却出现在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