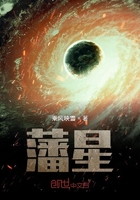夏笙寒愣在了原地,本以为这是什么感人的重逢,哪晓得她一个石头砸了上来,连忙侧身一避;她却毫不气馁,一把抹干眼泪,又拾起一块砸来。
片刻之后,傅茗渊几乎将脚边能举得动的石头都扔了过去,而阿寻和那老妇正站在一旁看。少年的脸上满是惶恐,根本不知发生了什么,嘴巴张得老大。
“矮子……。”夏笙寒一边躲闪一边求饶道,“要是砸中了残废了怎么办?”
“那正好。”傅茗渊冷冷地回道,“残废了就跑不了了。”
“……。”
言罢,她缓缓向着他走了过去,分明是如此陌生的装束,却熟悉到令她鼻尖发酸:“谁准许你不告而别的?”
夏笙寒微微一怔,徐徐放下了手,默然背过身去:“你走罢。”
“……?”傅茗渊不可置信地望着他,顿住了步伐,“你说……什么?”
“我说,你走罢。”他咬字极为缓慢,重复了一遍,“你也看出这是苗人的地方,他们不欢迎外人。”
“外人?”她的手甚至有些发抖,“对你而言……我是外人?”
这一回,夏笙寒并未作答,只是推开了屋门,重又走了进去。傅茗渊的目光紧锁在他的背影上,直到他关上门才回过神来,想也不想地冲了过去。
“请回罢。”
她尚未靠近,忽然有人伸手挡住了她,正是阿寻的奶奶,披着长长的斗篷,独特的帽檐之下是一张饱经沧桑的脸,看装束似乎是寨中的蛊婆。
“我找他有事。”傅茗渊咬着唇道。
蛊婆摇摇头,似乎叹了口气:“他不会跟你走的。”
“为什么?”傅茗渊猛然看向她,“他住在这里多久了?为什么不能跟我走?”
听到她的质问,蛊婆只是摇了摇头,似是在叹气:“阿寻,送客。”
阿寻立即应声点头,走到傅茗渊的面前,示意要将她带走,而她却迟迟不肯动,面向那扇紧闭的屋门,叫道:“如果你完全不想看到我,可以直接告诉阿寻不准带我过来……可是你没有这样做,不是么?”
屋内寂静如死,无人回答。
“我曾经不止一次以为你死了,我甚至都设想过如果真的找到你的尸体我要怎么办。”她闭上了双眼,哽咽道,“既然你还活得好好的,有什么解药……我们不能一起去找?”
说到最后,她的眼眶不觉又红了,连阿寻也不敢再催促她走。
尽管伪装得很好,这半年来她始终很心慌。她习惯去估量每件事,思考最坏的结果,以不变应万变;然而每每设想如此的结局,都会令自己心有余悸。
然而,夏笙寒始终没有出声。
像是料到了这个结果,傅茗渊捂住了双眼,深吸几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一睁眼,瞧见蛊婆正捧着一个罐子站在她面前,似乎是有些不忍心,叹道:“他不肯离开,是因为他身上所中的蛊,只有老身可以解。”
“……蛊?”傅茗渊心里忽而咯噔了一下,不可思议道,“他不是中剧毒了么?”
“剧毒?”蛊婆摇摇头道,“他所中的乃是苗疆罕见的阴蛊,阴寒至极,在他身体里潜伏了好几个年头;还好他的身体还算强壮,若是换个身子骨弱的,恐怕根本撑不下去,可惜……。”
她说到一半忽然停了一下,似乎是隐瞒了什么;傅茗渊却未在意她话尾的停顿,惊愕道:“好……好几年?!不可能,他在通州中毒分明是去年的事,怎么可能已经过了好几年?!”
蛊婆疑惑地望了望她,像是想起了什么,道:“这阴蛊在他的身体里起码呆了五个年头,一直在沉睡,直到去年他中了剧毒,才开始侵蚀他的身体;那剧毒已经解了,可是这蛊却……。”
傅茗渊恍然大悟地捂住嘴巴。
如果不是那次在通州被豫王下的蛊,而是在几年之前,难道夏笙寒……早早地就被朝中的某个人盯上了?!
“不……不可能。”一时间,种种猜测令她几乎要窒息,烦闷地扶着额头,“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他先前一点反应都没有?”
“或许只是你没有注意到罢了。”蛊婆耸耸肩道,“要解开阴蛊很难,要对人种****蛊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须得做得神不知鬼不觉,也只能是身边之人。”
“……身边之人?”傅茗渊一怔,“阿寒的亲卫在十多年前就解散了,剩下的便是……。”
不,严公公从夏笙寒儿时起就在他身边,无需等这么久;那这般说来,除了她以外,也只有……
陛下?
她被自己的猜测吓到了,连忙甩了甩脑袋,追问道:“那这阴蛊……要怎么才能解开?”
蛊婆顿了顿,有些无奈地摊开手,缓缓走回屋子:“办法是有,只是……他不愿意罢了。”
“为什么不愿意?”
蛊婆没有回答,只是进屋后将门带上,浑浊的目光有些复杂:“因为成功的几率……只有一成。”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只有稀疏的阳光照进了小屋,显得苍凉沉寂。屋中的摆设朴素简单,却处处洋溢着苗人特有的气息。
这座寨子大约是很久以前便建在秣陵附近的,没有受到洪灾的影响,居民都是土生土长在此地,除却装束之外,生活上大多融入了延国的习惯。
夏笙寒是在去年入冬之前找到这里的,他本是决定回秣陵一趟便离开,谁知却因阴蛊的发作而倒在了城外,恰好被路过的阿寻看到,以为他是流浪至此,遂找人将他带了回去。
阿寻的奶奶是寨中的长老,通晓所有的苗疆蛊毒,很快看出了他身上的不寻常,为他解了当初豫王所下之毒,然而对于阴蛊却产生了迟疑。
“想要解开阴蛊也不是不可能,需要的介质老身也能全部找到,只是……。”
“只是什么?”他抬头问。
不管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只要能解开阴蛊,他就能回到那个属于他的地方,回到她的身边。
蛊婆凝视着他粲然的双眸,神色愈发凝重,“阴蛊在你体内潜伏多年,老身只有一成的把握能帮你解开,但倘若失败了……。”
夏笙寒的心突然拎了一下,“失败了会如何?”
“倘若失败了,你会死无全尸,甚至可能……化为一滩血水。”
“……。”他沉默了许久,“那如果……不解开呢?”
“如果不解开,你很快就会死。”见他从满怀希望转为了失望直至绝望,蛊婆叹息道,“阴蛊随你而生,随你而死;待你死后,它也会不复存在。”
夏笙寒的喉头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却又无法开口。这段时间以来,他每晚都要受到钻心一般的煎熬,不知究竟还能撑多久;眼看着希望就在眼前,却永远只差那么一步。
“也就是说,如果不解开阴蛊,至少我还能留个全尸?”他自嘲似的笑了笑,“那我不要了;如果死得太难看,矮子会不高兴的。”
蛊婆有些惊讶,却欲言又止。
夏笙寒收回思绪,转头看向了桌上的药酒,不知为何叹了口气。
从前是那么喜欢喝酒的人,可如今为了延长寿命喝了半年的药酒,几乎是到了看见就烦的地步。他无奈地叹了口气,正欲倒出一杯,却惊觉屋门被人踹了开来;一抬头,是傅茗渊收回脚闯进来,阿寻在门外哭着阻拦。
“呜呜呜大人啊……这门是要钱的啊!”
傅茗渊闻而不应,“啪”地将门关上,走近后一把抓住了夏笙寒的手,作势便要将他拖向门外:“跟我走,去解开阴蛊。”
“不要。”他条件反射似的将袖子抽了出来,向后退了一步,嘟囔道,“我不要你了,你走吧。”
“如果不将阴蛊解开,你真的只有一个月的寿命了!”傅茗渊急得几欲落泪,“我不想看着你死!”
夏笙寒默了默,从袖子里掏出一个骰子,捏在她面前:“你知道什么叫作‘一成’么?”
他说着将骰子掷在了桌上,旋转的声音在此刻显得尤为刺耳,少顷后停了下来,最上面的是一个“四”。
“刚才我心里想掷的是‘六’。”他耸肩笑笑,“一成的几率,比这个还要低许多。”
傅茗渊怔怔地望着他,一时竟说不出话来,泪水终于止不住流下,心中的无力感几乎要将她吞没。
方才蛊婆将实情全部告诉了她,最后无可奈何地叹道:“先前他说他有个妻子,不想让妻子看到他死无全尸的模样;大约说的……就是你罢。”
“听说你是和云沐一起来的,所以我准备了好多炮仗。”夏笙寒专心致志地坐在桌上玩骰子,“可是我还是忍住卖掉了,剩下的阿寻拿去玩了。”
傅茗渊像没听见似的,仍然道:“如果你去试试,那好歹还有一成的几率;如果你不去,难道你想让我看着你死么?”
“谁告诉你我要死了?”他突然站了起来,伸手将她往外推,“那是阿婆骗你的,她只是想把你赶走,因为你太矮了,影响寨子的形象。”
“……。”她无心理会他是不是又发疯了,死死地拽住他的手不肯走,泪水“啪嗒啪嗒”地落下,而夏笙寒却只是顿了一下,继而像没看见一般,依旧将她往外推。
“其实那位云大人人还不错,再者你本来就喜欢他。”他的声音平静到觉察不出任何情绪,“等你以后不想当官了,嫁给他也好。”
听到这句话,傅茗渊突然抬起手,死死地扣在他的掌心,像是用了全身的力气握住他的手,气到满脸涨红,连嗓音也在颤抖:“你管不着……。”
她一字一顿,每一个字都像针似的扎在他的心上,却又令他感到庆幸。
“对,我管不着,所以你去找云……。”
“我以后要怎么样,我要嫁给谁,你都管不着……。”傅茗渊打断了他的话,猛地抬头望他,一把揪起他的领子,“这是我自己的事。”
她的目光坚决到有些可怕,倏然松开了抓着他的手,用力在他胸口一推;夏笙寒猝不及防,没料到这一动作,整个人被她推倒在了地上,连带着她一起,“嘭”地摔了下去。
傅茗渊趴在他的身上,因方才扯着他的衣襟而一道摔下,却固执地死也不肯站起来,直直地凝视着他的眼。
“矮子,起来。”
夏笙寒拍了拍她的肩,注意到她的脸颊不自然地发红,尚未反应过来,唇上却忽而被她啄了一下,登时愣住了。
她的双唇是柔软而香甜的,极为紧张地揪着他的领口,笨拙地亲了上来,面庞红得要滴血,可神色却是那般毅然决然。
“你……。”他慌忙握住她的双肩,不让她再乱动,霍然发觉在连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时候,喉咙变得如此干涩,连理智都在被逐渐消磨,“别……动。”
“你管不着。”傅茗渊紧咬着双唇,挣扎着摁住了他的手,伸出纤瘦的胳膊将他的衣服用力一扯,缓缓垂下头来,学着他曾经的样子,在他耳边轻轻啄了一下。
“你不是想要宝宝么?我……现在就送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