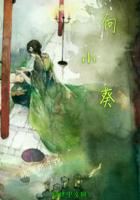这是不是那种带有稚气的天真无邪?不是的,主,这不是。主啊,我祈求你宽恕。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离开了伴读的人和老师,我们也不再爱坚果、弹子、小鸟了,而君主和王公、以及黄金、奴隶和采邑的大厦都是根据相同的原因而得来的。这种小孩的游戏随年月而消逝,正象跟在老师戒尺后面的却是更大的惩罚一样。所以,你,我们的主,你曾赞许儿童时期身材矮小是谦逊的特征,你说过,“天国属于这样的人。”
第三卷 第四章 杜莱的霍顿西尼斯怎样激发他学哲学
在我幼年的狂妄友伴当中,我学习了有关雄辩的书籍。为了达到可恶的虚荣的目的,加上人人怀有的对于光荣的喜悦,我妄想出人头地。在日常功课里,我仔细阅读了西赛罗的着作。差不多人人欣赏他的词藻,却不领会他的思想。他的这本书劝人学习哲学,书名叫做《霍顿西尼斯》(Hortensius)。这本书大大地改变了我的心理状态,使我向你,主啊,祷告,而且使我们的希望和志愿彻底改变。我的虚空的希望从此减轻,而且我以难以相信的热忱,向往着不朽的智慧。我因而振奋起来,又开始转向着你。我钻研这本书,不再着眼于辞令。我用我母亲给我的学费来买这本书。那时我十九岁,父亲去世已经两年了。我说我没有用这本书来磨练我的口才,这本书吸引我的已不是它里面的优美文字,影响我的是它的内容。
我的天主,我多么渴望摆脱人间的乐趣,飞向你的身边,可是我还不知道你对我作出什么安排,因为智慧是属于你的。爱好智慧,在希腊文里叫做哲学。西塞罗的那本书就是凭哲学激动了我。有人假借一个伟大、动人、高尚的名义来粉饰他们自己的谬说,假借哲学的名义诱惑他人。当代和以前时代的这一类人在那本书里几乎都受到责难,一个不漏。那本书里还有你,善良忠心的仆人,把你--圣灵,最为有益的劝告讲得清清楚楚:“你们应当小心,不可让任何人利用哲学和虚妄的诈行来毁坏你,这种只是合乎人们的传统和人世的经纶,不合乎基督,而天主的神性却有形有体地全部寓于基督之身。”
就我说来,你是你心中的光,你知道那时候我不大知道使徒信经。但是《霍顿西尼斯》里的那篇劝学的文章令我喜悦,因为它不要我归属于这个或者那个宗派,而让我自由地热爱、追求、获得、坚持并且遵奉智慧本身,不管智慧是什么。就是那本书偶然使我发奋激动,热情高涨,但是有件事情使我在热情高涨的时候不再爱看那本书,那就是书上没有提到基督的名字。按照你的恩惠,主啊,我的救主,这个圣名--你的“圣子”的圣名,在我哺乳之时即被我的童心所虔诚接受、深深蕴蓄于心坎中,所以,不管什么书籍,如果没有提到那个圣名,不论内容如何翔实,文辞如何雅典,根本就不会得到我的赞赏。
西塞罗的哲学论文之一,原书已遗失。
第五章 他轻视圣经,因其文体平易
我因此决心研读圣经,探求它的内容。但是看啊,我发现圣经里有些东西是骄傲的人见不到的,是儿童懂不了的,入门时觉得隘陋,越朝前越觉得高深,它整个地笼罩在神秘的帷幕之下。我那时还不能透彻理解其含义,也不能俯首虚心,唯其命以是从。我聚精会神,研读圣经,那时我所认识到的还不是我现在所说的,我那时认为圣经远远不及西塞罗的雄辩着作典雅庄重。我那时骄傲非凡,盛气凌人,不能理解圣经的文体与格调,我那时的才智也不能体会圣经的义理。
可是圣经的意义随孩子的年龄而与日俱增。但是我很不愿被人当作孩子,骄傲自大,自以为是个什么伟大的人物。
第九卷 第八章 关于女子教育
我的母亲除了追怀她生身之母勤劳抚育之外,更称道一位老年保姆对她的尽心教导。我的外祖父小时候已由这个女子带领长大,一如姑娘们惯常背负着孩子。因此这个教友家庭中,主人们对这位赤胆忠心的老妇人都很尊重,所有的女孩子都托她管教,她便尽心照顾,必要时用神圣的严规约束她们,而寻常教导她们时也是周详审慎。
除了女孩子们和父母同桌进用极俭朴的三餐外,为了不纵容她们沾染不良的习惯,即使极感口渴、也不许她们随便喝水,对她们发出极合情理的告诫:“现在你们只喝清水,因为没有办法喝到酒;将来你们出嫁后,成为伙食储藏室的主妇,会觉得清水淡而无味,取酒而饮便会成为习惯。”她这样一面开导,一面监督,禁住了孩童的饕餮,而女孩子们对饮水也就有合理的节制,哪里更会有不合体统的嗜好?
事虽如此,但我母亲仍然渐有酒的爱好。这是你的婢女亲口告诉自己的儿子的。她的父母见她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女孩子,往往叫她从酒桶中取酒。她把酒杯从桶口去舀,在注入酒瓶之前,先用舌头舔上一舔,并不多喝,因为她并不想喝。她所以如此,不是为了嗜酒,而是出于孩子的稚气,喜动而好玩,孩子的这种倾向惟有在家长管束下加以纠正。
这样,每天增加一些,--“凡忽视小事,便逐渐堕落”--习惯而成自然,后来津津有味地要举杯引满了。
那时,她把这位贤明的老妈和她的严峻禁诫已置之脑后了!主啊,你是常常关心着我们,对于这种隐匿的痴患,除了你的救药外,还有其他有效的方剂吗?父亲、母亲和保姆都不在旁,你却鉴临着;你创造我们,呼唤我们,潜引默导,甚至通过其他人物,完成有益于灵魂的行动。
我的天主,你那时在做什么?你怎样照顾她呢?你怎样治疗她呢?你不是用别人锐利刺耳的谩骂作为你秘传去疾的砭熨方法一下子把腐烂部分销蚀了?
经常陪她到酒窖去盛酒的使女,一次和这位小姐争吵起来,那时只有她们两人,这使女抓住她的弱点,恶毒地骂她:“女酒鬼。”她受了这种刺激,立即振发了羞恶之心,便从此痛改前非,涓滴不饮了。
朋友们的投其所好,往往足以害人,而敌人的凌侮却常能发人猛省。当然你处理这些人,仅凭他们损害别人的意愿,而不是依照你利用他们所得的善果。那个使女发怒时,只想使女公子难堪,并不想纠正她的缺点;她或是由于两人吵架的时间和地点别无人在,或是以为历时已久而方始揭发可能对自己反有嫌疑,遂乘着没有旁人的机会才敢放肆。
但是你,天地的主宰,千仞的悬瀑,时代的洪流,无一不随你的意旨而盘旋、而奔注;你用一个人的积怒治疗了另一人的积习。明察者不应以别人听我的忠告而去恶从善,使自以为出于我的力量。
第九章
她这样在贞静俭素之中长大起来,与其说是父母教导她尊奉你,尤应说是你教导她顺从父母。到了成年出嫁,便“事夫如事主”,设法使丈夫归向你,用贤德来向他宣传你,你也用这些懿范增加她的端丽,得到丈夫的敬爱赞叹。她忍受了丈夫的缺点,对于他的行为从未有所纷争。她只等待你垂怜丈夫,使他信仰你而能束身自爱。
我父亲的心地很好,不过易于发怒,她在丈夫躁性发作时,照常言容温婉,等待他火气平息,才伺机解释自己所持的理由,指出他可能过于急躁,未加思考。许多夫人们,丈夫的气性不算太坏,但还不免受到殴辱,以致脸上伤痕累累,她们闺中谈话往往批评丈夫的行为,我的母亲却批评她们的长舌,带着玩笑的口吻,给她们进尽忠言:
在听人读婚约的时候,她以此为卖身契,因此主张谨守闺范,不应和丈夫抗争。这些妇女知道她嫁着一个粗暴的丈夫,但传闻中或形迹上,从未听到或看出巴特利西乌斯曾殴打妻子或为家庭琐事而发生口舌,因此都很诧异,闲谈中向她询问原因,她便把上述的见解告诉她们。凡是受她指导的,琴瑟和好,每来向她致谢;不肯遵照的,依当时风俗,女子出嫁时,在证人及父母前读婚约,旧遭受折磨。
由于坏丫头的簸弄是非,她的婆婆开始也生她的气,但后来便为她的温顺忍耐所感动,竟把女仆们造成家庭间、姑媳间不和的谗言向儿子和盘托出,命令处罚她们。我父亲听从我祖母的话,并且为了整顿家规,保持家人和睦起见,便鞭责了我祖母所愤斥的女仆;祖母还声言谁再说媳妇的坏话,将同样受责;从此无人再敢妄言,家人之间融融泄泄,值得后人怀念。
“我的天主,我的慈爱”,你还赋予你忠心的婢女--在她怀中你创造了我--一种可贵的美德:人们发生龃龉争执,她总尽力调解;争吵的双方都是满腹怨气,像有不解之仇,人前背后往往会说出种种尖锐毒辣的话,发泄自己的急恨,她听到任何一方丑诋对方的语句,不但从不宣泄,只有从容劝解。
这种庸德庸言似乎不足称道,但人们刺心的经验,世间有不少人沾染了广泛流行的罪恶疫疠,不仅把积怨的双方对于仇家所发的言论尽量搬弄,甚至火上添油地加以造说;凡有人道的人,不仅不应该挑拨离间,增剧别人的怨毒,却应尽力劝说,平息双方的怒气。
我的母亲所以能如此,是由于你在她内心的学校中默导她。
在我父亲去世前一段时期内,她又为你赢得了他。我父亲成为教友后,对他未奉教前她所受的委屈绝不追怨。她真是你的仆人们的婢女。凡认识她的人,都因她的懿范而赞扬你、热爱你;他们感觉到你是在她心中,她的圣善生活的结果证明这一点。她“以忠贞事夫,以孝顺事亲,以诚笃治理家政,有贤德之称。”她教养子女,每次看见他们疏远你,便每次进行再造之功。主啊,至于我们,你的仆人们--由于你的慈爱,我们敢这样自称--在她去世前,领受了洗礼的恩泽,我们已同心同德生活在你的怀抱中,而她关心我们,真是我们一辈的慈母,她服侍我们,又似我们一辈的孝女。
第十卷 第八章 记忆和表象
我要超越我本性的力量,拾级而上,趋向创造我的天主。我到达了记忆的领域、记忆的殿堂,那里是官觉对一切事物所感受而进献的无数影像的府存。凡直觉所感受的,经过思想的增、损、润饰后,未被遗忘所吸收掩埋的、都库藏在其中,作为储备。
我置身其间,可以随意征调各式影像,有些一呼即至,有些姗姗来迟,好像从隐秘的洞穴中抽拔出来,有些正当我找寻其他时,成群结队,挺身而出,好像毛遂自荐地问道:“可能是我们吗?”这时我挥着心灵的双手把它们从记忆面前赶走,让我所要的从躲藏之处出现。
有些是听从呼唤,爽快地、秩序井然地鱼贯而至,依次进退,一经呼唤便重新前来。在我叙述回忆时,上述种种便如此进行着。
在那里,一切感觉都分门别类、一丝不乱地储藏着,而且各有门户:如光明、颜色以及各项物象则属于双目,声音属耳,香臭属鼻,软硬、冷热、光滑粗糙、轻重,不论身内身外的、都属全身的感觉。记忆把这一切会都纳之于庞大的府库,保藏在不知哪一个幽深屈曲的处所,以备需要时取用。一切都各依门类而进,分储其中。但所感觉的事物本身并不入内,库藏的仅是事物的影象,供思想回忆时应用。
谁都知道这些影象怎样被直觉摄取,藏在身内。但影象怎样形成的呢?没有人能说明。因为即使我置身于黑暗寂静之中,我能随意回忆颜色,分清黑白或其他色彩之间的差别,声音绝不会出来干扰双目所汲取的影象,二者同时存在,但似乎分别储藏着。我随意呼召,它们便应声而至;我即使箝口结舌,也能随意歌唱;当我回忆其他官感所收集的库藏时,颜色的影象虽则在侧,却并不干涉破坏;虽则我并不嗅闻花朵,但凭仗记忆也自能辨别玉簪与紫罗兰的香气;虽则不饮不食,仅靠记忆,我知道爱蜜过于酒,爱甜而不爱苦涩。
这一切都在我身内、在记忆的大厦中进行的。那里,除了遗忘之外,天地海洋与宇宙之间所能感觉的一切都听我指挥。那里,我和我自己对晤,回忆我过去某时某地的所作所为以及当时的心情。那里,可以复查我亲身经历或他人转告的一切;从同一库藏中,我把亲身体验到的或根据体验而推定的事物形象,加以组合,或和过去联系,或计划将来的行动、遭遇和希望,而且不论瞻前顾后,都和在目前一样。
我在满储着细大不捐的各式影象的窈深缭曲的心灵中,自己对自己说:“我要做这事,做那事”,“假使碰到这种或那种情况”,“希望天主保佑,这事或那事不要来”我在心中这么说,同时,我说到的各式影象便从记忆的府库存中应声而至,如果没有这些影象,我将无法说话。
我的天主,记忆的力量真伟大,太伟大了!真是一所广大无边的庭宇!谁曾进入堂奥?但这不过是我与性俱生的精神能力之一,而对于整个的我更无从捉摸了。那末,我心灵的居处是否太狭隘呢?
不能收容的部分将安插到哪里去?是否不容于身内,便安插在身外?
身内为何不能容纳?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真使我望洋兴叹,使我惊愕!
人们赞赏山岳的崇高,海水的汹涌,河流的浩荡,海岸的逶迤,星辰的运行,却把自身置于脑后;我能谈论我并未亲见的东西,而我目睹的山岳、波涛、河流、星辰和仅仅得自传闻的大洋,如果在我记忆中不具有广大无比的天地和身外看到的一样,我也无从谈论,人们对此却绝不惊奇。而且我双目看到的东西,并不被我收纳在我身内;在我身内的,不是这些东西本身,而是它们的影象,对于每一个影象我都知道是由哪一种器官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