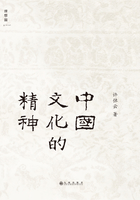这个政治结构的显然易见的特征是:
其一,封建国家权力的至高至大性。在中国封建时代,封建皇帝即天子是国家的人格代表,所谓朝廷社稷不过是天子家天下的别称,封建国家权力的至高至大性也就是天子权力的至高至大性。朕即国家,天下不过是天子的家,“家天下”很早就是中国的国粹。在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中,天子南面而治,凌驾于封建国家之上,并且代表着封建国家作为国家权力的最高代表,它集行政、立法、司法于一身,具有无法限制的至大权力,所谓“君子口出法随”,所谓“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就正是这种权力关系的生动写照。
封建皇帝通过直接任免行政官吏、批准议奏和所有国家事务的最终决定权,使他获得至高权力;又通过对全国一切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生活的任意干预表现他的权力的广大无边,他是国家权力的化身。封建中国,中央集权是以皇帝个人集权专制为其本质规定性的。
其二是政治结构的垂直型特征。西周的领主政治和战国诸侯林立,使社会政治结构呈现出网络形状,它具有一定程度的并列意味。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虽然也是网络状的,但它与并列状相反,是垂直型的(如图3所示)。这种垂直型状态,使国家政治活动中的各种关系很自然约束在统一和隶属关系网中。一方面,科举制和郡县制使这一网络得以成立并获得自身功能,从而使官僚政治确立起来;另方面,因为事实上整个网络是要依靠封建皇帝提纲挈领的,从而使这一结构获得了强大的灵魂。垂直型网络结构犹若一张大鱼网,皇帝就是撒网的人,皇帝的手动作起来,鱼网才能张开,从而纲目并举,官僚政治才得以实现。
其三,从家庭到社会,从皇帝到国家,便进一步构成了“一统天下”的局面。“一统天下”的意义并不仅仅表现在个人说了算,而更根本的是天下归在统一的原则和权力之中。所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不应该只看成是伦理准则,它首先是政治原则,是政治权力的分层和递进隶属关系的规定。而士大夫们一再强调的和奉行的君子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和抱负,就在事实上成为牢固上述隶属关系的人为努力。所以,封建国家权力的至高至上性和垂直型网络状态都把“一统天下”作为自己运动的结果,因而三大特征对于以中央集权为最高原则的官僚型政治结构来说是统一的。
这里的文化结构是指人们在心理精神活动中所形成的思想意识及其关系构成。从主要点看,它应包括思想本体、思维方法和价值观念。所以,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观是结成文化结构的三大要素。
中国古代文化丰富多彩,源远流长。但其主流,却是儒家的正统学说。所以分析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结构,应以分析儒学思想为主。孔子最早创立了“仁-礼”结构作为儒学的基线,奠定了儒家思想的本体论。孔子的“仁-礼”结构告诉我们,“仁”与“礼”是不可分割相互制约的。当从“礼”的角度看“仁”时,“仁”是受“礼”的制约的,它服从于“礼”,为“礼”服务,它的目的即表现在对“礼”的维护和恢复上,这时“礼”比“仁”根本;而当从“仁”的角度看“礼”时,“礼”同样地受到了“仁”的约束,“仁”
本来是手段,结果却使得手段高于目的,成为更根本的目的(“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矣”),这时“仁”成为本,“礼”
是末,“仁”是体,“礼”是用,“礼”反而成了“仁”的追求、实现的具体标准。这种“仁”与“礼”互为手段和目的、体用一源互为表里的状况是“仁-礼”结构的真实本性。
在这个儒学的基线里,“仁”与“礼”又是各具功用的。
“仁”的功用在于:一方面调和上层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另方面又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安身立命的准则。它为一部分人指明道路,又给大多数人以柔情的目光,从而取得了全社会的普遍效力。“礼”的功用在于:一方面限定统治阶级的内部秩序和结构,另方面又制约人民的不轨行为,成为封建国家不可易的“天下之本”,也具有了全社会的功能。但是,在现实性上,两者毕竟难以分割,它们是统一的,其统一之处就在于:“仁”屈从于“礼”。这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所谓“仁政礼治”特征的观念反映。理解这一儒学基线在整个儒家思想中的主体地位和性质至关重要,由此才能明白,所谓整个社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仅是“礼”的强制,同时又说明它是“仁”的劝慰;所谓“三从四德”,也不仅是“仁”的说教,同时也包括着“礼”的敬畏性;而“天理人欲”之分,在这里又找到了它的深厚根基;并且我们也就进一步能够弄清楚弥漫于整个中国社会的“忠”“孝”观念不过是“仁-礼”主体思想的现实要求,从“孝”到“忠”不仅是血缘宗法观念的延长,也是仁礼结合合二为一的必然结果。
上述儒家主体观念所以能够确立,从思想自身的演变规律看,实得力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天人合一”的合观方法,要求人们不能离开天去谈人,亦不抛开人去论天。而当中华民族从自身需要去进行天人关系思考的时候,就不但使对客观自然的理解印上了人际现实社会关系的主观投影,也使得对人际关系的理解打上了天命必然性的色彩。这种情况,一方面使中国文化关于自然的理解,带上了伦理与政治的色调,也使中国文化关于人际关系的理解,打上天命神学的印痕。而它的理论形态,则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庸”。一方面,“中庸”可以理解为“天人合一”合观认识的必然结果;另方面,它又成为追思天人关系的根本方法。所以,不能只把“中庸”作为道德论来理解,而从根本上说,“中庸”是矛盾观、发展观和方法论。不是由人际关系中抽出“中庸”的道德规范,恰恰相反,“中庸之道”是从“天人合一”的合观思考中抽象出来从而作为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过”和“不及”的指责首先要求的是“天人关系”的“合观思考的“致中和”,然后才是人们现实社会关系的“致中和”。“仁-礼”基线的内在一致在这里找到了更为广阔的背景和根据。
中国古代文化的价值观突出地体现在“义利之辩”上,形成了“贵义贱利”的价值观。儒、墨、道、法争夺封建中国思想正统地位的斗争中,儒家所以能打败墨、道、法各家,它的“贵义贱利”的价值观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贵义贱利”的价值观主要包括两点。其一是用“义”来排斥“利”,否定“利”,即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谋道,小人谋食”;其二是以“义”为原则将“利”
溶解其中,所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俭不违礼,用不伤义”。中国古代文化的价值观念并不一味地排斥“利”,关键在于将“义”、“利”关系如何摆。封建士大夫一再提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并不是仅仅看中了其中的经籍教义,而是首先在于“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所以,它的现实逻辑是:读书可以做官,做官意味着发财。“做官”与“发财”的结合实在是以“义”与“利”的结合为背景的。因而,并不是这个文化价值观无视功利,而是需要在现实功利之上挂上一块以“义”
为旗帜的秉性清廉、道德高洁的牌子罢了,它直接服务于“天人合一”敬畏原则和仁礼结合的主体思想。所以,“仁-礼”结合的主体论是中国封建文化的内在规定,是它的本质内容,“天人合一”是这个文化结构的根本观念和根本方法,而“贵义贱利”则成了前两要素的必然产物,它们三位一体,形成中国封建文化结构模式。
这个文化结构的最突出特点是强调了群体和谐一致。所谓“仁-礼”基线构成不过是以理论形态规范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同时又使这个秩序穿上了温情脉脉的外衣。并且由于这个结构以“天人合一”的“中庸”之道作为更深厚的根据和方法,所以“仁-礼”结构极力表现自己的人为成分少而客观性质多,它不只是现实人们要想成为这个样子,而是某种人类无法摆脱的力量管束着族类,使其必须成为这个样子。因为天人之际的平衡和谐,要求人际关系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而“致中和”的“仁-礼”主体论思想正恰好表现了这一点,所以,“仁-礼”的人际原则与天人之际的合一原则和谐起来了。
但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回避物质利益,无法不讲功利。然而人际关系一旦以功利为目的,上述的和谐立即就会遭逢动乱和背离,从而破坏和谐。所以,一定的价值观成为结构和谐的重要保证,“贵义贱利”就正是充当了保证结构和谐的角色。这个和谐具有三层意思,一是它追求天人关系的和谐,二是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三是它保持结构内部诸因素之间的和谐。但是,三层和谐的实现,也就同时使这个结构呈现出它的运动指向,这个指向正是一种层层隶属和约束,从而达到“上同而下不比”的“大一统”境地。它是这个结构的宗旨所在。“天人合一”的现实目标一是“君权神授”无可非议,二是规范有则人人不能超越;“仁-礼”
的要求通过“忠孝”和“三从四德”的引导和强制进一步把“君→臣→父→子”的关系贵贱序列化;而内在地泯灭了自己功利欲望之后才能称为高尚的君子,这正是防止反叛的“贵义贱利”的价值观的妙用。所以,和谐并不是一团和气,平等互利,它不是平等型的;和谐具有自己的运动指向,它表达了依附与隶属的性质,它通过层层规范和约束体现着“大一统”的最高原则,“大一统”成为这个文化结构的灵魂。因而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以大一统为宗旨的和谐型文化结构。
以国有为背景的地主型经济结构、以中央集权为原则的官僚型政治结构和以大一统为宗旨的和谐型文化结构,虽然它们各有自己的内部机制,从而具有自身的运转规律及其特性,但是,对一个社会来说,只有当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组成一个整体的社会结构的时候,才能发挥作用,对历史变化产生总体性影响。中国历史上,正是这种地主型经济结构、官僚型政治结构与和谐型文化结构三位一体,才构成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体化社会结构,如所示。
一旦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子系统结构结合在一起,便组成社会结构的总系统,从而表现出它的总体功能和特征。
中国封建社会的总特征首先体现在一体化上。社会结构的一体化不只是指社会结构的各子系统结构的不可分离,而主要是指通过国家政权力量把三个子系统结构统一起来,使其呈现出三位一体的状态。在小生产基础上形成的以国有为背影的地主型经济结构要求建立与自己相适应的以中央集权为原则的官僚型政治结构,这个中央专制的国家结构一旦成为一种独立力量,也就必然作为社会的实体而存在。小生产的经营方式要求外在的(对于它来说)统一力量即国家政治结构来加以保护,这个集权的国家就成为小生产经营方式的前提,因而它本身就成为重要的经济条件。没有国家中央集权的政治力量,首先是地主制经济就可能退化到庄园制领主经济,自耕农的命运也必然相继破产,从而在小生产经营之上的地主型经济就难以维持和存在。中央集权的政治力量因为掌握土地所有权和剩余产品的最终支配权,所以一方面它成为小生产经营方式的前提和条件,因而是其重要内容,同时它又是这种生产的权力意志表现,因而成为与小生产处在外在关系之中的一般政治权力。在这里,一定的生产方式产生出一定的上层建筑,而这种上层建筑又由于土地财产的性质转化为生产的前提,使它成为经济——政治混合主体。
很显然,中国封建社会这种同时实践经济和政治的双重职能是通过国家政治权力的杠杆而实观的。
但是,封建国家的政治权力并不是一种盲目的力量,它是由一个统一的阶层——儒生,按照一个统一的思想——儒家正统文化而建立的政治结构所表现出来的。在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上,要建立起统一的以中央集权为原则的官僚型政治,如果离开一个统一的以大一统为宗旨的和谐型文化是不可想象的。然而,这个政治结构一经形成,它便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同时又要求一定的文化结构与它相一致,反过来,它便支配和控制了文化结构。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史上,孔子一再被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儒家思想所以被推到“独尊”的地位,尊孔读经所以能成为士大夫生活的主要信条,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喜好,更主要的是封建国家的政治需要并依靠政治权力治化和教化的结果。文化结构与政治结构的相互联结不可分离同样是通过政治权力将其统一起来的。
在一定的经济结构之上产生一定的政治结构,这个政治结构同时又成为这个经济结构的运动前提;按照一定的理想和文化由统一的阶层组成国家政权,这个政权又反过来要求这个文化结构符合自己的规范。在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子系统结构中存在着高乎其上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国家政权的力量,它毫不客气地将其他两者统一在自己的门下,使它们一概丧失了自己的独立个性,从而使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呈现出一体化特征。
由于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结构能够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将其他两个结构集于一身,从而形成统一的三位一体的社会结构,所以这个社会结构便具备了自我调节的总体功能,从而形成超稳定系统。超稳定是现代控制论中的概念,指的是一个结构能够通过周期性震荡来调节对原有状态的偏离使其回到适应状态从而保持系统内部的稳定。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体化结构正是这样的超稳定系统。它的自我调节是通过用两种手段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