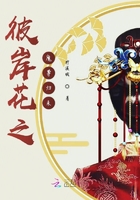整理往日旧稿,发现在以往自己所写的文字中,基本上都跟四个方面相关,即中国的哲学传统、文化选择、社会道路以及中国的现实改革。这些问题,又都可以被称作是中国问题。
有意思的是,这些问题从时间序列上来说,也正好反映出自己20年来关注学术问题的心路轨迹。记得1980年离开政府工作进入学术界以后,最初关注的就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问题,这是我进入中国哲学领域的原由。由思维方式而追寻其形成的社会历史根源,使自己从80年代初起,把中国文化的选择和中国历史社会发展模式作为新的研究重点,此正好与当时的“文化热”和“改革热”不谋而合。20年来,不仅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巨大的变化,而且学术热点也追随着时代的脉搏不断转移。从旧日文字中可以感到,不仅是自己,几乎整个学术界的兴奋点也都跟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迁而变迁着,这也正好表达出中国社会人文学者治学的价值取向。
我自己往日的文字就是这样由关注的具体问题不同而表达出来,但这些问题又都是中国问题的具体化。所以这次结集出版,想来想去还是冠名为“中国问题”论,不知是否妥当?
关于所谓“中国问题”,在今天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使用这一概念,看来此概念的可取性已经不是问题了。但是,记得在1982年即十多年前,我当时还在西安工作,曾经和国内的一批中青年学者相约,为了更好地使“中国问题”成为大家关注的学术问题,决定办一份“中国问题”
刊物,出版一套大型“中国问题研究丛书”。然而申报报告递出去后,却以中国人不宜提什么“中国问题”,所谓“中国问题”不过是西方外国人才用的词汇为由而被搁置了。
其实,在学术研究的意义上,任何问题,当它不能对象化作为问题出现的时候,是无法进入研究的视野的。当然,重提当年的旧事今天已没有太多的意义,然而这件事却告知人们一个简单的道理,一旦只从政治角度理解和判断学术的问题,就可能使问题本身面目全非并且顿时变得复杂起来。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也许还有一点意义。
“中国问题”确是重大的学术研究课题,但是人们对它的理解却不尽相同,也正是18年前,我们曾对“中国问题”的理解,作了如下的表述:
(一)“中国问题”作为综合性的研究课题被尖锐地提到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日程是由如下两方面的原因构成的:
其一是我国正在全面展开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乃是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为了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首要的问题就是对“中国”必须有一个清醒而科学的认识;其二是由于三十年来我们的失误而与世界重新拉开了距离,使我们仍处在比较落后与贫困之中。沉痛的教训要求我们整个民族进行深刻反思,我们不仅应该认真总结现实,还应该总结作为传统的历史,就是说,我们必须对“中国”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理解。上述两个因素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的失误使我们坚定地看到必须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而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又必须将它先前的教训作为历史新起点。这两个方面都强调指出,“中国问题”研究应该成为中国走向未来的深厚根据。
(二)其实,“中国问题”作为一个问题并被人们普遍关注,已有百年的历史,它的研究与中国的命运一直息息相关。
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者用鸦片和炮火砸开了中国的大门,顿时使神州大地充满耻辱,“救亡保种”成为古老民族的沉重呼声。应该怎样对待中国的古老文明,传统的千年古国应不应当“变”,如何“变”,如何才能使中国富强,构成当时“中国问题”的中心内容,它的直接成果就是变法运动。但是,事实证明,西方的路子走不通,“中体西用”也救不了中国。于是,“中国问题”研究走上新的阶段。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差距在哪里,区别又在哪里,中国有什么特殊性,中国应当建立起什么样的国家和社会,便构成辛亥时期“中国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孙中山作为中国革命的先驱第一次提出“国情”问题,标志着研究的深化。但是,资产阶级的身份立场与方法,使这一时期的研究无法走上科学化。惟有以陈独秀、李大钊开先河,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完成的思考,才使“中国问题”研究进入一个新纪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使中国走上了胜利的解放道路。与这一研究相对应的是西方帝国主义以关心中国为名,炮制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无法独立富强和发展的谎言,为其侵华寻找理论根据。国民党右派人物对中国历史的蔑视和对人民力量的偏见,封建顽固派对国粹的偏爱,实际上使他们成为帝国主义的帮凶。在中国近代史上,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始终是跟中国变革和革命联系在一起的,成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国问题的长期研究和思考,为正确理解中国的历史、现状和发展提供了一系列科学认识,使中国的解放事业获得了历史性成功。
但是,建国30年来中国在一种封闭系统中的运动,使它与世界重新拉开了距离。贫穷和落后的现状极大地震动了整个中华民族,引起整个民族对自身的反思:为什么在新中国会出现百万人蒙冤的错划事件?为什么会发生持续十年之久的大动乱?为什么现代中国的封建主义阴魂不散?为什么中国会长期封闭而不自醒?为什么苦干30年却与世界的距离越来越大?为什么中国至今仍很贫困和落后?多年前就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及“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原因”的大论争决不仅仅是无关痛痒的学术争鸣,而恰恰证明中国人必须在新的条件下对自己进行重新认识。
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冲击,不但对中国造成压力,而且又一次提供了机会。而历史证明,中国的经济起飞和社会全面发展,又必须以对中国问题的全面而正确的认识为前提,中国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中国应如何对待自己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谋求发展,中国应当为人类作出什么贡献,都构成了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重要内容。
百年以来,“中国问题”研究之所以经久不衰,而且不断发展和深化,构成中国长时期的重要课题,其根本原因是与中国命运息息相关。不仅如此,随着世界一体化趋势的增强,海外机构和人士对“中国问题”的关注亦与日增加,由世界1/5人口组成的并且具有超级文明历史的中国情况如何,成为全人类无法回避的大课题。“中国问题”将成为专门的“中国学”。中国人不能很好研究“中国学”,中国便无法摆脱其举步维艰的局面;世界不能解决好“中国学”,整个人类便会影响到自己走向新的时代。“中国学”已经历史地构成海内外更加注目的挑战性课题。
(三)但是,我们国内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状况却不能令人满意,截至目前为止,国内没有一个这样的专门机构,也没有一份专门刊物报纸。我们不仅为外国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说法而感羞愧,更为当代中国发展战略的不少主张由国外人士提出而感到不好意思。这一状况亟待改变。
上述文字,是我在整理旧稿时发现的,从今天的眼光看,无疑其中带有强烈的当时的时间烙印,但我想关于“中国问题”的认识基点尚有参考之处。我们现正处在世纪之交,新的挑战不断出现,人类面临的问题也更加多样化,我们正应该以新的视角来关注中国问题,因为中国的命运与人类整体的命运是紧紧相连的。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于海南“如常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