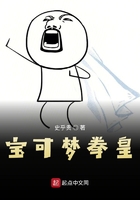我没有一点头晕目眩的感觉,刚刚在里面抽血时,那个四十多岁的女医生一边抽还一边拍着装我的血的血袋满意地说,“嗯,这个血不错。”好像那里面装的不是血,而是在肉菜市场挑中的一块刮洗干净的肥猪肉。
但是膝盖却越发地痛起来,没有一点因为雨停而好转的样子,双腿勉强地支撑着自己的体重摇摇欲坠地向前迈了几步,终于还是两腿一软,跪到地上。
冰凉的雨水立即从厚厚的裤袜里渗进来,迅速浸透了我的膝盖。来往的行人个个都回头看我一眼,眼里有好奇和嘲笑。真丢脸!我低下头,呼出一口气,强迫自己不去看别人的表情,右手撑住肮脏且湿漉漉的地面,我企图站起来,但没有成功。从膝盖涌来的寒气似乎还在身体内流窜着,我使不上力,也觉得冷。
直到一双强健的手臂,把我从地上扶起。
那么有力,仿佛整个世界都可以掌握在他的手里,我的身体在他的掌心,不盈一握。那种透着温暖的力度,可以抵卸任何冰冷的侵袭。
我回头,迎上那双沧桑的眼楮。
莫名地就生出一股怒气,洛u灾v的身体竟然如此贪恋他掌心的温度与力度,我咬牙切齿地挣开他的手臂,“多管闲事!”
乍一挣脱他的钳制,身体却不争气地摇摇欲坠,有力的手掌再度钳紧了我的双臂。
“看起来我不像是在管闲事。”男人的脸色暗了暗,声音却透着坚持,“你的身体比你的嘴更诚实。”
“你神经病。”他的力气好大,我挣脱不开,一个女人如何有能力去与男人比试蛮力,“关你什么事,我又不认识你。”
“张芒,电视台的记者。”男人松开钳住我的一只手,塞了一张名片到我的手心里,“现在我们认识了吧?郑琳小姐。”
“这世上有很多骗子。”我看也不看那张名片,随手把它向后一扔,雪白的小卡片像只断翅的蝴蝶,在寒风中瑟瑟地下坠,“你是陌生人。”
“刚刚在里面抽了你血的医生和护士也是陌生人。”他好整以暇地,似乎早就想好了台词,“至少我不会吸你的血。”
“安,管她做什么?”掉了手机的男人从停车场开了车过来,遥遥地叫道,“这女人神经有病。”
“是啊,我是神经病,你管我做什么?”我不怒反笑,嘲弄的唇角向下一勾,“你也疯了不成?”
“我送你回家。”他专注的凝视我冷嘲的表情,眼角笑出温柔的纹路。
“不要。”越是专注的温柔,越是印留在我心底残忍的痕迹,心会沦陷在这种不真实的温柔里,再无了归期。“放开我!”我在他的掌心不安地挣扎,“你凭什么管我,我又不认识你,放开我,你滚开……”
他却不理,就像是什么也没有听见一般的淡漠,拉着我的手就往他们的车走去,我又急又怒,本能地低下头就往他的手臂上狠咬一口,腥红的血味在我的唇齿间四散,男人痛呼一声,松开了紧紧钳住我的手腕。
我转身便逃,膝盖不痛了,双腿突然有了力气,这个男人是头逃出牢笼的怪兽,我必须逃离。
但那温暖的力度如鬼魅般侵袭,男人抓紧我,把我拦腰抱起,我在他怀里挣扎怒骂尖叫捶打撕咬,男人闷哼一声,双臂却如铁铸般坚不可摧。“你这个跋扈冷漠的该死女人!”他拉开后车门,粗暴地把我连同他自己一同甩进车位。
我伸手想去抓车门,被他拉了回来,紧紧地压在他身下。我的脸贴在男人的胸前,听着他有条不紊的呼吸和心跳,强健的肌肉和温暖气息透过薄薄的T恤,我冰冷的身体仿佛也稍微有了一点温度。
突然失去了坚持的力气。冰冷的身体,如此贪恋他的温度。怕些什么?挣扎些什么呢?顶多也不过是弃尸荒野。鱼有嗜水的权利。
察觉到我的妥协,男人低下头看我,笑了。眼角细细的鱼尾纹深深的拉长。
我好像从来没有问过你,为什么会取名叫火翼?
沉默,半响QQ才响起“吱吱吱”的叫声。
火翼……是一种在海里活得好累的虫。
累?累。
人在人海,难免会有找不到自己的时候,或苦或悲,都是生活,怎敢轻言一个累字?
打出这排字,我冷笑。
我居然扮演起神父的角色,现实中如此灰色的一个女子,在网络中却是另一个永远不可触摸的极端。热情开朗、善解人意、妙语如珠、锐利剔透、风华尽现。
就像一团火。恣肆着红红的燃烧,吞吐着勾引的火焰。
笑……曾经有过很积极很向上的时候,虽然只是芸芸众生里的一个碌碌无为的小人物,但是却觉得自己有一颗与别人颜色不太一样的心,即使轮回在今生只能做一条小虫,也应该选择能努力挣扎成蝴蝶的那种。一旦展翅,哪怕大半辈子都必须匍匐于泥泞之间,亦无怨悔可言。
我的心一颤。多么像是在说我!越是自私的人,越怕受到伤害,因为我们总是爱自己最多。呵我何偿不是一只火翼,一只蜷缩在自己脆弱的壳里保护自己的小虫,尽管那壳之于现实的严酷并无多大用处。
那个曾经,很痛?
嗯,很痛。
笑……想必累也一定是一种有着旋转形花纹的美丽硬壳,让人一旦投身进去,就化作了软体,活了畏缩,感觉困窘,遭受背负,再也做不成自己。
我是如此深刻地理解火翼的无奈,因为我曾经也很怕自己一不留神就渐瘫成一副软体,固定在一个僵壳里,成为火翼。可是现在,我居然那么甘愿做一只火翼。
女人太敏锐,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笑,手指飞快地在键盘上跳跃。
男人总是不希望女人太聪明,惟恐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
呵呵,总是这样咄咄逼人。你呢?似乎很少提及自己。为何要叫琳子?
停在键盘上的手指顿了顿,我点了一支烟,眼神跟着缭绕的烟雾一起朦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