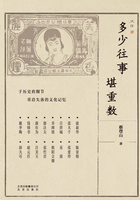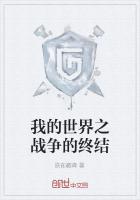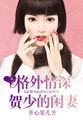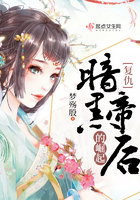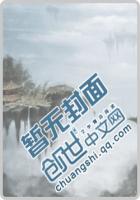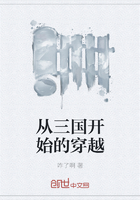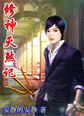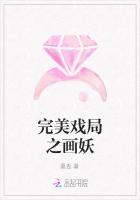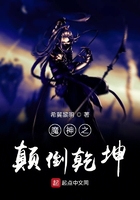死者以死亡扩大了空间
生者以思念装饰那星空
当我站在阳台上默默地吸烟
下面的广场上已空无一人
走呀走呀,两个旧时代的人儿
沿着新世纪的大街
未来由烁烁灯光铺就
仿佛昨天的太阳已然熄灭
江水的气味随风飘来
泥土的芬芳一阵阵爆炸
虚无的怀抱接纳我
神秘的恩情犹如这腊梅花开
走呀走呀,谁遗留了世界
就像遗留了我们?谁以旧换新
校正新年?爆竹声声,扩大了空间
从此与死亡更亲
【石头孩子】
在庄严的墓地我遇见那石头孩子
他的笑容印在石头上
死于八岁,拒绝长大
这操蛋的孩子改变了父母的人生
不可能再相爱,因为
他们只能爱你
不可能再爱生活,因为
他们更爱死亡
曰光如风吹拂,他死于谁都有过的八岁
小小的石头孩子
把石块垒砌在我们的心底
虚无就像从没出生过
驾定就像年逾百岁
曰光如风,目光如雨
小小的石头孩子如玲珑的石蛋
藏身石头墓园
【晴空朗照】
虚无如晴空朗照,因为有人问
“你母亲好吗?”
因为身后就是她的房子
路边就是她熟视无睹的修鞋摊子
站在你面前的是她五十岁的儿子
在这条小街上总有老友偶尔相遇
总有这晴朗松懈的时光
总有一些光刻画了生活
但是,我母亲好吗?
问话的人继续走路,但她再也遇不见一个熟人了我继续上楼,坐进母亲坐过的沙发
楼下的老妇人越走越远
晴空漂移,刺入这扇窗户
偶然的人世像骰子摇晃(小引)
所有对诗的不同定位必将产生对诗不同的解释方式。这似乎也表明了,诗的确是一个有着不同含义的东西。比如,我一直认为诗是偶然的。这个“我认为的偶然”中包含有两个意思。一方面,我觉得诗从本质来讲都是“假”的。诗人的任务,就是如何把这个假的东西,自然或者不自然的弄成真的,且让它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力或者欺骗性,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忍不住喜欢,莫名其妙地接受,并且认为它就是一种事实。而另一方面,诗又有其必然的一面。它时刻都企图超越标准的约束,或者说,它其实一直在标准之前标准之外存在着,只是尚未被我们偶然地发现。
阅读韩东,我常常这样想,在幽暗的神秘中,诗人是如何偶然又必然地抵达那些常识呢?换句话说,在当代汉语的语境下,我们对诗的看法应该首先来自于我们怎么写还是来自于2别的什么?在我看来,诗从来就不会单纯地旁观世界和生活,而是直接参与其中,是创造这个世界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诗就是诗的写法。而更进一步,要理解诗,首先必须理解怎么写诗而不是怎么看诗。这有点像我家楼下的一群孩子,他们整天乐此不疲地在沙堆上玩耍,搭建他们想象中的高楼大厦,如果你趋近问其中一个孩子,为什么要这样搭建这样一座房屋,他会回答你,因为上次没有搭好。
我猜想,作为当代汉语诗歌杰出的代表诗人,韩东遇见类似的问题,或许也会像那些孩子做出同样坦率又迟疑的回答。早年的韩东,曾经以决绝的□吻提出“诗到语言为止”,这句近乎箴言的判断,影响了一大批年轻诗人关于诗的思考和尝试,虽然他在多年后反复提到“话是一次性的话,这种一次性的话变成了真理就很可怕了”。而近年来,诗人似乎逐渐放松,并开始秉持着更加宽容和自然的艺术观点。比如他在最近的博客上谈到自己的创作观念时说:“诗歌是多元的,一定是多元的。”并进一步解释说:“如此,才没有压迫,才有快乐和真知。”
我理解韩东的这种转向(或者说深化更为合适)。因为一个诗人的创作,其根本性的来源还是承担在他的思想和工作的价值上。我当然相信,二十年前《有关大雁塔》的韩东和现在的韩东还是同一个人,但我又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似乎还有另外一个韩东的存在。当我们从诗的内部来考察时,我们会发现,这两个韩东一以贯之的是对语言和形式的不懈追求和探索。诗到底应该怎么写,是每一个诗人都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它从哲学层面上有效地回避了“诗是什么”这样一个虚妄的永恒问题。直接进入了诗的内部进行着具体的操作永远比围观在旁边来得有力。当“写诗”成为一个问题,“诗”这个概念早已经动摇。换句话说,当我们开始新的写作时,就会面对新的问题,诗也将成为新的概念。
其实,任何一个杰出的诗人,都一直在不断的不确定中跋涉着,不独韩东。每一个诗人的写作都有着一个不愿意公开的野心,就是力图修改和填补诗的含义,甚至,用新的含义去排挤旧的含义。只不过大多数的诗人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做的这项工作,而韩东,则是把这种自发的诗学冲动转换成了自觉的工作。
2002年,韩东与朋友们重新建立了“他们”文学网站。在这段时间中,他创作了一批与以往写作迥然不同的作品,其中有一首诗的名字叫《格里高利圣歌》:
唱歌的人在户外
在高寒地区
仰着脖子
把歌声送上去
就像松树
把叶子送上去
唱着唱着
就变成了坚硬的松木
一排排的
这是一首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的短章。让我感兴趣的是,即便你从其中读到了某些属于宗教色彩的气息,但是作为诗本身,却又在语言的角度上剥离和超越了宗教色彩。这首诗既延续了韩东早期对语言的追求,也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诗人近年来对诗歌内在精神的新的探索。在这首诗中,我看到了以格里高里圣歌搭建出的一个文化背影,却不再看到跃下高塔般的对意义的无情消解。或许,历史意识与英雄主义的解构对韩东来说,已经逐渐转变成了理性的思维,那种断裂感产生的痛楚,已经转变成了“唱歌的人在户外,在高寒地带,仰着脖子”。
而另外一首《我和你》则似乎是他同名小说的诗歌版的再解释。韩东在诗中写道:“我和你一样,来自父母/偶然的相遇、相爱、相伴随/来自他们偶然吃到的食物/偶然获得的性别/我们长大,任凭偶然的风吹/偶然的人世像骰子摇晃……”理性、客观的基本调门是韩东擅长的语言方式,但他在这里似乎并不是以怀疑的态度面对世界,转而更多以承认、反思的面容坦然登场。虽然一脉相承的虚无感依旧在这首诗中洋溢,但这或许是韩东作为一个诗人的天性使然,“偶然的人世像骰子摇晃”,这种虚无感不是韩东的一个偶然特征,而是作为一个生活中的人,韩东在面临多元、复杂的现代化世界时,努力想保持住的一个诗人的不合作的尊严。
不管从哪方面来理解,把诗写成什么样,或许永远是一个真正决定诗歌命运的话题。可是,我们如何来知道并相信这一点呢?韩东的思考是回到多元。不妨这样来理解,韩东所认为的多元,实际上是意识到了,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生命体,诗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诗要做的工作无非是从各种知识重新走到无知的境地中去。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恐拍是没有了。“把歌声送上去”是诗的目标,“就像松树,把叶子送上去”,韩东从理所当然,走到了理所当然的限制,何尝不是一次对自己的重新整顿和叛逆。有趣的是,从这种整顿和叛逆中,我看到了韩东对主体和秩序的渴望。现代主义时期尼采曾高呼“上帝死了”,后现代主义时期福科说“人死了”,韩东作为第三代诗人的杰出代表,一步步走来,现在却冷静地在诗中写到“唱歌的人在户外”。是的,这不过是我们偶然的胜利。
走过大雁塔的韩东不再“以夸张的、游戏的、滑稽的方式展现人生的卑琐”,相反,他更加愿意勇敢地直面这冰冷的世界。这其中,有隐藏的理想主义,有对崇高和神圣的向往,也有着对快乐和真知的追求。
对一个诗人来说,只要存在着理想和现实,就必定存在着选择。那么,“一天的欢愉有如一生”可以是一首诗的结局,或许韩东认为,这也是生命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