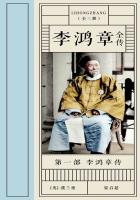吴征镒在病床上躺了半年。出院后,他便直奔清华大学生物系植物教研室。这时,他还穿着石膏背心,不能弯腰,只能直挺挺地坐在桌边,整理植物标本,做卡片。他的举动引起了一位女性的注意,这便是后来成为吴征镒夫人的段金玉。段金玉是辅仁大学的毕业生,当时是李继侗先生的助教,她动手能力很强,做的植物生理实验,操作非常严格,很受李继侗先生的器重。1951年4月22日,这对年轻人走到了一起,结为伉俪。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为他们主婚,历史学家吴晗(时任北京市市长)为他们证婚,婚礼简单而热闹。几十年来,这对夫妻志同道合,相濡以沫,早已过了婚姻的钻石之年。
1949年12月,吴征镒奉调到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工作,与汪志华一起分别担任党支部正副书记,党组由恽子强、丁瓒领导,但全院党员只有七人,均由院外调入,其中一人尚为秘密党员。
1950年1月,吴征镒就任静生生物调查所整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为钱崇澍,接管私立静生生物调查所和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并将二所合并为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静生所”在文津街3号的旧址成为科学院最初院址。直至5月,吴征镒主要从事解放前各老研究所的调查、研究、整顿、合并工作,以及筹建一批新的研究所,如昆虫研究所、动物研究所、海洋生物研究所、水生生物研究所等。
1950年2月,吴征镒到北京植物所任研究员兼副所长,回到了他挚爱的植物学研究岗位。
次年,吴征镒奉派与陈焕镛、侯学煜、徐仁组成代表团参加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南亚栽培植物之起源及分布”学术讨论会。此行有两重使命,首先,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参加国际学术活动,又是二战后在新兴国家印度召开的,所以临行前吴征镒和侯学煜受到周总理亲自接见,总理指示:“要多交朋友,多了解情况。”第二个使命是在印度访问期间,动员当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供职的殷宏章和在印度Sahni古植物研究所任所长的徐仁归国。代表团在印度考察了典型的热带季雨林和稀树干草原、热带荒漠等植被类型。吴征镒发现,在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山南麓,印度的不少古植物和云南植物的种类很相似。回国后,他写了一篇报告,介绍了历时两个月考察印度的情况。此行对他十年后返回云南所作的“关于北纬20°~40°之间的中国—喜马拉雅植物区系的研究”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1953年,吴征镒又随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苏联。他对苏联学者详细研究苏联植被、植物地理学以及植物区系学所取得的成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中国植被、中国植物区系类型和分区问题,作为自己以后的研究对象。回国后他写了两篇报告,详尽地介绍了苏联在地植物学、植物生态学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在植物园建设和利用植物资源方面的宝贵经验,以及植物学研究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的情况。这两篇报告发表后,在中国植物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这一年起,吴征镒开始组织中国大区的综合考察。这次大区考察分为华北和西北,华南和西南两个大组,其规模之大,是中国科学考察的第一次。吴征镒先任华南组的负责人,1955年又转到西南组。
原产于巴西亚马逊河的天然橡胶,是重要的工业原料和战略物资。当时,帝国主义对刚诞生的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为了打破这种封锁,党中央作出了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引种橡胶的决策。以北京大学李继侗教授等为首的全国植物学、林学、生态学等方面的专家奔赴海南岛、广东西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进行橡胶宜林地的调查工作,并在海南、广东、广西、云南等地栽种。当年,三叶橡胶从南纬5°的巴西引种到中国一次成功。但是,橡胶栽培中问题较多,橡胶成活率较低,广东、广西沿海不宜种植橡胶。1952年到1954年,吴征镒和罗宗洛、李庆逵、马溶之等科学工作者每年都要去海南,一去就是三个月,对橡胶宜林地大气、土壤、肥料,以及橡胶生长规律进行综合考察,积累了几万个科学数据,并通过细致的观察分析,终于找到了橡胶种植的科学栽培方法,橡胶种植和高产的目标得以实现。到1955年,橡胶林终于在海南岛自然成林,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橡胶基地。这几年的热带资料考察,使吴征镒认识了华南热带季雨林,特别对其次生林和灌草丛等热带植被的分布、演替等规律有所了解。虽然对其他稀少的原始雨林、海岸林、红树林等是走马观花,未能深入,但对热带北缘的特点,季风、台风、寒潮和石灰岩区干旱仍有切身体验。在此基础上,吴征镒重写了中国植被初步分区中有关热带植被的部分。
此时,吴征镒在学术研究上已硕果累累。1955年,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
1956年,苏联科学院提出与我国合作,研究解决紫胶虫北移至苏联的寄主问题,初由科学院派刘崇乐率队,蔡希陶在云南就地参加,后又派吴征镒和简焯坡两人赶去。至次年再由刘崇乐任队长,吴征镒和蔡希陶任副队长,正式组成西南生物区系及资源综合考察队,实际上他们承担了橡胶宜林地和紫胶寄主问题两项重点考察工作,苏联专家的任务只是动植物区系调查和采集。此行先到德宏一带,因吴征镒是旧地重游,植物区系和植被都比较熟悉,有问必答,苏联学者给了他 “植物电脑”的谑称。1958年,考察团又去了滇东南一带。至1959年,考察团的队伍有所扩大,就开始了在西双版纳的调查。虽然此时中苏关系开始恶化,但植物学家之间的合作尚在高潮中。
随着考察的深入,他们开始筹划在西双版纳建立热带生态地理群落定位研究站的工作,并到勐仑的葫芦岛勘查热带植物园址,从而为现在的西双版纳植物园确定了园址。
(九)
1957年,吴征镒发表了解放后的第一篇论文《中国植被的类型》(署名钱崇澍、吴征镒、陈昌笃)和第一幅全国植被图(署名吴征镒、陈昌笃)。
这时的吴征镒已年逾不惑,他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实现吴韫珍老师所说的建立中国植物学本土化的研究体系。在解放前这只是梦想,新中国却使这个梦想有可能成为现实。吴征镒还有一个魂牵梦绕的地方,那就是“一天高一丈,云南在天上”的神奇的云南。
吴征镒说:要搞清中国的植物,必先认识云南的植物。于是,1958年他毅然放弃了北京优越的生活和科研条件,举家迁往云南。
吴征镒一到云南,便与在抗战时期就结下了深厚友谊的蔡希陶一道,组建了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并根据云南自然条件复杂、生态类型多样、植物种类丰富、资源开发利用和发展潜力巨大的特点,开展植物分类、植物地理、植物化学、植物生理、植物引种驯化和植物形态解剖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并在50年的时间里,培养出一支高水平的植物学研究队伍。
吴征镒对蔡希陶非常钦佩。1933年当时还在清华念书的吴征镒到静生所时,就听胡先说:“希陶将有壮行!”果然,蔡希陶只身去了云南,并历尽艰险,完成了中国植物界对云南的一次大考察。
在云南植物界,如果蔡希陶是披荆斩棘、开山辟路的勇士,那么吴征镒就是胸怀万壑、探索奥秘的睿者。他们相知相交,情谊深厚。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经历过中国最黑暗时期的苦难,都汲取了中国优秀文化的精髓,都有很深的文学功底,都有着最坚定的为真理奋斗的崇高信仰,都有着为中国植物学献身的坚强意志,都有着科学的创新精神。吴征镒调到昆明后,与蔡希陶互相敬重,合作十分默契。他们与苏联专家共同赴西双版纳考察,为热带植物园选定园址,不久,蔡希陶即赴西双版纳勐仑葫芦岛创建了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并在热带生态地理群落定位研究站的基础上开始多层多种经营的研究。
1961年2月,吴征镒随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在广州开热带资源开发利用会议,在会上首次提出“开发热带作物的同时必须建立相应的自然保护区,以保存和继续观察自然环境的发展变化”,这一建议后由钱崇澍、陈焕镛等在全国人代会上正式提出议案。后吴征镒又和寿振黄在云南省提出建立全省24个自然保护区的具体建议,并首先由曲仲湘率队在热带勐龙、小勐养进行本底调查,不久,小勐养和勐仑、勐醒等三处的自然保护区也予以划定。这是吴征镒涉足保护生物学的开始,现在我国自然保护区已成为一大事业。
1962年5~6月,吴征镒率队赴古巴进行热带植物考察,此行取道前苏联,重访莫斯科,再至捷克,经爱尔兰越大西洋,到加拿大,又循北美大西洋岸南下直达古巴,遍历了古巴全国。这是吴征镒首次到新世界,并见到加勒比海植物区系。虽然只采了少数植物标本,但却在其南岸原为Arnoldarboretum的热带分园内,采得各种树木种子共一大柳条包,托当时在古巴作外交访问的卫生部长李德全带回国。这批种子是当时在美国封锁条件下“漏网”的首批热带植物,有酒椰子Raphia、香果Casimiroa(芸香科)、猴面包树、轻木、象耳豆等等,均分给了西双版纳植物园和海南的热作学院植物园种植,其中有些至今已成大树。此行也为后来赵其国(研究土壤学)、郝诒纯(研究微古生物学)赴古巴做援助专家作了铺垫。从古巴归国不久,吴征镒又与云南大学生物系朱彦丞教授和北京植物所研究生陈艺林等赴丽江、中甸进行了历时约两个月的植被和植物区系调查。
1964年1~4月,吴征镒与北京植物所汤彦承、张永田组队赴越南北方考察,足迹几遍北越,此行的收获是肯定了越南北方至我国南方的区系相似性及其从第三纪以来共同的历史发展背景,这些都充实了吴征镒随后发表的《中国植物的热带亲缘》一文的内容。
同年10月,吴征镒又率队赴柬埔寨考察,虽所见原始林区甚少,但也见到稀树草原中的龙脑香林和吉里隆的热带松林。柬埔寨若和北越相比,显然热带性更强,更带有印度色彩。
1966年,“文革”开始,吴征镒是“当权派”,又是“反动学术权威”,毫无例外地被批斗和关进“牛棚”。大约是1970年,全国兴起大搞中草药运动,他在劳动之余为云南省中医中药展览会展出的中草药进行学名订正,利用同志们为他搜来的各地中草药手册,整理记录了各地中草药植物的四大本笔记,后来成为编辑《新华本草纲要》的基础和基本上可靠的依据。在艰难的岁月里,吴征镒虽身处“牛棚”,但仍旧坚持做科研工作。他那双深沉的眼睛不知疲倦地寻求、思索着。一种渴望献身的欲望,一种拥抱祖国母亲的激情,久久地缠绕着他。他坚信,冬会过去,春会到来,枯萎的树枝会绽放嫩芽,会结出蓓蕾,会繁花满枝……
(十)
1972年,吴征镒基本得到“解放”,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他热爱的植物学研究事业。
1975年,吴征镒(左三)在海拔5000米的西藏希夏邦马峰考察在上世纪70年代,进西藏进行植物野外考察,对每一个科学家来说都是艰难的,一是缺氧,二是交通不便,三是不少地方人烟稀少,人迹罕至。1975年5月,花甲之年的吴征镒参加了中科院组织的青藏高原考察。在3个月的时间里,他到了藏西南的日喀则、聂拉木和志隆萨噶。他的任务是考察喜马拉雅山北坡的植被和青藏高原的植物区系,包括森林、灌丛、草甸、草原和高寒荒漠等。吴征镒真正体会到西藏的雄伟和辽阔,壮丽和神秘。西藏辽阔深邃的蓝天,白雪皑皑的雪山,晶莹透明的冰川,湍急而清丽的河流,都让他激起了诗情。然而,青藏高原的特殊地理环境和植物的分布更引起他的兴趣。以至于1976年6月他再次从道路十分艰险的滇藏线进藏,横穿三江(金沙江、怒江、澜沧江)大峡谷,又对喜马拉雅山脉的南坡和东南坡植被进行深入考察。在这里,他对横断山脉地区植被的分布带有了更深的了解;对金沙江、澜沧江分水岭和澜沧江、怒江分水岭植物垂直带的分异,对西藏高原面上和雅鲁藏布江沿岸的河谷柏树林及大片原始云杉林等生物多样性的差异和联系,有了深刻印象;对三江河谷的干热、干暖及干冷河谷的植被的递变更有直观的感受。两次入藏,使吴征镒对横断山地区和西藏高原植物区系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和认识,他花甲之年的生日也是在林芝度过的。
进藏考察时,吴征镒一路上都是谈笑风生,毫无倦意。他在颠簸的吉普车上,仍然手拿纸笔,随手记下车窗外看到的植物。在泥泞的山路上,他因为平足而经常摔跤,让他吃尽了苦头,走遍中国的吴征镒也因此获得了一个“摔跤冠军”的称号。有一年在云南文山考察时,吴征镒摔了一跤,却因为这一跤而发现了云南的一种新植物——锡杖兰。所以他笑言:“摔跤好啊,摔跤还可以发现新种呢!”
1984年,吴征镒去实验室途中出了意外,左股骨颈骨折,从此以后,他只能拄杖而行。但他从没有停下自己奔波考察的脚步——
上世纪80~90年代,吴征镒先后进东北、内蒙古,在大兴安岭、长白山和千山考察,对我国北方的温带植物区系进一步加深了认识。他还两次入新疆,从西宁翻越祁连山时,虽是6月却遇漫天大雪,他坚持冒雪前行。一路上,他考察了戈壁荒漠,考察了天山、阿尔泰山的旱生草甸、草原植被,以及特有的春雨和夏雨短命植物,还到新源的野果子沟看原生的苹果属Malus的自然林,直观云杉植被和其他林带分布。后来,他又对华中的梵净山、张家界、天平山、神农架,华西的灌县卧龙、九寨沟、黄龙寺,东南的武夷山、天目山、千岛湖等地进行考察,其间还到海南总结人工群落的工作。直至1998年到宝岛台湾,从台北、台中、台南一直考察到最南端海岸,才结束了他的国内植物考察工作。对全国的野外考察,使吴征镒对中国广阔国土上的植被类型和植物区系以及从热带、亚热带到温带、寒带的植物区系分布的替化性和过渡性已了然于胸。加上70年代两次进藏的考察和对中南半岛诸国(越南、柬埔寨、菲律宾和泰国)的考察,使他对青藏高原的各种垂直植被带分布以及喜马拉雅与横断山脉的联系与区别,还有对中国南部热带季雨林与中南半岛的热带雨林的联系和分异等问题,有比以往更为清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