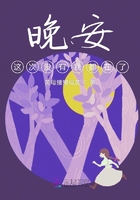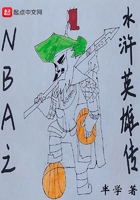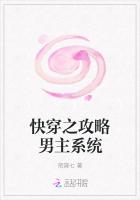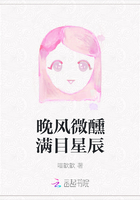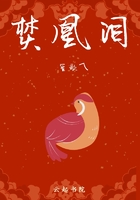在五四运动的前夕,我在上海同济大学学习德文后,因法租界封闭了同济,同济迁吴淞,我无意学医,自己在家阅读德国古典文学,歌德、席勒、赫德尔林等诗人的名著,同时也读了一些哲学书,如康德、叔本华、尼采的著作。当时青年的求知欲和关心国家前途的热情是普遍的。第一次欧战的结束和俄国革命的成功对于中国青年的刺激是难以想象的。青年们相见时,不论识与不识,都感到有共同的要求,共同的热望,胸怀坦白相示,一见如故。少年中国学会的朋友们就是这样集拢起来,组织起来的。浪漫精神和纯洁的爱国热忱,对光明的憧憬,新中国的创造,是弥漫在许多青年心中的基调。少年中国学会的最早六位发起人一九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在北京岳云别墅聚会发起筹备学会后,我在上海由魏时珍同学的介绍加入学会的筹备,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王光祈到沪,二十三日在吴淞同济学校开第一次团体会议时我就参加了。王光祈青年老成,头脑清楚,规划一切井井有条,满腔爱国热情溢于言表,极得我的信任和钦佩。他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我认为他所写的《少年中国精神》是他的心血所凝成的文字,代表他的理想,也代表了“少年中国”初期成立时一些同人的思想。
五四后北京大学许多同学来到南方上海等鼓动罢校、罢市、罢工,我还记得在上海西门外大体育场全市学生及市民大会上看见许德珩、刘清扬在台上大声疾呼,唤醒群众,至今脑中印象犹新,非常兴奋。我会见黄日葵、康白情、陈剑修(他是当时全国学生会主席之一)等人,黄日葵后来成为共产党员、壮烈牺牲了。他是热情多感的广东青年,非常纯洁可爱。
少年中国学会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七月一日正式成立前的期间刊出了几期《会务报告》,里面也刊载了上海会员的学术谈话会的情形,并发表了一些记录,我谈过一次康德的空间时间唯心说大意,又谈过一次歌德的《浮士德》。当时的学术兴趣异常浓厚,虽然所知晓的是浅薄浮泛。
我应了《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编辑郭虞裳的邀请,替代他编辑《学灯》。我主编《学灯》的一年期间,每天晚饭后到报馆去看稿子,首先是寻找字体秀丽的日本来信,这就是郭沫若从日本不断惠寄的诗篇,我来不及看稿就交与手民,当晚排印,我知道《学灯》的读者也像我一样每天等待着这份珍贵的,令人兴奋的精神食粮。我介绍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田汉到福冈市与他会晤。千里神交,一见如故,五四时期的浪漫精神也表现在这种青年人真诚相见,胸怀坦白,重视友情的方面。
这时少年中国学会刊行《少年中国》月刊,稿子由李大钊王光祈在北京编辑好,寄来上海我处,我送去付印,负校勘责任。我也写了一些文章。据闻读者尤爱看会务消息及会员间的通信,这也可以窥见当时一般青年读者兴趣所在(所以,亚东书局后来要求我把郭沫若、田汉和我的通讯编成《三叶集》出版)。
一九二○年夏天,我辞去了《学灯》编辑及《少年中国》
校勘职务,到德国去留学。我一九二五年夏天回国时,少年中国学会也完结了历史所赋予它的一段任务而停止活动了。
我认为研究少年中国学会这一段历史,可以具体地生动地见到五四以来中国青年思想及活动方面的一个侧影,见到它们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反映着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内在的矛盾。
原载《五四时期的社团》第1册,
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554-5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