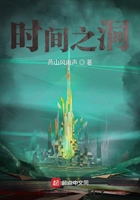舞会除了熟人谈天、招揽幕僚、调情暧昧以及相互恭维,终于发挥了一点点作用,也不知是好是坏——英国的使臣提出来想看看中原战线的战况,看看有没什么帮得上忙的。帮忙当然是客气的说法,每一个头发金黄、八字胡卷曲、见了女士进屋便起身的英国使臣都是一个狡猾的商人,这是科长的原话。那湛蓝的眼珠子稍稍一转,就有了新的好处可以占。帮忙?至多是相互利用,不从我们这儿再多挖些去就算客气的了。
然而纵使这样,前线吃紧,无论是武器、战术还是最简单的钱粮,当前能拿到的都是好的,不管日后利滚利是多少。我们要做的一份图文并茂的报告也就格外重要。报纸上刊的全是笑容满面、精神振奋,丝毫没有用处,反倒是那些不得公布于众的影片才是真实的需要的。
然而几个战地记者带回来的照片里,连破败的房屋都少见,显然在后方离郑州都还有好长一段距离,不过好在总司令的相片倒是拍得很全面的,仿佛衣食住行都寸步不离地跟到了。
科长领头挑了几张,然后就再也挑不出来了,把那一叠相片往桌上一推,“拍来拍去都是何司令,这么脸色红润精神饱满,我们还装什么可怜,要什么粮草?”气得直拍桌子,拍完坐在椅子上继续找,却一无所获。
我打了舞会上拿到的号码,那个自由的摄影师本就送来了三四张样片,战壕里了无生气的兵士与街市上双眼空洞的市民,看得科长大喜过望,报了三百块大洋的经费,向本买下了一百张相片。
本来办公室送相片的前一天,我给他打了个电话,希望他能把拍到的程昊霖的所有照片都放在那一百张照片里。他沉默了一会儿,我的本意不是拍指挥官的,更不是为了什么私人的目的。
你拍到的指挥官里最前线的就是他,他如果不能出现在报告里,全是后方脑满肠肥、夜夜笙箫的军官,是你要的结果吗?
他说了句我想想,就挂了电话,留给我一个焦灼的夜晚。
这些天和同事熟络了,他们下班之后的饭局也带上我,谈天说地间现今的局势也了解了一些。本地的、直系、皖系背景的早就盘根错节、暗流涌动,近一年来北面来的奉系背景的人加入更是成了一团乱局,军中局里,处处针锋相对。奉系的人原本就在军里的多,这次打起仗来,人人都知道,若是凯旋归来,那还不是如日中天。等到他们如虎添翼地回来,倒不如现在占据自己在后方的优势抢个先机,多吹吹风,把军中亲自己的人抬一抬。
科长嘴上说着挑不出,暗地里十来张已经扣下了,从低级军官到高级将领,早已盘算好在报告里放的位置,就等着一些惨兮兮的底层图片一合,报告就写好。
心里知道,他和程昊霖不是一派的,断不可能爽快的把这本就宝贵的版面分给他,但是如果一百张里倒有三四十张,摄影师又是英国使臣的儿子,他不可能毫不顾忌。虽然摄影于本来说是个纯粹的兴趣,但在老谋深算、处处算计的科长眼里,大概也代表着一种他参不透的力量。
我心里这样盘算着,待到第二天看到本冲着我爽快地一笑,心下明白,终于还是说动了他。
这边的石头落了地,家里却又不太平。
苏北老宅有个老管家,帮着舅舅收着家里地的租子。今年春天瘟疫,整个村子人减了靠一半,地里收成惨淡,收成上来只能勉勉强强抵上古董铺子里的帐。心里暗念,亏得有了这个对外事务部发的饷钱,不然这日子还不知道怎么过。
回家的时候,往常都闷坏了的文竹,今天却格外的振奋,听到我的脚步就忙不迭开了门。
“二小姐!”她愉快的腔调里带着点幸灾乐祸,“小翠又给我写信了,小翠,就是那个豆腐西施。”我点点头,小翠我是知道的,豆腐西施这个名字也是够损,叫她豆腐西施绝不是因为好看,反倒是因为长得怪异了些,原先被叫东施,后觉得东施东施的叫唤,不太尊重,就改成了西施。让我看,这改了不如不改,都是些没有口德的人干的。好在这卖豆腐的小姐儿虽然先天不那么好看了点,心胸却豁达,“怎么的?我还算得上西施,你们连西施丫鬟也不是。”也就哈哈一笑过去,这豆腐西施后来便成了她的名字似的,被人忘了初衷。
文竹虽是家里的丫鬟,没什么亲人,却是个活泼的人,从前在苏州城里,朋友不少,最好的就是这个豆腐西施,让她去买个豆腐,一去能去个半天也不见人影。
现在她人常在南京,那个豆腐西施趴在私塾外头,也学了些字,两个人勉勉强强也能写信打发点时间、叙叙小姐妹的友情。
“你还是说小翠吧,我懂的,豆腐西施……”我摇摇头。
“她不在意。”她摆摆手,帮我接过包,将门带上,“从东街郎中那儿听来的,张家上上下下瞒得一丝不漏,终究还是传出来了。”
张家?回到南京之后,我一直忌讳再提苏州的事情,连想都不愿意,至于张家,我常常诧异于世交原是这样脆弱不堪的交情、所谓青梅竹马原是这样虚伪的情谊。“出什么事了?”我皱皱眉,“别又在我家祖宗边上搞什么名堂。”
“哼!让他们埋金锭子,让他们压咱们冷家!”她总是义愤填膺的模样,“真是活该!这就是上辈子做的孽,这辈子来还。不对,做这么缺德的事情,想损人利己,这辈子下辈子都别想还清!”做出一副要啐一口的样子,见着我摇头,不知说了她多少回,今天总算忍住了。
“那个好不容易嫁进去的玲玉。”她从来直呼她的名字,带着不屑与愤愤,都是替我表达的,“你猜她得的是什么病?”